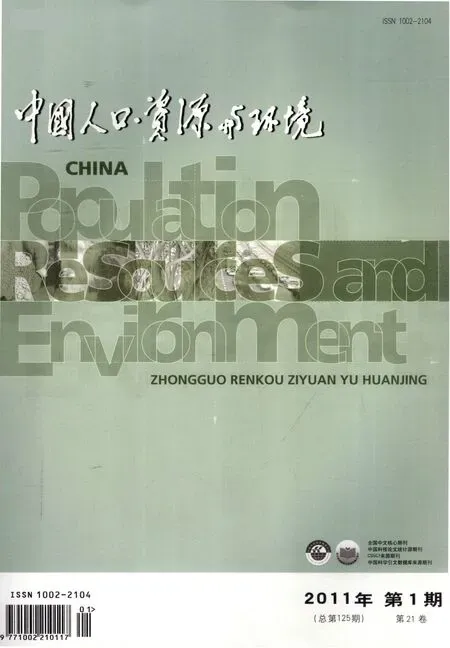當代生態維護的困境與生態新理念的建構
羅康隆
(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
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既然爆發于當代,而當代世界的工業類型文化又占據著主流地位,致使在評估生態維護的得失時,肯定會將矛頭指向工業類型文化,批判其在生態維護上的嚴重失誤,并要求當今世界上的工業類型民族承擔起全部后果來。作為一個認識過程,這并不奇怪,也可以理解,但千萬不能將這種責難流于具體化。因為自然與社會都沒有止境,而人類社會的認識卻始終是有限的。工業類型文化僅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所能形成的認識也是有限的,它與人類歷史上的其他類型文化并無質的區別。因而在對待生態問題上出現失誤,甚至是極其嚴重的失誤,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時也是無法具體承擔責任的。因此,具體的生態維護失誤是任何一個民族都會犯的,但最終都是可以挽救的。因而具體的失誤追究,特別是將工業類型民族孤立出來進行追究,并不能改變人類社會在生態危機面前的被動局面。要改變這一局面的唯一辦法只能是,探求造成這種失誤的實質,以及由此而釀成生態危機的過程。只有對這個問題獲得了泛化的理解,才能確保當今世界上的所有民族能心平氣和地面對生態挑戰,并在具體的生態維護行動中協調一致。
1 當代生態維護的困境
當代生態危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很多無機世界的物質和能量運動形式被引進到了地球生命體系之中,推動這種引進的主要力量來自工業類型民族,這樣的引進使人類社會擁有了極為強大的實力,可以局部地改變地球表面的生存環境,從而提高了人類社會的生活質量。這樣的引進是文化發展的必然,也是人類社會的需要。但問題在于,人類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樣的引進應當有一個限度,不能威脅到了人類社會的寄主——地球生命體系的安全。可見,當前面對的生態危機并不是質的問題,而是一個防范過猶不及的量度問題。只要不將工業類型文化絕對化,我們總會看到即使工業類型文化不復存在,或者工業類型文化種下的所有生態惡果全部爆發,人類社會及其文化也還沒有走到盡頭。換句話說,當代的生態危機對人類社會而言并不是致命的,而是人類社會自身有能力加以消解的。目前的關鍵問題是,人類社會能否找到一種調節機制,將人類社會對化石能源、核能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費控制在一個地球生命體系能夠容忍的范圍內;或者找到一種替代形式,可以使人類社會無需消耗如此巨量的化石能源和核能,卻同樣可以保持人類現有的生活質量。那么當代工業類型文化所造成的全部生態后果都可以得到逐步的消解,人類社會也可以從中獲得可持續的發展。要做到這一步單靠工業類型文化是遠遠不夠的,但要確保處于任何一種類型文化的民族都能平等地參與全球生態維護,必須建構一個前提,那就是不能將工業類型文化的價值觀和文化建構體系強加于其他民族。由于工業類型文化在當代處于主流地位,因此建構這樣的前提顯然需要它來承擔責任,而它也有能力和義務承擔起這樣的責任。
全球市場體制是工業類型文化的派生產物。對這個派生產物的認識也應當一分為二。從好的一面看,正是這一體制使人類獲得了宏觀的全球視野,從而賦予生態維護一種全球性的眼光,這是人類社會的無價之寶。從壞的一面看,正是這樣的市場體制掩蓋了人類的生物性本質,使世界上的各民族文化被市場牽著鼻子走,從而忽視了任何一種文化都必須寄生于具體的一種或幾種自然生態系統之中,才能正常延續和發展。各民族在追求直接經濟效益的同時,將文化的生態調適幾乎擱置起來,最終降低了人類社會對地球生命體系的總適應能力,這才是當代生態維護的大敵。
地球生命體系是復雜的龐大體系,人類社會要與之保持安全的寄生關系,自然得有豐富復雜的各具針對性的手段[1]。但經濟的全球化導致的卻是市場價值單邊化。光憑這樣的單邊市場價值觀顯然無法應對錯綜復雜的地球生命體系的多重反饋。如此龐大的體系必然充滿了多重復雜的反饋方式,也具有無比多樣的偶然性,人類社會的價值觀一旦劃一,始料不及的地球生命體系反饋都可能動搖人類社會的安定。這是當代人類社會生態維護中的又一重大失誤。
當前,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潮流,既然是潮流,那就意味著會有潮起潮落。世界各民族應對這種潮流的最佳選擇莫過于承認它的存在,但卻不能對其產生過分的依賴,應當啟動本民族的文化排抗機制,對這一潮流加以節制,以免忘記文化的本質之一——文化需要對生態進行調適。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在經濟全球化中陷得太深,以至于在其退潮時,民族文化成了它的殉葬品。工業類型文化不僅派生了市場體制,而且為了自身的利益掀起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因為經濟全球化而導致的生態危機正是工業類型文化自身利益驅使的結果,因此,他們必須為此擔負相應的責任。
工業類型文化在生態問題上的第三個重大失誤是對生態危機的轉嫁與規避。當今世界上最先發展起來的工業類型民族,還在他們的起步階段就已經注意到了生態問題的危險性。但是這樣的認識卻長期被工業類型民族掩蓋起來,將其視為發展所必需付出的代價,而長期沒有將生態問題的處理提到議事日程。等到生態問題極其嚴重后,則采取了另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將生態災難轉嫁到其他類型民族身上。
由于這種轉嫁有市場體制作為掩護,有虛假的平等和人權作為偽裝,致使這種轉嫁長期蒙蔽了其他類型的民族。直到地球生命體系的運行規律發揮了作用,由于復雜系統必然具有的內在牽連性,使得那些轉嫁出去的生態災禍通過地球生命體系的運作反沖,最終又威脅到工業類型民族身上,他們才被迫承認生態危機具有全球意義,也才開始著手認真地研究和對待生態維護問題。這種做法盡管是一種亡羊補牢的措施,但畢竟值得慶幸。因為它可以借此將全球各民族調動起來,共同參與生態維護。
可見,工業類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釀成眾多的生態災禍,并不是他們應當承擔的主要責任,因為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新興的文化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但有意識地把禍水外引,卻是十足的民族利己主義,這個責任才是工業類型民族真正應該負的責任。其他類型民族需要思考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對他們自己而言發展的目標應該是什么?是無條件的仿效工業文明,還是走另外的道路?
文化的本質告訴我們,文化的生態調適和社會調適對文化而言都是必需的。為了追求與工業類型文化趨同,不顧后果地單方面強化社會調適,對非工業類型文化的民族而言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為了與工業類型民族趨同而接受轉嫁來的生態災禍,絕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建立這樣的認識,對建構有意識的生態維護同樣必不可少。
當代生態維護中另一個有害的隱患就是對科學與技術的迷信[2]。這種觀念的形成與擴大也與工業類型文化相關,是工業類型文化將本來有限的化石能源作為建構發展的基礎,在帶給人類重大成功的同時,使人類暫時忘記了這種基礎的脆弱性。與生態危機相并行的能源危機僅是化石能源的危機,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能源危機。但化石能源的超額利用卻給人類造成了技術萬能的假象,也正是這種假象導致了世人對傳統知識體系的蔑視,并由此而發展為對各民族生態智慧與生態技能的踐踏。由此而形成的生態后果,才使得人類社會必須面對有史以來最大的生態危機。現代科學技術的價值當然不容否定,但它也僅是人類知識體系之中的一個有限部分,而且僅是一個階段性的知識總匯。從原則上講,它與人類已有的傳統知識只能并行和互補,而不應當將它置于一切人類知識之上,去加以過分依賴。說到底,當代一切輝煌的科學與技術,僅僅是利用資源的能力,而絕不是能制造資源的能力,世界上只有地球生命體系可以為人類提供有機資源,只有地球的無機構成可以為人類提供無機的資源。離開了這兩類資源,現代科學技術將變得毫無意義,而生態維護則是能為人類社會可持續提供有機資源的務本之舉。
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到了“技術異化”這一概念,標志著人類逐漸意識到了工業類型文化建構的知識體系存在著天生的弱點,它無法確保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當代的生態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現有的知識技術體系被濫用的結果。而濫用的最極端表現形式就是將它當作獲取利潤的手段,而不是用于增進人類的智慧和促成各民族間的協調。而這兩方面的知識利用,恰好是生態維護最必需的內容。人類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與地球生命體系的關系,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跨文化的協調就不能實現,現代的科學技術水平帶給人類社會的將是災難大于造福。因此,當今世界各民族對現代科學技術應當有清醒地認識,它僅是人類社會所掌握的工具。它優于以往的任何工具毋庸置疑,但人類社會使用工具首先要考慮的是它的適用范圍,無節制的使用遲早會釀成苦果。每一個民族都應當認真地考慮對現代技術的應用,應該從本民族的文化出發做出理智的選擇,對現代科學理論應當學習和把握,但只能將其置于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同等地位去加以對待。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當今世界上的各民族在理智上保持相對獨立性,才可望在面對自然生態系統不同的反饋時可以做出有選擇的清醒判斷。人類社會才可能擁有盡可能多的對策去應對地球生命體系的復雜性。如果全人類僅按一種模式思維,那將是十分危險的事情。一旦應對失誤,那將是一場慘劇。
各民族保持思維方式的多樣性,是維護文化多元并存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既然文化的多元并存是應對生態危機最有效的人類社會建構格局,那么清除對現代科學的迷信就勢在必然了。當然我們也應注意到,有不少學者提到了傳統知識與現代科學接軌的問題,從生態維護的角度看,確實有這樣的必要,因為它是確保人類的生態維護相互協調的認識基礎。但在其中,隱含著這樣一個前提,那就是傳統文化,包括各民族的傳統生態智慧與生態技能必須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不然談結合就失去了意義。
因此,絕不能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接軌簡單化,從而造成傳統文化需要屈從于現代科學理論的誤解。相反地,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理論只能是并行的知識系統,它們可以相互映證、相互溝通,絕不是任何形式的合二為一。這一觀念形態上的基本原則,絕不能放棄,放棄則意味著多元文化的并存名存實亡。也正因為現代科學迷信帶給人類的是一種假象,因而在這種假象掩蓋下,釀成的生態災變往往更具有欺騙性,救治起來就更困難。這也是正確評估維護成效的最難突破的思維死角。
地球生物資源消費的單向傾斜擴大到全球范圍,這是工業類型文化留給當代生態維護的最后一個失誤。作為地球生命體系的寄生體,人類社會根本沒有能力屈從自己的意志,只能是人類社會認識地球生命體系的實質去加以均衡利用。但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在其進程中出于調整族際關系的需要,社會適應總是不免要掩蓋生態適應,從而導致了各民族生境對所處自然生態系統的偏離,在無意識中擴大化和疊加。對地球資源的單向傾斜利用也就因此而發展起來。但把這種單向利用方式擴展到全球,則是工業類型文化留給現代生態維護的難題。人類社會運行到今天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那就是人類的活動已經切斷了許多原有的食物鏈,使許多生物物種間的生命物質和能量及其信息的流動,屈從于人類的意志,從而使生態系統失去了自我修復,相互替補的調節機能。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社會已經不得不替代某些生物物種去參與地球生命體系的物質和能量循環。但對這些循環的信息控制渠道,人類社會并沒有放在心上,于是造成了只會無節制的利用,而不遵從應用規則的畸形行為模式。若不改變這種背離地球生命體系的運行模式,人類社會很難與它的寄主長期共存。匡正這一失誤具有更大的難度,因為人類建構的文化自身存在著弱點:為了確保文化對所處社會維系牢靠,文化越穩定、越按慣性延續越好。對地球生物資源的單向消費一旦被相關民族的成員所接納,校正起來就得面對文化的慣性延續,就得挑戰文化慣性延續的本能,因而它必然要牽涉到相關文化的重構。目前,人類對生態問題的探討尚未對這一失誤引起警覺,這將會造成更大的不良后果。
2 多元化發展與21世紀環境保護
生態理念對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而言,由于所處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彼此的立足點和建構的發展目標也呈現出各自的特色。
21世紀初以來,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們從自己所研究的學科出發對新的生態理念的建構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南京師范大學陳君博士認為,工業文明為人類社會的繁榮帶來了巨大貢獻的同時,也帶來了深重的環境危機和能源危機,不僅使經濟的增長難以為繼,也使整個人類社會的持續生存和發展面臨困境。因此,人類的生態理念必須轉向一種新的文明,即以生態文明作為一種人與自然和睦相處、協同進化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而這些生態文明的特征則體現為物質生產生態化、生活方式生態化、社會制度生態化。他提出實現生態文明的有效途徑有兩條:一是改進生產工藝,倡導清潔生產;二是優化人們的生活方式,建立合理的消費觀念[3]。
20世紀人類社會面對的生態難題十分繁復,其中較為集中體現為各種能源的超負荷利用和有毒“三廢”的處置無法得到科學的解決,這是資源利用方式趨于單一化的惡果,而資源利用方式的單一化則是由于原有文化制衡在解體后新的文化制衡格局尚待建構的過渡時期必然伴生的狀況,而人類歷史上類似的狀況曾多次重演,只不過具體的內容和波及的范圍與當代略有不同。21世紀的生態人類學研究目標僅至于縮短這個必經的過渡時期,加速新興文化格局的定型,為此生態人類學需要分析發現當今強勢民族的文化運行弱點幫助弱勢民族獲得更強的延續能力,借助文化的誘導重構和文化要素的嫁接,推動強勢民族資源利用方式的多元化,利用各民族資源利用方式的客觀差異,引導各民族在資源利用上的互補和互惠,利用文化的差異引導不同民族以至社會調適的無限擴大,集合各民族潛在的生物適應機制,從積累下來的“三廢”中開發新的再生資源,實現“三廢”治理和資源利用的有機接合,憑借對人類已有文化的系統把握,借助現代的科學技術手段,使生態人類學成為21世紀人類面對生態困境時科學解決相關問題的重要依據。
對于生態維護的艱巨性及其當代生態維護中的眾多失誤,上文已經做出了討論,但與此同時,工業類型文化也給新的生態維護鋪墊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使人類社會有可能高起點的去應對艱巨的生態恢復問題。
工業類型文化帶給了人類社會無比豐富的物質財富,這樣的財富對地球生命體系而言會構成各種沖擊和擾動,但由于人類種群具有兩重性,因而可以將這些財富應用于生態維護之中。在化石能源還能支撐人類社會以前,盡快地消除已經露頭的生態災變,建構一個世界各民族都可以接受的生態安全體制,使生態維護職責具體落實到每一個民族,由每一個民族分別完成其具體承擔的生態維護責任,同時建構起全人類的泛化生態維護框架,確保每一個民族的生態行為協調一致。
工業類型文化為人類社會建構了高效便捷的信息網絡系統,可以將全球發生的事情在短時間內納入觀察的視野。這是保證泛化生態維護協調有效與起碼的物質裝備。利用好這一系統,全球生態安全的監控將成為可能,這對于建構有意識生態維護的體制顯然是一個必備的條件。不過,它僅是物質裝備,代替不了對各民族生態智慧與生態技能的具體認識和把握。突破信息隔膜,完成各民族生態智慧與生態技能的溝通與理解,這是生態民族學具體要完成的研究任務。
工業類型文化出于分割市場的需要,建構起了一系列的國際協商機制,盡管這些機制無一不打上特定民族文化的印記,其運行的實效也大可懷疑,但這樣的溝通機制畢竟給全人類提供了一個相互闡明觀點和思想的場所。利用好這樣的場所,對于強化各民族在生態維護中的協調機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近年來通過《里約熱內盧宣言》、《京都議定書》以及聯合國有關抑制軍備競賽的決議等等,盡管很難在短期內徹底生效,但至少讓世人看到了一線希望,并提供給人類一些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歸根到底都與生態維護相關聯,因此這樣的溝通機制對全球的生態維護可以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可以吸引全球各民族的廣泛參與。這是泛化生態維護必不可少的先行步驟。
最后,工業類型文化所驅動的現代科學研究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無比豐富的知識庫藏,幫助全人類提高了對地球生命體系的認識。盡管這些認識還遠遠不夠,但它畢竟是建構今后泛化生態維護體制的理論基礎。工業類型文化還給全人類帶來了一系列有效的技術,只要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技術的適用范圍,那么這些技術在生態維護中就大有用武之地。有了這樣的科學技術,再加上各民族的生態智慧與生態技能,泛化的生態維護才可能做好。
總之,工業類型文化產生后,對全球的生態維護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造成了眾多的失誤。現在已經到了清理這些失誤,從頭開始著手全球生態維護的時候了。
(編輯:王愛萍)
[1]劉國城,等.生物圈與人類社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邱夕海,陳俊明.從科技異化和科技人化:西方后現代主義對科技的倫理反思與道德重塑[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1,1(2):5-8.
[3]陳君.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1,11(S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