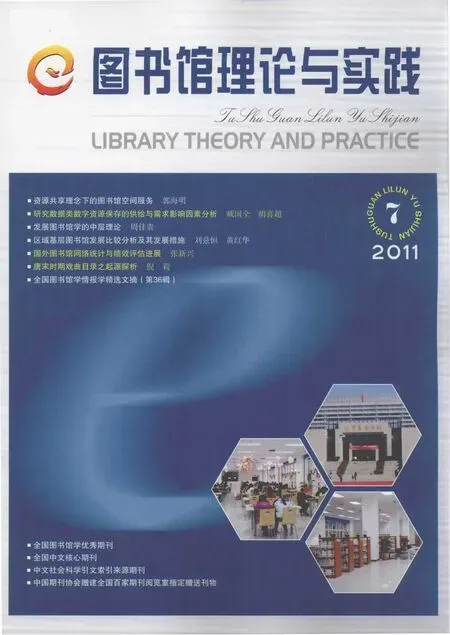敦煌寫本《茶酒論》文體考論
●鐘書林(西安文理學院 文學院,西安 710065)
敦煌寫本《茶酒論》自發現后,引起學人的極大關注,成果夥多,但意見的分歧也較大,尤其以它究竟歸于哪一類文體的分歧為最大。現按照其說法出現的先后順序,逐一梳理,然后闡述淺見,以期能將方家對《茶酒論》文體的認識及其淵源的理解有所補充。
一
敦煌寫本《茶酒論》見于伯2718、伯2875、伯2972、伯3910、斯406、斯5774六個卷子。《茶酒論》最早為劉復先生編入《敦煌掇瑣》,在目錄中,它與《韓朋賦》《燕子賦》等,同被歸入小說類。[1]至于原因是什么,可惜劉先生并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但這卻是對《茶酒論》文體最早的說法。
稍后,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中首次對《茶酒論》作了粗略研究,他認為《茶酒論》是從戰國時期宋玉的大言賦、小言賦發展來的“爭奇”一類的游戲文章。[2]大、小言賦的結構主要采用問答對話的方式,《茶酒論》的結構模式與之大體相同。由于鄭先生是在俗文學史中說這番話,后世將《茶酒論》稱為俗賦或由此而來。不過要強調的是,鄭先生本人并未使用“俗賦”一詞。
到了20世紀50年代,王重民等6位先生編撰的《敦煌變文集》中收錄了《茶酒論》,[3]王先生將它歸類為敦煌變文中的對話體。[4]80年代初,張錫厚先生率先突破成見,指出《茶酒論》應是受誹諧文影響的論議文體,短小精悍,論戰性強。[5]隨后,周紹良先生進一步肯定了《茶酒論》受前代誹諧文體的影響,并將它歸入論說體。[6]受周先生的影響,顏廷亮先生主編的《敦煌文學概論》等書中將《茶酒論》歸入敦煌文的論說體進行了深入論述。[7]到了90年代初,趙逵夫先生又從戲劇的角度提出新的看法。他認為,《茶酒論》應是唐代的一個俳優戲腳本。[8]稍后,或受趙先生說法的啟發,王小盾先生提出了一種“論議”的新文體:“指一種由表演雙方圍繞特定命題往復話難、以問答形式進行的伎藝及其文學記錄”,[9]并將《茶酒論》《孔子項論相問書》《晏子賦》和五言體的《燕子賦》等歸入了此類文體。盡管眾說紛紜,新見迭出,但在90年代末,張鴻勛先生編撰《敦煌學大辭典》“茶酒論”條時,遵從一般性的說法,將《茶酒論》歸入俗賦一類。[10]不過這一分類,仍然遭到了譚家健先生的異議。譚先生提出:“據我所見,似乎可以算作白話散文。”[11]
以上從劉復到譚家健先生,縱觀《茶酒論》文體研究近百年的歷史,圍繞《茶酒論》的文體分類先后形成了8種不同的說法,雖然有些說法較為近似,但總體分歧仍然是較大的。可見《茶酒論》文體的復雜性。
其復雜的程度,還表現為對《茶酒論》文體的認識,有時甚至在同一位研究者那里也會出現前后不一致的看法。如對敦煌文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顏廷亮先生等在《敦煌文學概論》(1993年) 中將《茶酒論》歸入“論”體,但到了他們編寫《西陲文學遺珍——敦煌文學通俗談》(2000年)一書時,卻轉而同意王小盾歸入“講唱”體的說法。[12]這些前后不一致看法的出現,正證明了顏廷亮等先生仍然還在孜孜不倦地思考、探索,以求找到關于《茶酒論》文體的最佳答案。
二
《茶酒論》以擬人的手法,采用對話體的結構方式,茶與酒論辯短長,相互爭功,最后由水出面調停,點明題旨。這些特點都能在先秦諸子散文中找到它們的影子。先秦諸子散文作為中國散文的源頭之一,大多都采用的是語錄體對話形式。春秋時期,《論語》《墨子》多以語錄對話的方式結構謀篇;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為了闡明各自的主張,論議辯對之風盛行。以《莊子》《韓非子》為例,多有與《茶酒論》結構、文體相似者,茲舉數例以證,并明瞭其間的源流關系。
《莊子·逍遙游》開篇寫鵬鳥“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卻招來了蜩與學鳩的譏笑:“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而莊子最后出面批評二者說:“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在這里,莊子充當了第三方“水”的角色,蜩與學鳩炫耀己能,攻擊對方,實有茶、酒爭妒的身影。而眾所熟知的《莊子·秋水》中河伯與海神若的對話,通過7輪的反復問答、辯對,最后莊子給出結論:“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首而勿失,是謂反其真”。不過其最為相像者,應首推《秋水》中夔、蚿、蛇、風之間的對話: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不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
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圣人能之。
夔、蚿、蛇、風互相爭勝,論辯短長,而都只看到自己的長處,對方的短處。這一番對話,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與《茶酒論》很接近了。前文所引鄭振鐸先生在他的《中國俗文學史》中指出:《茶酒論》是從宋玉的大言賦、小言賦發展來的。大、小言賦是有名的對話體辭賦,將《茶酒論》歸為俗賦也即由此而來。其實,宋玉的對話體辭賦并不是最早文學樣式。已有學者通過對比研究指出:“宋玉的辯對作品在辯對結構、辯對藝術特色和思想內容等方面,對《莊子》借鑒頗多”,“宋玉的賦,都采用問答的方式,以問開頭,從而引出后文的長篇大論。這正是《莊子》辯對文體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同時“漢大賦的文體結構遠承《莊子》,近承宋玉之賦,與之有明顯的淵源關系”。[13]因此,《茶酒論》的文體淵源并不止于宋玉的大、小言賦,它還得從《莊子》說起。
不過,它的文體淵源也并不局囿于《莊子》,《韓非子》《戰國策》對它也應有較大的影響。《韓非子·外儲說》記載的“鄭人爭年”較為典型:“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后息者為勝耳。”兩人為了爭年,競相夸耀,虛妄無比。而《戰國策》的“鷸蚌相爭”:“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鉗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舍,漁者得而并禽之。”蚌、鷸互相斗狠,兩敗俱傷。這一極為深刻的反面教訓,為《茶酒論》所吸收。
上述例證足以讓我們明瞭《茶酒論》的文體特征是散文,而不是其他。實際上,在上文回顧的有關《茶酒論》文體歸類研究的8種代表性意見中,如果濃縮一下,主要是5類:(1)小說類:劉復先生持此說;(2) 變文說:王重民等先生持此說;(3) 俗賦類:鄭振鐸、張鴻勛先生等持此說;(4)散文之論說類:張錫厚、周紹良、譚家健先生等持此說;(5)戲劇講唱類:趙逵夫、王小盾先生等持此說。小說類、變文類的分法,是早期敦煌學家的觀點,由于當時時代條件的束縛,他們看到的資料很有限,所以他們的歸類也有點欠于穩妥,后來信從的人也極少。戲劇講唱類的分法,“以表演的伎藝特征來區分敦煌文學作品的類屬,固然無可厚非,但是若以此替代敦煌文學作品的文本特征,就有可能導致把某些不具備表演伎藝特征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以散體敘說為特征的敦煌文,將繼續被擯逐在敦煌文學之外”。[5]所以以此對《茶酒論》的歸類,似乎就有些不恰當了。
“俗賦”類的分法,帶有較深的“敦煌俗文學”的色彩。由于鄭振鐸先生在敦煌俗文學上的貢獻,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內,就用它來指代了整個的敦煌文學。直到張錫厚先生的《敦煌文學》及周紹良先生牽頭而由顏廷亮先生主編的《敦煌文學》的相繼問世后,“敦煌文學”的提法才逐漸取代了“敦煌俗文學”之說。因此,筆者以為將《茶酒論》歸于俗賦,仍然是“敦煌俗文學”提法的遺留的體現。最可稱道的是張錫厚先生,他在《敦煌文學》專門設有“俗賦”一章,但他并沒有將《茶酒論》簡單地歸入俗賦,而是高度評價了《茶酒論》在敦煌文學論議文體中的獨特價值。他說:“敦煌藏書中還有為數不多的論議文體,常常是為了論述某種道理而寫成的短小精悍的雜文,語言通俗,駁詰有力,論戰性強。如《茶酒論》就是一篇代表作。”[5]這是很有見地的。譚家健先生也說得很好,如果將《茶酒論》“歸之于俗賦,然而與同時的俗賦《燕子賦》、《晏子賦》、《韓朋賦》似有區別,否則何以不叫《茶酒賦》?”這一質問是很有道理的。《茶酒論》之所以稱之為“論”而不稱之為“賦”肯定有它的道理,盡管我們不能武斷地僅從“論”字上就判定它是論說文。
三
敦煌地處中西方交通要道,是中原文化與與西域文明的交匯之地。《茶酒論》出自敦煌鄉貢進士王敷之手,具有鮮明的敦煌地域特色。所以,它既帶有中原文化的烙印,又吸取了西域文明的養分。敦煌是佛教的圣地,也是佛教由此傳入中原的重鎮。佛教文化是敦煌文化的重心,出土的敦煌文獻中佛教文獻占了絕大的比重。因此,《茶酒論》的出現,不僅來源于中原文化的影響,也飽受佛教文化的浸染與熏陶。《茶酒論》一文,從內容到形式,也受到佛教典籍的一定影響。《茶酒論》擬人的手法,對話的方式,論辯短長,相互爭功等諸多文學要素,似也與佛教文學存在一定的淵源。《雜譬喻經》中記載有“頭尾爭大”的故事。
昔有一蛇頭尾自相與諍。
頭語尾曰:“我應為大。”
尾語頭曰:“我亦應大。”
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最在前,是故可為大。汝無此術,不應為大。”
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以身繞木三匝三日而不已,頭遂不得去求食饑餓垂死。”
頭語尾曰:“汝可放之,聽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
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在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火坑而死。[14]四528
這是佛教教誨僧眾時援引的例子,《茶酒論》中的茶、酒爭勝,與此處的頭、尾爭大,較為相似。只是頭、尾爭大中,沒有中間人出面調停,雖然頭到最后做出讓步,但仍不免頭、尾一同走向毀滅的悲劇結局,其警戒意義令人深省。《雜寶藏經》《佛本行集經》等典籍中還記載有二頭鳥[14]三923、共命鳥[14]四464的故事,情節與此略微類似:昔雪山中有鳥,名為共命。一身二頭。一頭常食美果,欲使身得安隱。一頭便生嫉妒之心,即取毒果食之,使二頭俱死。可見佛教故事,雖然大體情節與《茶酒論》相類,但結局都帶有悲劇性,或是佛教為加強勸世教化使然。
《茶酒論》中多處涉及佛教,即為受到佛教之影響的明證。如在茶、酒的第三番辯對中,茶對酒說:“我之茗草,萬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黃金。名僧大德,幽隱禪林。飲之語話,能去昏沉。供養彌勒,奉獻觀音。千劫萬劫,諸佛相欽。酒能破家散宅,廣作邪淫。打卻三盞以后,令人只是罪深。[15]茶多為高僧所鐘愛,但酒卻為佛教五戒之一,所以《茶酒論》中借茶之口指出:“酒能破家散宅,廣作邪淫。打卻三盞以后,令人只是罪深。”在第五番的辯對中,茶又對酒說:“阿你不見道:男兒十四五,莫與酒家親。君不見生生烏,為酒喪其身。……阿阇世王為酒煞父害母,劉零(伶)為酒一死三年。吃了張眉豎眼,怒斗宣拳。狀上只言粗豪酒醉,不曾有茶醉相言。不免求首杖子,本典索錢。大枷植項,背上拋椽。便即燒香斷酒,念佛求天,終身不吃,望免迍邅。”[15]在這次的辯駁中,茶不僅提到人們“燒香斷酒,念佛求天”,還引用了廣為流傳的阿阇世王為酒殺父害母的佛教典故。阿阇世王因為酒而殺父害母的故事,出自《觀無量壽經》等佛經,足見作者對佛教典籍的熟悉。就在與《茶酒論》的同一張經卷上,還寫有王梵志詩。其中有“飲酒是癡報,如人落糞坑”“造酒罪甚重,酒肉俱不輕。若人不信語,檢取《涅槃經》”等詩句,都為勸化世人戒酒。可見《茶酒論》的創作由于受到一定佛教文化的影響,在茶、酒的辯論中,一些佛教的教義、典故等也隨之自然流露出來,滲透在《茶酒論》的行文之中。
經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茶酒論》傳世以后,對后世的小說創作及藏族文學、布依族文學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藏族文學《茶酒仙女》將《茶酒論》中所受的佛教影響擴展到整部作品,“從故事背景、內容情節、人物取名等,都顯示出一種濃厚的佛教氣息”。[16]在《茶酒仙女》中,茶炫耀自己身世的高貴,自稱是天界如意寶樹的后代,生在天竺為菩提,生在支那為茶樹。在行文上,《茶酒仙女》與《茶酒論》有一些較為明顯的傳承和再創作的關系。如《茶酒論》中茶的自我夸耀語:“名僧大德,幽隱禪林,飲之語話,能去昏沉。”到《茶酒仙女》中則改為:“只有我才能使名僧大德欣然,使他們神智清醒,勤奮修行,增進智慧。”又如《茶酒論》中茶攻擊酒說:“酒能破家散宅,廣作邪淫,打卻三盞以后,令人只是罪深。……阿阇世王為酒煞父害母,劉零(伶)為酒一死三年。吃了張眉豎眼,怒斗宣拳。狀上只言粗豪酒醉,不曾有茶醉相言。不免求首杖子,本典索錢。大枷植項,背上拋椽。便即燒香斷酒,念佛求天,終身不吃,望免迍邅。”到《茶酒仙女》中有了較大的改動,變為“(酒)飲一碗,煩惱心起,手摸刀柄,口亂言語;飲二碗,丟掉了理智謹慎心,產生種種詭計邪念;飲三碗,全然忘記罪孽;飲四碗,竟勾引女仆、女商和娟妓;飲得再多,犯下了十不赦罪。”[17]相比較而言,內容更細化、具體,更富有生活氣息,語言也更加通俗化。因而,藏族文學《茶酒仙女》濃厚的佛教氣息,恰也從“流”與“源”關系譜上逆向折射出了《茶酒論》中所受的佛教影響。這樣,《茶酒論》的創作既受到了諸子散文的影響,又有佛學的沾溉。不過,由上文的分析看到,在這二者之中,它所受到的諸子散文影響無疑是主要的,并最終決定了它的文體特征。因此,它仍是一篇受諸子散文影響較深的論說文。
[1] 劉復.敦煌掇瑣[Z]//黃永武.敦煌初集叢刊第1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2]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M].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1984:175.
[3] 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267-272.
[4] 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C]//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73.
[5] 張錫厚.敦煌文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周紹良.敦煌文學芻議[J].甘肅社會科學,1988(1):104-115.
[7] 顏廷亮.敦煌文學概論[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492-494.
[8] 趙逵夫.唐代的一個俳優戲腳本——敦煌石窟發現《茶酒論》考述[J].中國文化,1991(3):157-163.
[9] 王小盾.敦煌文學與唐代講唱藝術[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20.
[10] 季羨林.敦煌學大辭典[K].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586.
[11] 譚家健.中國古代通俗文述略[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1):33-40.
[12] 顏廷亮,張彥珍.西陲文學遺珍——敦煌文學通俗談[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9.
[13] 劉生良.鵬翔無疆——《莊子》文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大正新修大藏經[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1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0.
[16] 張鴻勛.敦煌故事賦《茶酒論》與爭奇型小說[J].敦煌研究,1989(1):66-73.
[17] 李德龍.敦煌遺書《茶酒論》中的茶酒爭勝[J].農業考古,1994(2):7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