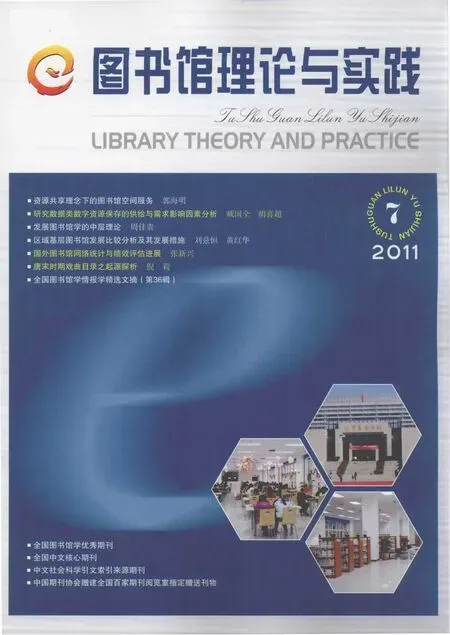孤本《蕅舲詩話》的內容和價值
●李淑燕(河南中醫學院 基礎醫學院,鄭州 450008)
詩話是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論詩文體,在詩歌發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清人詩話,以其數量的龐大和資料的豐富,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蔣寅先生在其《清詩話考》的自序中說:“經我十多年的考察,清詩話存世書籍已知968種,亡佚待訪書籍隨手記錄,也有504種——這還是不很充分的調查,因為我尚未徹底調查縣志,只瀏覽了省志、部分府志和少量縣志。縣志中著錄有大量的清詩話,實在苦于工作量太大,未能遍考。現合見存書目和亡佚待訪書目,已得書1472種,清詩話的總數超過1500種是沒有問題的。”[1]自序2而這個1500種也還只是一個保守的估計。除蔣寅先生外,關于清詩話的目錄書還有臺灣吳宏一的《清代詩話知見錄》《清代詩話考述》、蔡鎮楚的《石竹山房詩話論稿》中的《清代詩話考略》、張寅彭的《新訂清人詩學書目》等,使得清代詩話的清理調查與研究工作呈現出可喜的局面。
在眾多的清人詩話著作中,王瑋慶的《蕅舲詩話》尚沒有被有關專家詳細介紹和研究過。王瑋慶,乾隆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二年(1778-1842年),山東諸城人,字襲玉,號蕅唐,一作藕塘,又號藕舲。[2]嘉慶十九年(1814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1817年)改吏部主事。道光七年(1881年)升員外郎。九年(1883年)轉福建道監察御史,改署江西道。十二年(1886年)遷內閣侍讀學士。十三年(1887年)升順天府府丞,歷遷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九年(1893年)擢禮部右侍郎,改署刑部,調戶部。并先后任武會試副考官、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1893年) 卒。事見于《清史列傳》卷三十七。[3]2898-2900王氏為人正派耿直,《[咸豐] 青州府志》①咸豐九年(1859年) 刻本。稱其“多所陳奏,彈射不避當道”。其所奏,肅流弊,蘇民困,澄吏治,強治安等建議,均下部議行。[3]2898-2900是嘉、道年間極有作為的官吏。政事之余,則讀書論學。性好金石,多藏碑刻拓本,有《蕉葉山房藏書畫碑帖圖》三卷。其子錫棨,孫緒祖、希祖,曾孫維樸皆金石名家。又好作詩,有《蕅唐詩集》十四卷行世。喜評詩,有《滄浪詩話補注》和《蕅舲詩話》兩種論詩之作。《滄浪詩話補注》雖只是對《滄浪詩話》中《詩體》一篇的補注,且僅四十余條,但對研究《滄浪詩話》有不容忽視的意義。曾與《蕅唐詩集》合刻,民國王維樸又輯入《東武王氏家集》。而《蕅舲詩話》則只有稿本,未曾付梓,今藏于青島圖書館。據筆者所知,該稿本可能是《蕅舲詩話》唯一傳世的本子。各家書目未見著錄或著錄極簡,《新訂清人詩學書目》著錄的是《滄浪詩話補注》。[4]《清詩話考》著錄了《蕅舲詩話》:“王瑋慶《蕅舲詩話》一卷。精鈔稿本。青島圖書館。”[1]21僅是簡單著錄,并無提要。所以,對該書的內容和價值等方面作進一步的介紹和探究,顯然是很有必要的。
青島圖書館收藏的這本《蕅舲詩話》四孔線裝,封面題簽“蕅舲詩話”。首頁有王瑋慶像,像的右上角題“蕅唐四十小像”六字。王氏四十歲,是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則該書約成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之前。該書九十余條,共三十六頁,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以精美小楷抄寫,字跡清秀流動。前三頁有圈點。如第二條:“漢魏之詩,閎博絕塵,下至六朝,亦華茂情兼,斷不可不熟讀。而韓退之謂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舔,此論余謂過當。謝玄暉之奇章秀句,范元龍之清便宛轉,邱希范之點綴暎媚,江文通之體兼眾善,任彥昇之拓體淵雅,沈休文之縝密清怨,徐孝穆之風華綺錯,庾子山之俊逸清新,何可一舉而廢之。”其中,“六朝”二字右旁有頓點,“奇章秀句”“清便宛轉”“點綴暎媚”“體兼眾善”“拓體淵雅”“縝密清怨”“風華綺錯”“俊逸清新”字右旁有圓點。第三條:“七言古必有雄渾飛揚之勢,奇警排奡,始足以驚人,故當宗李杜。七言律必有纏綿悱惻之情,抑揚往復,始足以感人,故當法西昆。”其中,“李杜”“西昆”四字右旁頓點,“雄渾飛揚之勢”“驚人”“纏綿悱惻之情”“感人”字右旁圓點。此種圈點僅見于前三頁,后面則不見,未知何故。
《詩話》首條即引用宋代許凱的《彥周詩話》語:“詩話者,辯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者,皆所不取”,開宗明義地表達自己評論詩作的宗旨,即本著客觀公正的態度,不會以個人好惡作為評價標準。如他對韓愈所不滿的漢魏六朝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謝朓、江淹、任昉、沈約等人的詩各有其特色,不可“一舉而廢之”。除了《彥周詩話》,書中還引用了《詩品》《滄浪詩話》《古今詩話》《西清詩話》《詩式》《隨園詩話》等其他前人的成果。
《蕅舲詩話》全面體現了王瑋慶在詩歌創作方面的理論見解和經驗總結,并錄存了不少當時人物的詩作,內容豐富。在論詩方面,他認為,好詩應該兼有氣、力、情、才四個因素,而在具體寫作過程中,寫景、詞藻是必須著力的兩點。即“氣高而不怒,力勁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瞻而不疏,寫景物而不著色象,運詞藻而不落言筌。”其中“情”是他尤為看重的。《詩話》的大部分篇幅是圍繞一個“情”字展開的,這也是王氏論詩的基點。他說“人而無情,可為人乎”,是否表現真性情是王氏評價詩歌優劣的最高標準。在《詩話》中,關于情的討論,隨處可見。他說“古人論詩必本于情”,但這個情又是在遵守人倫前提下的情:“人生所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莫不有情”。“故詩言情之至者,必篤于人倫者也。”他是將情與生活、與人性聯系在一起的,那么,在實際作詩時,這個情字又如何來體現呢?王氏認為詩是由詞語組成的,這些詞語中就熔鑄了作者的情。但要體現真情,靠的并非華詞麗句和大量的引經據典,而是通過質樸的語言,反映內心真實的感受。他主張將心中之情自然地融入詩中,使語言和情感和諧地融為一體,相得益彰,“必令讀者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方為得之。”另外,融入詩中的感情應該是真誠的來自內心的,而不能無病呻吟,為文而造情。他反對抄撮前人詩句而作為己詩,他說“作詩與注書不同。注書者,所以考據古人之成跡。作詩則以抒寫自己之性靈。”又引用袁枚的詩句“天涯有客大讠令癡,錯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鐘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來進一步明確自己的觀點。在另一條中,他又說:“詩不外情景二字。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方為佳詩。作者奈何舍當前之情景而抄以往之卷軸乎?”他認為,作詩應力求平實,不能一味追求艱深晦澀,應該像白居易的樂府詩那樣,老嫗也能解才算是好詩。“凡作詩者必使鄉塾小儒閨門婦女聽其音即知其意,方足以動人,方足以感人。”正是基于對情的這種認識,王氏把詩品與人品聯系在一起,他說:“詩本于性情,故誦其詩即可知其人。詩能明爽者,其人必正直。詩能豪放者,其人必曠達。詩能淡遠者,其人必高雅。詩能俊逸者,其人必秀麗。”王氏的這種論調雖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失之偏頗。詩品與人品,并不能完全一致的。關于這點,前人已有論及,此不贅述。
不過,王氏對真性情的體認還是有現實依據的。他認為無論是什么人,只要發乎真情,就有可能作出好詩。《詩話》中記載了他家鄉一個牧童作詩的故事:這個牧童如果“目前無真風景,便不能措一字”。但當他看到好風景時,就會有感而發。曾于雨后見老農筑場,怨天連雨,遂成一句“農翁筑圃嫌朝雨”,然后,卻數日不能對。一天在河邊看到釣魚者抱怨因為沒有風而導致魚不上鉤,這個牧童靈感就來了,遂對上了下句“漁子垂綸愛晚風”。王氏對這兩句詩極為贊賞,他說:“真能曲體人情物理之至矣”。可見他對自然、對真情流露的推崇。“詩貴自然,不可矯揉造作。鼓刀為雄,倚門為艷。”真實地表現生活,才是作詩的最高標準。
王氏對情的提倡與他本人的性情和經歷是分不開的。他自己就是個深情之人。《詩話》中記載了他與亡妻單茝樓(號紉香,年二十五亡)的生活往事,飽含深情:“居室曰碧香閣,日與余攤書其中,香篆輕裊,花光滿院,墻外垂碧柳三株,綽約自紗窗窺人。紉香有句云‘綠窗紗映三株樹,繡閣香薰兩架書’。”同時也錄存了他為妻子寫的數首悼亡詩,“余赴鄉闈,繡蟾宮折桂佩囊以寄余,勸余保重讀書,所以望余者至矣。余悼亡詩故云‘蟾宮丹桂繡囊工,爭奈蓬山隔萬重。對臥牛衣聽報罷,文章何處哭秋風。’”夫婦情深,令人不忍卒讀。在憶妻事之后,引袁枚《銘金纖纖墓》“女子有三不祥:有才者不祥,無貌者不祥,有才貌而所適與相當者猶不祥。”王氏又加上自己所認為的又一“大不祥:幽靜賢淑,天更使之不永于世”,這顯然是針對單氏早亡有感而發的。
雖然王氏一力主情,但卻并不濫情,而是將情放在理的限制之下。“理賦于天,情具于人,善作詩者止乎理而不涉乎理,發乎情而不過乎情。”體現了封建士大夫的中庸之道。
與主張“情”一致,王氏又強調作詩時要真而不落俗套。他說:“詩之最忌者一庸字。詩之至要者,一真字。”“凡作七古必須天馬行空,長鯨掣海,不可落一凡字。”他強調真切體驗,而不可妄加臆斷:“地不親到,物不親見,說來便多錯訛。”蘇軾詩有“試掃北臺看馬耳”句,王氏認為馬耳是地名,指南山,而注者所以為的野菜名是錯誤的。又宋荔裳有《憶故鄉銀刀》詩,銀刀,王士禛說“一名八帶魚”。王瑋慶則認為“八帶魚身小而團,四圍如帶。二物大不相侔,覽之令人失笑。”蘇詩注者和王士禛都是因為沒有經過實際考察,只是出于臆斷而致誤,徒留笑柄。
作詩不能憑空臆斷,而取材則不必定是真事,只要材料可以入詩,皆可拿來使用。“七夕渡河之說固屬荒唐,然此等詩料斷不可少,何必膠柱而辨其真偽乎?”又體現了王氏詩歌創作方面的靈活性。
取材上要不拘泥,在作詩的方法上就更要融會貫通。他特別提到用典,“詩套前人作者間有,然須運化靈通,不可拘于跡象也。”套用前人之句,應該不著痕跡,轉換靈活,而不能生搬硬套。王氏認為,在用典方面,杜甫詩可謂典范,其詩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句,“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功,不知乃用事也。”其實這是用的《禰衡傳》和《漢武故事》里的兩個典故。王氏認為,用典的最高境界應該是“如絮風捕影”,讓人無跡可尋,使人不覺得是在用典。杜詩又有“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句,用的是梁蕭文奐畫扇故事,初讀似沒有用典,實則因為杜詩將典故完美地融入到詩中了。
王氏又認識到詩歌特色跟地域環境的關系。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群,其詩作特色是不一樣的。“江北之風土純而厚,故其人為詩多深思沉郁,而或失之粗。江南之風土清而秀,故其人為詩多綺麗新刻,而或失之薄。”“山左閨秀不及江南,蓋南方之山川氣多清淑,北方之山川氣多粗豪也。即偶有一二成章者,亦多隱沒不章。”與此相應,不同家庭環境中的人,其詩作也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歐陽修所說“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于所處,如‘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此富人詩也。‘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此貧人詩也”。這也是王氏的看法。
《詩話》中對詩歌的體裁也有所論及。“詩有興、比、賦三體,一章之中先后互異,始有虛實變化之妙。”“三代而上,雜體互出。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覆,寓憂思輾轉之情。雙聲疊韻壯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奇出不窮。”“艷體詩自徐孝穆《玉臺新詠》后有西昆體,有香奩體”。既追溯了詩體的發展演變源流,又羅列了詩歌的不同體裁。書中又收錄了幾首在體裁方面比較有特色的詩作,如高梅仙的《閨怨》詩,韻限溪、西、雞、齊、啼,內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兩、雙、半、丈、尺等字。又有幾首詩句中隱妓名的詩,則純屬文字游戲之類。
王氏在《詩話》中除了表達論詩觀點外,還經常透露出自己對某事某人的好惡傾向及自己作詩的特點。比如對于袁枚和王士禛,《詩話》中多次論及。他認同袁枚對王士禛“一代正宗才力薄”的評價,同時也肯定袁枚才力雖富,但“終不可為一代正宗”的事實。“近來譏之者曰風流宗主,名教罪人,亦是定論。”雖然承認袁枚有不足之處,但他對袁枚,實際是持贊賞態度的。袁枚主張性靈說,王氏在《詩話》中多次提到,他自己也儼然以性靈派自居。而對王士禛,則更多譏刺,《詩話》中提到王士禛,多是作為反面教材出現的,而很少正面贊揚,如前所舉宋琬《憶故鄉銀刀》詩,王士禛將銀刀釋為八帶魚。王瑋慶說“二物大不相侔,覽之令人失笑。”在論及套用前人詩句問題時,分別列出王士禛和袁枚兩人對白居易詩句的套用:白居易原句“襟上杭州舊酒痕”,王士禛易以‘衣上明湖舊酒痕’,袁枚作“班班衣上香痕滿,都是揚州酒未消”。王瑋慶認為王士禛的套用太板滯,而袁枚的運用則靈活多了。后論潘岳《悼亡》詩,稱“字字神傷,不忍卒讀。若王新城二十余章,皆泛填虛詞耳。”這些都明確表達了他對袁枚的贊賞和對王士禛的貶斥。又比如論及前人之詩時,王氏會明確表達出自己的取舍“韓詩有‘羞澀佯牽伴’,前人以謂摹盡小女子情態。余尤喜孟浩然《春怨詩》云‘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恰是女子待嫁景象,恰是待嫁思春景象,恰是思春而非淫邪景象”。再如,王氏本人喜愛的詩歌風格是綺麗纖細一路,所以,在《詩話》中,他也明確地表露“家樸齋方伯公所著《破夢齋詩草》,浩瀚雄渾,多類滄溟。余獨愛其《雪梅十詠》,用唐伯虎花月體,綺麗新奇,巧不傷雅”。《破夢齋詩草》整體風格是波瀾壯闊,而王氏卻獨喜其中的風花雪月,巧麗之作。又《詩話》中記載了女子潘素心、金蓉、陳長生、錢孟鋁田的唱和詩,王氏說“喜其詞綺麗芊綿,俱錄于此”。他又偏好艷體詩,雖囿于身份禮法,“不敢多擬”,但心實向往之,并在《詩話》中記錄了自己作的艷體詩《春緒》一律。前人多不滿西昆體的狹隘華艷,而王氏卻將之與李杜并舉,稱七言古當宗李杜,七言律則當法西昆,將西昆體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這是與他自己的喜好相一致的。可見他也并不能絕對地本著客觀公正的態度來論詩的。
或許是天性使然,或許是妻子早亡,王氏對有才女子甚是看重和憐惜。他在《詩話》中發表了很多議論、見解都與此有關:“富貴有命,死生有命,讀書亦有命。方先室未亡之時,互相唱酬以為樂。因廣購名人詩集,方欲深求其蘊,未幾而花落煙硝,卷帙飄零。”“李義山詩云‘古來才命兩相妨’,丈夫與女子皆然。隨園女弟子二十余人,非早夭即早寡,才命全者只數人而已。造物妒才,理或有之。然余謂既妒之,何為生之?故嘗有句云‘豈是懷才即見妒,此才未有何必生’。豈憤激之辭哉!”這些顯然還是為悼亡而發的。又有不少對于女子之才的議論:“女子有才者,所遇必不偶”“婦人有貌無才,尤花之有色無香也。終是一大憾,故婦人所貴者,一曰德,二曰才,三曰貌。”“擇妻如擇友。故得一佳偶,朝夕談論,不惟有益于詩詞,并且有裨于禮義,如獲良友焉。若娶一目不識丁者,粗言俚語,如對一俗友,豈能終日”。“婦女出于世家,多嫻禮義,蓋其所見所聞者多詩書之澤,廉恥之行也”。“嫁女擇富家,人情恒然。近來素嫻詩書之女亦多嫁于商賈,實為憾事”。“魚玄機《寄鄰女》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此亦勸人當擇佳婿,勿徒貪無價之寶乎”。“卓王孫系臨邛巨富,為女擇婿必亦擇一富家翁,始相匹配。則文君始嫁之夫定是程鄭之流,其富與卓氏等者。乃相如琴心一挑,而文君遽舍巨萬之富而隨四壁徒立之貧士而奔。此豈見金夫不有躬者所能哉。”對身世飄零之才女的同情,在封建時代體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開明豁達。
除了評論前人詩作,《詩話》中還記載了王氏自己的一些經歷及當時的一些事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如“余年十八肄業濼源書院,時中丞鐵冶亭愛才育士,偶有吟詠,必令諸生和”。“詩有讖語,余庚午春夢賦悼花長歌,起四句云‘東風一夜珠簾透,煙愁露泫紅消瘦。階下殘花覆草深,匆匆人面倏非舊’。未幾果有悼亡之痛”。“余入泮年已十八,又七載喪偶,始得領鄉薦”。“庚午,余在濟南”。這些記載,對于了解王氏的生平經歷有所助益。又如“劉金門先生督學山左,余初出試即蒙其賞拔。嘗游大明湖,得句云‘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鐵中丞冶亭書作對聯,懸于鐵公祠”。“柳生敬亭以評話聞公卿。入都時邀至接踵。一日過石林許曰:薄技必得諸君子贈言以不朽。實菴贈以《沁園春》詞二闕……合肥尚書顧安叔學士皆和之,敬亭名由此增重”。“明崇禎間石柱女官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策楊嗣昌邵捷春必敗。御制詩旌之云‘從此凌煙高閣上,功臣先畫美人圖’”。這些歷史事實的記載,都有較強的史料價值。
總之,《蕅舲詩話》既是王瑋慶的論詩之作,也是清人詩話重要的一部分。近日,《山東文獻集成》第三輯將該書影印出版,終使其得以示人,惠及后之研讀者。無論是該書,還是清詩話,都有待我們做更多更深探討和研究。
[1] 蔣寅.清詩話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5.
[2]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1118.
[3] 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7.
[4] 張寅彭.新訂清人詩學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