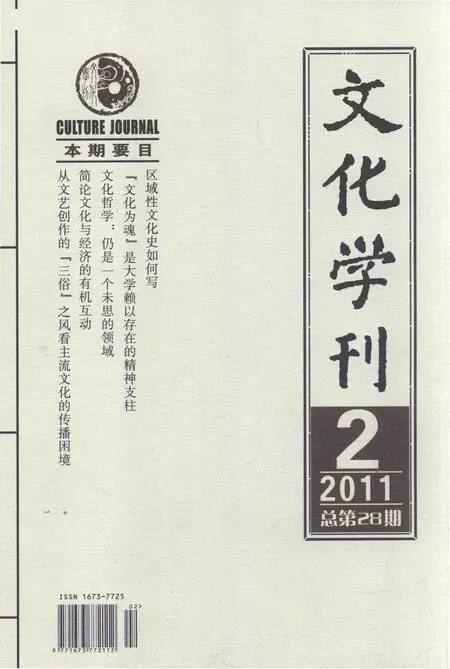地域文化史同樣是多元薈萃、絢爛悠長的歷史畫卷
——讀《遼寧文化通史》
趙世瑜
(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 100871)
地域文化史同樣是多元薈萃、絢爛悠長的歷史畫卷
——讀《遼寧文化通史》
趙世瑜
(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 100871)
在中國眾多區域文化之中,遼寧似乎并不是人們眼中的重點。但是,這樣的觀感即使不是因為“勢利”,也是因為評判標準上的偏頗。首先,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這些文化也都對人類具有獨特的價值;其次,華夏中心觀或者漢族中心觀將以往處于“邊緣”的“四夷”過于貶低,他們甚至忘了,北京長期以來也不過是長城腳下的邊塞,只是拜了從東北來的民族之所賜,才成為了中國王朝史上的都城。當然,這種現狀的造成,也是對這一地區的研究相對薄弱所致,而曲彥斌先生作為總主編、集多位專家學者的心血編寫而成的九卷本《遼寧文化通史》的問世,則極大地改變了這種現狀。
地域文化史;遼寧;評判標準
說到遼寧,一般人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一些什么印象呢?趙本山的二人轉和小品?被稱為“闖關東”的大移民浪潮?“胡子”、馬隊或者張大帥?滿洲入關前的金戈鐵馬?甚至還有屈辱的“滿洲國”的歷史?一個地處邊塞以外的冰天雪地的地域,具有怎樣的文化發展歷程?究竟是哪些方面反映出了遼寧文化的真正品格?
在中國眾多區域文化之中,遼寧似乎并不是人們眼中的重點。陜西的關中文化頗受青睞,因為那里是周、秦、漢、唐的都城所在,所謂“雄漢盛唐”,其文化成就自然為人們津津樂道;山西的三晉文化也為人稱道,因為那里是上古圣王堯、舜、禹的活動之地,華夏文明從那里起源;不用說,江南文化更是重中之重,“江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且不說六朝古都,就是明清時期的三鼎甲,也是江南占優;即使是開發比較晚的廣東文化,亦由于在近現代史上的特殊位置,特別是近30年來的發展,不由得不讓人另眼相看。
但是,這樣的觀感即使不是因為“勢利”,也是因為評判標準上的偏頗。首先,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這些文化也都對人類具有獨特的價值;其次,華夏中心觀或者漢族中心觀將以往處于“邊緣”的“四夷”過于貶低,他們甚至忘了,北京長期以來也不過是長城腳下的邊塞,只是拜了從東北來的民族之所賜,才成為了中國王朝史上的都城。當然,這種現狀的造成,也是對這一地區的研究相對薄弱所致,而由曲彥斌先生作為總主編、集多位專家學者的心血編寫而成的九卷本《遼寧文化通史》的問世,則極大地改變了這種現狀。
一般來說,文化是與人密切相連的。有了人就有了人類的創造,無論是創造的過程、方式還是結果,就構成了所謂文化。但說到遼寧的文化,總會讓我聯想到那個人類產生之前的古老世界,這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電影《侏羅紀公園》之類讓我把人與地質年代聯系起來的緣故。我對自然科學完全沒有發言權,但也關注那些科學新發現。當年在遼西地區,曾發現了1.3億年前的早期被子植物“遼寧古果”,比當時所知的同類植物起源時間提前了1500萬年。科學家認為,這種植物的直系祖先有可能是水生的種子蕨類,與以前的認識完全不同。同樣在這一地區發現的“原始熱河鳥”,其骨骼特征與奔龍類恐龍類似,為鳥類的起源與恐龍的關系提出了新的證據。這一地區的豐富化石遺存揭示了一個生意盎然的遠古世界,而這個世界曾對未來的人類世界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盡管人類長期以來并不知道這一點。
我們現在已經不能輕易地用單線進化論的觀點來假設這一地區生物的起源與人類史前文化的關系,但遼寧地區的史前文化的確呈現出非常獨特的面貌。正如本書第2卷所揭示的,在查海等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龍形堆石、陶器上的龍形圖案,牛河梁女神廟的泥塑龍和玉雕龍,說明當時存在一個非常清晰和普遍的龍的崇拜。雖然可以確定它與原始宗教有直接關系,但我們并不知道它與怎樣的一個區域文化背景有關聯,我們也還不清楚它與中原龍崇拜是否具有或具有怎樣的淵源關系。考慮到趙寶溝文化“四靈圖”中的鳳、鹿、豬的形象,可能與當地的古動物遺存有密切的關系,我們或許也可以大膽假設,原始先民所能見到的古動物遺存,除了可以與當時生活中所能見到的動物直接對應的動物——如鳥類、鹿、熊、豬等以外,還有一些他們無法識別的遠古動物,從而構想出龍的形象,并賦予其超出其他動物的神秘意義。
從紅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廟到青銅時代的夏家店遺址,體現了遼河文明的早期形態。紅山玉文化除了顯示權力象征以外,它與牛河梁女神廟顯示出的上古祭祀一起,共同展現了早期的禮儀圖像。玉可以作為禮器,在各種與祭祀有關的場合使用;而牛河梁的女神廟、圓形祭壇和積石冢則是祭祀的場所。盡管我們未必一定將其與中原傳世文獻中的上古禮儀相疊合,但這些禮儀器物與場所仍然彰顯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重要意義。“戎”的一面或許可以由夏家店文化遺址中分布密度很大的石城堡得到證明。這些城堡包括城墻、城門、城壕、馬面等部件,明確體現了防御功能。屬于夏家店以及以后時期的陶器和青銅器不僅同樣大量作為禮器存在,也有鮮明的北方特征。特別重要的是,本書第2卷告訴我們,在東亞世界,存在一個玉玦文化圈,而遼西可能正是它的起源地。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里是與中原和南方文化類型有異卻可等量齊觀的另一文明源地。
正如本書第2卷的作者正確地指出的,進入周秦時代,遼寧地區的歷史就在以長城東部為景觀標志的地理舞臺上展開。本書自第3卷到第9卷,即描述了這一豐富的文化發展歷程。
在本書第3卷中,作者通過大量考古學成果和歷史地理學的考索,揭示了秦漢時期以“漢郡文化”逐漸取代“方國文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又可以西漢東北四郡之設及其發展為代表。從大量考古發現中,我們可以看到這里的制度、物質生活與習俗都日益多地受到長城以內文化的影響,日益形成一個“趨同漢制”的走向。但是,正如我們所知,中原政權的制度與文化向邊疆地區的延伸是一個逐漸的、甚至多有反復的過程,郡縣之設起初只是大海中的幾個孤島;我們所發現的許多考古證據和文獻記載不過是這幾個“孤島文化”的集中反映,它們還不能代表整個大海的全貌。在這些郡縣的城墻之外,甚至在官署的墻外,仍生活著大量語言、風俗等文化各異的人群,他們多數還不是中央政權的編戶齊民。恰恰關于這些地區的族群,我們還缺乏更豐富的歷史證據。對兩漢時期這一地區夫余、高句麗、烏桓、鮮卑的社會文化發展道路,我們還不能只停留在中原王朝文獻的只言片語的程度上去把握。
本書第4卷所描述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遼寧地區社會文化發展歷程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階段。事實上,我個人并不十分情愿用“魏晉南北朝隋唐”這樣一個中原王朝更迭的時段名稱來概括這一時期的東北或者遼寧,因為雖然這一地區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往來日趨頻繁,但并非全部時間和整個地區都是中原政權之下的地方政權,與南朝更沒有直接的關系。既然是文化史,我們當然是以文化系統之間的關系而非政治系統作為原則。相反,以鮮卑為代表的本地族群的強盛,隨著他們進入塞內并建立強大的政權,給北方中原文化造成巨大的影響。甚至此一時期中原漢人較多地進入遼寧地區,不僅是中原文化向外擴展的結果,也是鮮卑等族進入中原、在長城內外形成統一的族群文化版圖的結果。
這一結果導致了一個人們往往回避討論的歷史連續性。在中原王朝中心論的影響下,傳統的歷史敘事往往以王朝的更迭為歷史的斷裂;在漢人中心論的影響下,這一敘事傳統又往往以邊疆族群入主中原為歷史的斷裂。但是,假如從邊疆族群的角度出發,在鮮卑等族入主中原之后,唐朝的“安史之亂”爆發于東北邊塞并不是偶然的,緊接著就是唐末契丹的興起與南進,直至女真在華北建立統治,這恰恰體現了一種歷史的連續性。這段歷史不僅是遼寧的歷史,也不僅是東北的歷史,而是把東北和華北連接成為一個整體的歷史。而過去,這個整體是被長城障塞隔斷的。今天的遼寧,正是這個整體的空間連接點。
本書第5卷是講契丹文化與女真文化的內容。如前所述,這應該是這幅畫卷中最輝煌絢爛的華彩部分了。這一階段的歷史,不僅是時段上的相近,在區域文化發展的意義上,也可以與中原王朝史上的唐朝相提并論。但是,遼代文化并不等于契丹文化,金代文化也不等于女真文化。遼代和金代都是時間的概念,它們必須涵蓋在這一時段中存在的一切文化,那恐怕就不只是契丹和女真文化的問題了,因為在遼統治區和金統治區內生活的絕不只是契丹人和女真人。當然,這也體現了遼金史研究界這些年來視野上的一些缺失,即將遼金史視為以契丹和女真為研究對象的歷史,這就把這一歷史時段的意義大大局限了。最為重要的是,我們知道契丹和女真文化并不僅呈現于今天的遼寧,因此所描述的內容,不能是泛泛的、在整個遼金統治區內的契丹、女真文化,而必須要落腳到今天的遼寧。或者說,我們應在這卷看到的,是在遼金時期,遼寧這個地區的文化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變化。遼地之得名,與遼之國名的關系,并不是可以隨意忽略的。這些都恰恰說明,遼金時期的遼寧史,以至遼金時期的北中國史,是大有可為的。
本書第6卷將元明兩代相連,是注重了元明二者間的連續性,而非以往強調的差異。與以往不同的是,從遼金以降,關外遼東地區與關內屬于同一個行政版圖,這種狀況至元不變。到明代,雖然漢人成為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并在這里設立遼東行都司,隸山東都司,而非州縣,但畢竟保持著中央的直接控轄。與此后的清相比,雖然盛京地區與關內仍在同一版圖內,但因其龍興之地的特殊地位,反而在近300年里成為不可隨意往來的禁地,從而一時失去了發展的活力。這也是為什么人數有限、變化無常而又頗具悲劇味道的“流人文化”也在第7卷中占有較大篇幅的原因所在。
第6卷的作者在講述明代遼東文化時,十分注重衛所體制的影響,這是非常重要的。在這里,學校、書院等教育機構,都是在衛所體制下設立或在其支持下創辦的。雖然明代在全國各地遍設衛所,使其與州縣體制共同構成明帝國的基本管理體系,但在遼東,衛所代行了內地州縣的職能,使其成為研究衛所軍戶制度之行政實踐的極好地域。因此,本卷較大篇幅描述的寺廟與信仰,特別是將真武廟與關帝廟及其信仰與衛所的設置及軍士的信仰生活聯系起來,是非常正確的解釋路徑。這不由使我們聯想到以往頗為人樂道的廣寧寺碑和奴兒干都司之設,雖然不在今天的遼寧,但同樣是明初帝國經略東北邊陲的產物。為什么永樂時派遣宦官亦失哈巡視奴兒干都司時,修建廣寧寺并立碑紀事,正是前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與祀事相輔相成的例證——寺廟并不僅像今人理解的那樣只表現出宗教信仰,而是帝國對某一地區實現有效控制的象征:軍事征服只是第一步,但卻不能總是“馬上治之”;所謂文治武功,寺廟就代表了文治,代表了某種禮儀秩序的確立。今人研究寺廟者,多不及此,故無法理解其中的真諦。
清代的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明代的遼東邊鎮一變而成盛京,到清末開禁、大量關內人口涌入后則發生更劇烈的社會變革。正如第6卷一樣,第7卷所涉及的遼寧文化應該置于內務府體制下的旗人社會這個框架中去理解,主要的篇幅不應給予少數幾次皇帝的東巡謁陵和作為流人的漢人士紳,這時的主流是生活在這里的旗人和部分民人。許多檔案和族譜沒有能夠得到利用,不能不說是件憾事。近代遼寧社會至少有三件影響巨大的事,都對本土文化產生了沖擊,同時也影響到全國、甚至東北亞世界:一是闖關東,二是“滿洲國”,三是解放軍出關及土改。這三個事件給20世紀以后的遼寧和東北文化帶來了重要特征,即移民文化、殖民地文化和老解放區文化,在本書第8卷中,作者對第二、三個特征及其相關文化現象作了較充分的展示,但對第一個特征卻幾乎付諸闕如。
我本人在當代文化史領域是個門外漢,無法對本書第9卷作出很恰當的評述,而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往往是難度很大的事,因此對作者的勇氣表示由衷的欽佩。事實上,人類學者、民俗學者等等的研究對象也都是當代文化,他們的文化書寫與歷史學者的書寫會有怎樣的不同?我們可以期待。
非常感謝本書的總主編和作者,使我不僅通過閱讀全書增長了許多見聞,而且啟發我思考了許多以前很少想過的問題,所謂讀書使人明智,應該就是包含了這兩層含義吧。當然,有許多問題我還沒有想透,更沒有經過實證,因此許多想法都是假設而已。上面的讀書體會所提出的問題,就讓我和作者、讀者們一起繼續思考和研究吧!
[責任編輯:董麗娟]
K29
A
1673-7725(2011)02-0007-04
2011-02-20
趙世瑜(1959-),男,四川成都人,教授,主要從事區域社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