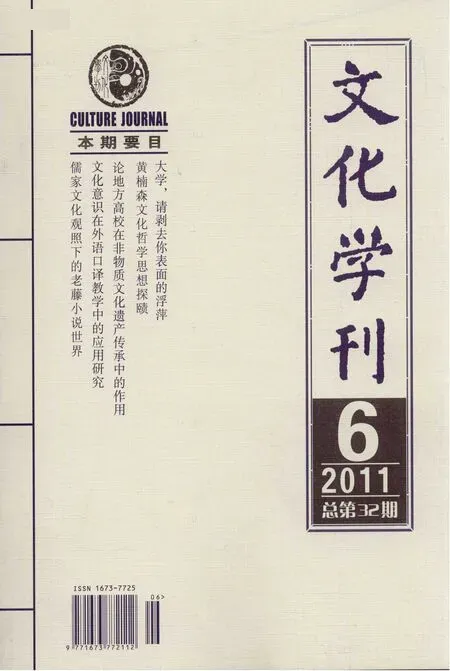試述古典批評當代化的可能性
范小娟
(貴州大學人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眾所周知,古典批評普遍運用直觀感性的思維方式與言說方式,使具體的批評帶有濃重的詩性氣質,這集中表現為古典批評家們在具體批評中對“言外之意”的推崇與實踐。許多學者由此認為古典批評的這一特點會使許多重要的范疇,如風骨、神韻、氣象等缺乏明確定義,出現對其內涵無法得到確切剖析和界定的問題,但筆者認為,這種言說方式的模糊性及不確定性正是古典批評煥發新的生命力的前提所在,在學術界處處高喊古典批評現代化、當代化的今天,許多人單一的認為古典批評走向當代的唯一途徑就是運用西方理論來解讀古典批評,他們沒有看到古典批評家們對“言外之意”的推崇就是實現古典批評當代化的重要路徑。
“言外之意”強調運用最少的語言表達出最深刻、最豐富的多角度多層次的內涵和意蘊,對作品的批評之言所表達的意是不確定的,其言帶有強烈的模糊性與多義性,這正是古典批評具有的獨特的審美魅力,而古典批評家對“言外之意”的推崇實際上最早是從道家文化中生發開來的,“道家文化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虛靜其心,法天貴真,言外之意”,[1]從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開始,對“言外之意”的重視與強調在整個中國古典批評史中形成了一條粗大的紅線,影響巨大并貫穿始終。繼老子后,莊子在《天道》中說“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明確的提出“得意忘言”這一重要命題,而后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鐘嶸在《詩品》中“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的表達也是對這一命題的發展,到晚唐的司空圖認為創作的最高境界在于“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歐陽修也有類似的看法:“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到嚴羽更明確提出了“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觀點,而清人王士禛的“神韻”說得也是對這一觀點的繼續發展。顯然,“言外之意成為創作中的一種自覺追求,并在理論上不斷得到充實”,[2]古典批評家們對文學的要求與哲學的最高境界趨同一致,諸如陶淵明所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只是去梳理“言外之意”這一批評觀的來龍去脈,更值得提出的問題是,古典批評對“言外之意、象外之致、文外之旨”的強調本身說明古典批評帶有強烈的開放性、未來性,這也是古典批評能夠走向現代、實現當代化的重要條件。傳統批評的許多范疇堪稱經典,經典雖意味著難以超越的標竿和榜樣,但并非意味著它們是封閉、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如“意境”這一重要的批評范疇,其內涵就不可能是生而固定的,而是自其萌芽之初其意義在歷代都得到了不同層次的拓展,先秦時“意”與“境”是分開的,具有不同的含義,“意”作為一個文論范疇并未具有美學上的情趣、韻味的意義,而最早將“意”與“境”連起來用的是在唐代詩人王昌齡的《詩格》中,他認為詩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這里的意境雖與后世審美范疇的意境有諸多聯系,但也不等同于后來的意境,而后意境這一范疇的意義在每一時代都得到新的發展與挖掘,直至其審美意義完全成熟,到王國維先生那里成其集大成者,但意境的發展并非到這里就停滯不前了,到近現代仍然有許多文人學者運用新的角度、方法不斷對意境這一傳統批評范疇做出新的不同層次的挖掘與闡釋,同時,意境這一傳統批評范疇也在不斷地實現其自身的當代化歷程。
在具體的批評方法上,由于傳統批評對“言外之意”的言說方式的推崇,批評家們通常運用的是感悟式批評,感悟式批評雖然存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缺少科學精神和方法”[3]的問題,但它強調運用感悟與直覺的審美方式,在潛心品嘗的過程中頓悟式的直接把握作品的高妙境界,這種批評“在吉光片羽的即興評說中往往閃現靈思,妙語驚人,使人茅塞頓開,受益匪淺”,[4]鐘嶸的《詩品》是第一部詩話作品,他品詩論詩,用的就是這種直覺式思維方法,“在直觀感悟中,心與物直接對話而無須以邏輯推理作中介”,[5]他在評價范云、丘遲時說:“范詩輕便婉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看這樣的詩,會讓人“有一種妙不可言的領悟,感受到甚至比定性分析更清晰的內容”。[6]一方面,這種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直觀感悟式批評也為后來欣賞者的解讀保留和提供了空間,在《世說新語》中對作家作品的批評就可以充分的說明這一點,在《容止》篇中對嵇康之子的評價“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對王恭形貌的描述是“濯濯如春月柳”,可見,這種以物喻人的批評常常只用一字或幾字就能全然將人物的內在素質與外在形貌描述殆盡,諸如松、鶴、山、龍、柳等,一方面這些極簡的詞語“能準確概括出人物內在品格與精神風貌的某些特點,傳達出許多朦朧微妙的審美感受和信息”,[7]另一方面,這樣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表述方式又充滿了難以說盡的多義性和模糊性,它保留了進一步批評的可開發性、可闡釋性,給欣賞者留下了諸多想象的意味,更給人留下只可意會、不可言詮的回味無窮的審美享受與愉悅。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批評方式很有可能造成最初的批評者與后來的批評者完全不同的理解和闡釋,后來的批評者可以對最初的批評進行二次、多次的挖掘,從而實現與古典批評的對話和溝通,這類似于西方著名的接受美學的觀點,不管怎樣,每一時代的理解者必然會受到他所處時代各種因素的影響與限制,通過對傳統批評的重新解讀,甚至“解構”,傳統批評也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力,產生新的多重理解的可能性,用西方流行的觀點,古典批評由此也獲得了新的“陌生性”,諸如哈羅德·布魯姆所言,“一部作品能夠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性標志是某種陌生性”,[8]因為“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9]這里雖是講文學作品,但同樣適用于文學批評,文學批評的獨特就在于這種陌生性,傳統批評雖被奉為經典,但不可能是封閉的,它只有不斷地被賦予新的審美素質,才具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最終,不同時代的理解者產生基于與其時代相統一的不同的新的批評與闡釋,傳統批評也就實現了相對于理解者所處時代的“當代性”,當然,我們這個時代的批評者同樣可以針對傳統批評,運用不同的方法視角作出與這一時代相統一的與前人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么,古典批評也就實現了我們這一時代的當代化,仍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批評的當代化并不會在今天就終結或是停滯不前,由于古典批評言說方式的開放性,它們會隨同時代的變遷而煥發新的生命力。簡而言之,由于“其理論文本面向未來并對未來有所期待,期待在自我革新中與時俱進”,[10]那么每一時代的批評者都可能根據其社會歷史環境的不同對傳統批評有新的闡釋和挖掘。
實際上,當代批評的根本價值及其健康的發展趨勢是在于建構一個通過古今對話、中西溝通而實現的充滿多元化、包容化的批評體系,“批評是對話,是關系平等的作家與批評家兩種聲音的匯合”,[11]其實,不光是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對話,更有可能是中國批評者與西方批評者、古典批評者與現當代批評者之間的對話,對于后者,就存在一個如何跨越時間障礙的問題,基于這一點,古典批評的當代化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這是進行古今對話的基礎和前提,而古典批評在言說方式上對“言外之意”的推崇恰恰就為實現古典批評的當代化提供了重要條件,也為實現古典批評的當代化提供了可能。
[1] [2] [5] 李建中.中國文學批評史[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5.
[3]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3.
[4] 蔣述卓.文學批評教程[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215.
[6] 曹旭.詩品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6.
[7] 熊月華.世說新語品評人物的審美特征及影響[J] .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96,(1).
[8] 哈德羅·布魯姆.西方正典[M] .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3.
[9] [意] 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M] .黃燦然,李桂蜜,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3.
[10] 徐中玉.中國文論的我與他——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第二十七輯)[M] .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9.3.
[11] [法] 托多洛夫.批評的批評:教育小說[M] .王東亮,王晨陽,譯.北京:三聯書屋,1988.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