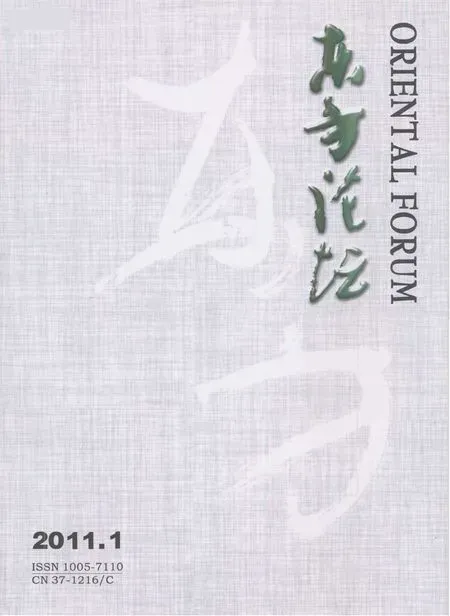“自然觀”與生態困境的道德哲學演繹
牛慶燕
“自然觀”與生態困境的道德哲學演繹
牛慶燕
(南京林業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210037)
生態難題日益成為威脅整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問題。以系統論思維方式全面考察人類“自然觀”的生態演化歷程,歷經遠古文明時期“自然為人立法”、近代工業文明時期“人為自然立法”,應當尋歸生態文明時期有機契合的系統“生態自然觀”,是謂“人為自身立法”。其中,現代“生態自然觀”的確立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在現時代的內在要求,為緩解生態危機并破解生態難題提供了重要的哲學依據,應當成為綠色文明時代的倫理共識和文明期待。
自然觀;生態困境;道德哲學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生態難題日益成為威脅整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的全球性問題,直面生態威脅,人類必須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的“自然觀”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它在思想觀念深層影響著人們的生態道德認知,沖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歷經遠古文明時期的本體論“自然觀”——“自然為人立法”、近代文明時期的認識論和工具論“自然觀”——“人為自然立法”,應當尋歸生態文明時期“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有機契合的系統“生態自然觀”,是謂“人為自身立法”。其中,現代生態自然觀的確立為緩解生態危機并破解生態難題提供了重要的哲學依據。
系統考察人類“自然觀”的生態演化歷程,以系統思維方式嘗試探究走出生態困境的有效路徑,對于全面完整地探析生態困境、積極推進“兩型”社會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自然為人立法”
早在遠古時期,隨著人類意識逐漸趨向成熟,從原始神話、自然宗教和早期圖騰崇拜中逐漸分化出屬于人類自身的世界觀和自然觀,把自然本身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尋求自然和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邏輯。古希臘所強調的宇宙整體秩序性以及西方中世紀神權統治時期的上帝預置萬物理論,都肯定了人類與自然、個人與共同體的一體相關、混沌未分,屬于“天人合一”的本體論“自然觀”。懾于自然的威力,當早期先民運用自身的力量無法與自然相對抗時,便不得不順從自然、順天而動,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實際上在沒有人類明確的自我意識關照下是一體未分的融合狀態,是謂“自然為人立法”。
(一)主客一體的原始本體思維
遠古時代,人類整體處于蒙昧和未開化的狀態,人類的主體意識在尚未完全呈現出來時,人只是作為自在和自然狀態的主體而存在,并且不能完整辨別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人類源于自然、依賴自然,人與自然是原始直接、混沌朦朧的統一關系,這種主客一體的原始本體思維模式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注入了更多神秘一體的感性因子。建基于自然本體論之上的對自然與生俱來的膜拜信念,通過原始宗教和“圖騰”神物的締造,以一種發自生命深層的對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表達著遠古先民的自然情懷。如此,遠古先民能夠“克服”人類主體意識和主體力量的有限性,化解人類在強大冷漠的自然面前無助,從而在潛在和自發的層面上直面人與自然的沖突和矛盾,維系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
遠古文明時期主客混一的原始本體思維把自然看作是具有生命和靈性的有機體,這是一種潛在的有機論生態倫理思想。
(二)樸素的“天人合一”有機論自然觀
“天人合一”的自然觀,是東方傳統文化資源的基礎性命題。在遠古文明的發展進程中,人類在面向自然的生產實踐活動中逐漸增強著對自然的體認過程。人類“意識”與“自我意識”的萌發開始區分作為認識與實踐對象的客體自然與主體人類,但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之上尊重自然和歸依自然卻作為一種深層的價值理念印刻在遠古先民的思想深處,在主客一體的本體思維的激發下,逐步確立起樸素直觀的“天人合一”有機論自然觀。
“天”是至高的權威和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人類在具體的生態實踐中要“懼天”、“畏天命”,進而在“尊天命”的基礎上順天而動,遵循自然規律,以確保農業生產和生活的穩定。“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具備不可替代的生態價值,是遠古文明中主客一體的原始本體思維的延伸,這不僅是一個哲學存在論的命題。更是價值論的命題,它認為自然是一個統一性的有機整體生命系統,肯定自然存在的價值及其自然規律對人類實踐活動的制約調節作用,并且認為人作為自然中具有能動意識的生靈,理應關愛自然、尊重自然的價值,擴展道德關懷的范圍。
“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在傳統儒家文化中作為一種世界觀、宇宙觀和普遍的思維方式,體現著人生最高的精神追求境界。作為儒家生態智慧的精髓,彰顯著和諧的人生態度,不僅是東方傳統自然觀的樸素唯物辯證思想展現,也是“天人合一”形上精神旨歸的理念體現。其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精神旨歸、“民胞物與”的文化關懷與“取物限量,取物以時”的道德規范,彰顯著天人合其德、天人合其性、人之性與天之性合其類的宇宙情懷。“天人合一”的古樸有機自然觀在道家生態思想中主要體現為“道法自然”。“道”作為道家思想體系的核心范疇和主導理念,是宇宙生成論和宇宙本體論的辯證統一,“道”是萬物的始基、本源和萬有之根,是宇宙萬物運動變化的客觀規律,“道”是向“自然”的理念認同與價值合一,“自然”是“道”的皈依,“道”是“自然”的彰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佛教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自然觀的生態理念,但卻以宗教信念的形式潛在地契合了“天人合一”。它站在生命關懷的高度主張應當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人類、生物與非生物,因為“眾生平等”、“萬物皆有佛性”。個體依靠道德修行的努力能夠向佛的本體境界邁進,從而獲得“內在價值”,因而具有平等的生命本質,所以應當以平等慈悲的心態關懷宇宙眾生,體現了佛教生態倫理自然觀的道德情懷。
(三)混沌直觀的“生態印記”
“天人合一”的樸素有機論自然觀,是東方傳統文化自然觀的基本生態理念。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源和價值之基,人在創生并實現著萬物和自然的“價值”的生態實踐過程中,不斷實現著自身的“內在價值”,在人與自然主客合一的本體思維模式下,達成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同一。在“天人合一”自然觀的熏陶影響下,中國古代文明的實現過程蘊含了天、地、人的有機協調與統一,生態倫理思想初露端倪,五帝時代設置了專門管理草木鳥獸和山林川澤的機構,東漢時意識到水旱自然災害與亂砍濫伐息息相關,到晉代時已把人口數量的暴增與生態環境問題相關考慮。
東方傳統的“天人合一”自然觀是中國遠古先民順天而動,維系自身生存和生活的深層指導理念。作為創生萬物的自然是具有內在生命力的生命始基和價值源泉,所謂之“天道流行”、“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對于今天生態倫理學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囿于時代的局限,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缺乏對自然規律的科學體認。這種建基于“主客一體”的經驗直覺思維基礎上的生態理念具有直觀混沌的總體特性,并過多地強調了人對自然的先天依附性,對主體人類的能動創造性突出不足,但畢竟是遠古文明時代“自然觀”的生態印記,體現出一定的歷史合理性。
二、“人為自然立法”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近代自然科學得到迅速發展。新興資產階級以人權反對神權,高揚人的主體性和價值尊嚴,追求俗世的舒適享樂和現世的實用幸福。當把自然看作一種“純粹的有用性”[1](P535)的時候,單純的經濟增長指標便成為社會進步的唯一價值依據和終極目的。人類開始過度關注經濟發展速度,漠視和排斥發展的目的性和價值性問題,過分追求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無視自然生產力的同步增長。由此,人類過度樂觀的經濟實踐在打破了自然生態平衡之后所獲取的物質增長,實際上是拋棄了生態效益的經濟效益。當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充斥社會,對自然的掠奪式開發、不負責任的毀壞和無節制的浪費也便愈演愈烈。因此,近代工業文明彰顯的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指導下形成的認識論和工具論“自然觀”,是“人為自然立法”的生態悖論。
(一)主客二分的認識論與工具論思維
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使神權統治造就的精神與物質、思維與存在的分裂狀況有所改觀。在高揚人的主體能動意識的基礎之上,注重哲學思維的微觀分析和細節描述。然而,機械論思維的“自然觀”把整體的宇宙、自然與萬物看作靜止、孤立和永恒不變的僵化的“物質世界”,人類成為認識和實踐的絕對主體和對自然進行任意宰割和鞭笞的主人,自然成為滿足人類需要的對象性的工具存在,在工具性的意義上,只能被人類無限地占有、使用和消費,自然本身的精神審美屬性和價值被無限放逐,人類開始“從事著推翻自然界的平衡以利自己的活動”[2](P125)。機械論“自然觀”以單純的認識和實踐關系看待人與自然,把科學認知與道德理念截然分開,認為倫理與道德的原素只限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不存在于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倫理觀念在文化體系中被抽離,生存困境與生態危機便難以避免。
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命題的提出,奠定了西方哲學史上“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基礎,人類相對于自然的主體地位逐步確立起來;康德在強調人類主體認識能動性的基礎上突出了人類的理性主體地位,并把理性自我提升到先驗自我的高度,要求“人為自然立法”;黑格爾把人類的主體意識繼續推向前進,認為人類即理性自由與絕對精神。在“主客二分”的機械論自然觀影響下,培根的經驗主義、笛卡爾的科學分析以及牛頓機械力學充斥整個西方世界,它們共同把作為整體存在的自然生命系統經過分析和還原的方法拆卸、分解為各自孤立的、靜止的原子和單個個體,這是一種數學化和物理論中的“自然觀”圖景:“我們在認識了火、水、空氣、諸星、諸天,和周圍一切其他物體的力量和作用以后(正如我們知道各行工匠的各種技藝一樣清楚),我們就可以在同樣方式下把它們應用在它們所適宜的一切用途下,因而使我們成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3](P593)
因此,“主客二分”最終落實為“人類中心”。人類是唯一具有價值意識的存在者,同時也是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主體性存在,客體的價值屬性成為滿足主體需要的有用性,而這種“有用性”只是相對于主體人類而言的“工具價值”。如此,當以人類物種為尺度衡量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的價值,顧及的是自然對人類的短期效用,自然被降格為向人類提供生存環境和物質資源的工具性存在和沒有靈性的客觀存在,狹隘有限的視角漠視了生命自然系統整體的生態價值以及對人類和其他自然物種的終極性的價值意義,從而進一步消解了人類對自然的道德責任和倫理義務。
(二)“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
“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是“主客二分”的工具論思維方式的具體展現。西方社會自普羅泰格拉明確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命題以后,人類主體性的基調便基本奠定。文藝復興運動打破了神權的枷鎖后,整個社會開始推崇人類的理性和主體能動性,滿足主體人類的欲求和實現人類的幸福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推動了人類運用科技手段統治自然的實踐行為,折射出人與自然相抗爭和對立的“自然觀”的認知意蘊;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以人類理性的普遍懷疑精神,打破了過去幾百年的統治權威和神權信仰,黑格爾以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視角把自然置于人類理性和“絕對精神”的統治之下,人類主體意識最高層面的“絕對精神”是自然演化的至高目的和動力源泉。因此,主體人類的理性意識和能動意識高于自然存在,人類是自然的主人,自然是認知對象,二者是分離和對立的關系。
“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在推動人們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實際上不斷地張揚著人類生命物種的個性,增強著人類的主體性,帶來了人類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的飛躍,又反向強化著人類“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的強權意志,為人類向自然索取找到了合理化的證明和依據。建基于此種“自然觀”的認知理念基礎上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社會經濟理念,被打上“征服”和“占有”的烙印,人類與自然逐漸背道而馳,能源枯竭、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一系列的生態難題接踵而至。由此可見,“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在高揚人類的主體意識和自我創造的優勢的同時,也在不斷毀棄著對自然的人文理念和生態精神。
(三)人與自然的疏離與生態災難
“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其必然性的積極意義。它在高揚人類主體能動性的同時,增強了人類對自然世界探索的勇氣,并拓展了人類對自然認識的廣度、深度以及進一步改造自然世界的力度,促進了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著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生產力的迅猛發展,推進著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但是,“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以對自然的認識論和工具論思維取代自然本體論思維,以機械論取代有機論,以“天人相分”代替“天人合一”,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人與自然的一體相依性,背離了生態倫理思想的深層底蘊,也暴露了人類生命物種個體的狹隘性,引發嚴峻的生態災難。
首先,人的“類本質”的遺忘和生態理念的缺失。如果說,“遠古文明時期“天人合一”的有機論自然觀的認知理念統一于德性論,那么,“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則是以認知論消解價值觀,把道德認知從人與自然關系當中抽離出來,徹底顛覆了自然本體論的價值認知。而脫離了人性的道德束縛的實踐行為必定在充分張揚人類的占有欲和物欲的基礎上對自然開戰,特別是關注主體人類利益并對自然進行機械分割的強勢人類中心主義,從道德認知的深層遮蔽了人類與自然的有機聯系,忽視了對自然生態規律的體認,遺忘了人類與自然共在平等的價值關系和自然本身不可替代的“系統價值”,遺忘了人在“類”的本真狀態下所應當擔負的倫理責任和道德使命,引發難以預計的“生態災難”。殊不知,人類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類的生命之源,在否定自然的實踐行動中實際上又在不斷地否定人類自身,當人類本質力量的呈現片面化和碎片化,那么,人類在追尋自由的同時也便日益陷入不自由的境地。
其次,人與自然關系的疏離和背馳。人類成為控制自然機器并統攝萬有的至高存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線性還原和簡化,遮蔽了自然的價值和人與自然的豐富和多樣性的聯系,自然生命主體地位的缺失使得人類原本應當對自然具有的“敬畏之情”消解,對其他自然生命物種的道德關懷弱化甚至不復存在。這里,人類所謂本質力量的實現歷程同時也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過程,即對自然資源的無度掠奪和對生命尊嚴的摧殘和踐踏,使得自然的生命本性和存在狀態遭受嚴峻的沖擊,并且,自然已經向人類發起了反擊,接踵而至的生態困境已經逐漸發展成為蔓延整個地球生命系統的生態災難,痛定思痛,人類有足夠的理由進行自我反省。
因此,近代工業文明時期“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摧垮了自然本體論的神話,確立起人類主體能動性的理性神話。遠古文明時期對自然的敬畏和敬重之情被近代工業文明時期對科技理性的崇拜所替代,人類與自然相脫離,自然成為工具論和認識論意義上的對象性存在被征服和占有,“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使得人與自然的有機整體聯系分崩離析。實際上,自然是充滿生機和活力并不斷演進和進化著的生命系統,其本身并非是毫無價值意義的“荒野”之地,而是趨向完整、穩定與美麗的生命共同體,這是現時代應當重新確立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自然觀”。重建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關系,應當以生態的道德認知理念和思維方式看待自然萬物,以發自內心“愛”的情感關涉自然,以生態、有機、系統、整體和互利的文化理念和思維視角實現對“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的變革與更新,在對自身進行反思的基礎上,為自身設定行動的域界,即“人為自身立法”,從而探尋生態文明時代“共生和諧”的生態自然觀,替代“天人相分”的機械論自然觀。
三、“人為自身立法”
生態文明時代在人與自然關系的看法上,不同于遠古時期原始混沌的“天人合一”,也不同于近代工業文明時代的“天人相分”,它認為宇宙萬物與自然中的單個生命在生命系統中存在彼此相依的內部關聯,其價值的展現通過自然整體生命系統而獲得生態意義,是“主客統一”思維模式的辯證復歸。因而,重新建構“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有機契合的系統“生態自然觀”,是人類依靠自身價值觀念的反省,不斷地向內追索,為合理“自然觀”的確立及時地補充生態價值的合理因子的路徑,是“人為自身立法”。
(一)“主—客—主”的辯證復歸
走出生態困境,就要在充分考量自然價值的基礎上建構人對自然的新認知模式,以生態的思維理念超越舊的機械論范式,建構系統、整體、有機的生態自然觀,進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生態世界觀的革命,這是深生態學發展的必然趨向,是“主客統一”的思維模式。
不同于舊的孤立、還原的機械論自然觀,系統有機的生態整體主義世界觀把整個自然生命系統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其內部的生命要素相互作用、彼此聯系,作為相互關聯的動態整體中的有機構成,共同維系著整體的生命系統的持續穩定運轉。因此,“主客統一”的思維模式是以自然生命整體的存在為依托的“主—客—主”的關系模式。主體人類能動地作用于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命過程,折射出的是人與自然關系背后的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因此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有道德的原素滲透其中。生態有機論自然觀關注“人——自然”生態共同體的協調運作,其間涵攝了主體“人——人”之間的道德關聯,在生態世界中主要以“人——自然——人”的生態相關性體現出來。通過人類的主體能動性在遵循自然生態規律的基礎之上謀求“人——自然”生命系統的和諧發展,在尊重和維系地球基本生態過程和生命維持系統的同時,尊重自然價值和生命物質的生存權利,在遵循客體生態規律的前提下辯證看待主體人類的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與受動性和依附性的關系,達到主體與客體的辯證為一,實現“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和諧統一。
“主客統一”的思維模式下,主體與客體之間通過自然中介建立起來的“主——客——主”的關系范式,既融匯著人類與自然生態共同體的倫理意蘊,同時也滲透著主體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切和道德內涵,是人——自然——社會復合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思維模式,也是生態文明時代正確把握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自然觀的思維體現。人類的思維從機械式的理性、分析、還原的線性模式下解放出來,向生態文明時期系統有機的綜合、整體的非線性模式轉化,能夠融入更多的知覺情感和人文關切的因素,由支配控制自然的欲望的無限膨脹,轉換為在全人類共同保護自然實踐行動基礎上的理解、寬容、信任和支持,承認生態系統整體的存在意義和價值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有機聯系,這是生態時代的倫理意蘊和“主客統一”思維模式的辯證復歸。
(二)系統有機的“生態”自然觀
“主客統一”的思維模式把自然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有機地整合為一體,使自然認知論融會了主體人類特有的道德認知的因子,把近代工業文明時期的機械論的自然認知觀轉換為生態文明時期的科學、系統、整體和有機的自然價值觀,是作為“類”的存在的人的生態倫理意識的深層覺醒與道德自覺。
人類——自然——社會的整體有機系統是生態的存在系統和價值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及其內在的生命個體,不僅具有相對于人類生存的需要和意義而言的工具價值,而且具有自身存在的固有的內在價值。作為“價值主體”,生命本身的自組織活動必須緊緊依賴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的物質和能量,利用其他系統物質的工具價值維系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這是本身固有的“內在價值”。作為“價值客體”,自身在生態系統中創造的物質成果又不斷地為生命系統整體的維系與協調運轉和其他生命個體提供著不可或缺的“工具價值”。作為整體的自然生態系統在系統運作過程中是一個自組織、自協調、自進化、自選擇、自平衡的生態過程,在自然周期性的運轉過程中不斷孕生、養育和發展著豐富多樣的生命目的中心與價值中心,在系統進化與價值增值的過程中維系著自然生命整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這是自然生態系統整體的“系統價值”。因此,生命個體之間、生命個體與種群、生命個體、生命種群與自然生命系統整體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價值關聯,個體的生命存在具有“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的價值屬性,而自然生命系統整體卻具有至高的“系統價值”屬性,它們共同構成了生態系統中的“價值”整體。
因此,“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的系統整合的生態自然觀認為,人類作為自然之子,產生于自然生命系統,是生態系統不可分割的生命組成部分。人類的生存維系和發展,必須緊緊依賴自然生命系統的穩定和進化。同時,人類的主體價值也必須歸依自然生命系統的整體性的存在價值才能夠得以展現,主體人類在自覺意識到自身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存在價值的基礎上,應當尊重其他生命存在的“內在價值”和自然的“系統價值”,發揮生命主體的調控作用,維護自然生命系統乃至整個生物圈的穩定與和諧,促進人類與自然生命系統的協同進化。
(三)反思與審視
“生態”自然觀不僅是系統論自然觀在人類生態社會的具體彰顯,也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在現時代的內在要求。生態自然觀把人類對自然的科學理性認知和對待自然的倫理關懷與道德關切統一起來,把自然“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系統整合起來,在科學認識自然因果律的基礎上注重自然生態平衡規律的維系,在合理運用自然工具價值的基礎上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尊重自然的“系統價值”,把人與自然的協同發展和共生和諧作為生態實踐主體的道德價值訴求,在具體的生態實踐中充分發揮人類主體的意識能動性,維護、恢復并優化自然生命系統的動態平衡。因為人類——自然——社會是動態有機的復合生態系統,人類的自然性、社會性以及精神性的生命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一體樣態,這是系統有機的生態世界觀和自然觀的內在規定和價值含義。
因此,人類“自卑——自負——自省”的思想成長歷程,也是現代人類在“類本質”覺醒的基礎上不斷地向內追索的道德哲學生長過程。道德哲學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不斷思考中得以“深化”,人類自身在“類本質”意境的不斷彰顯中得以“進化”。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解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契機。和諧共生的建設性的伙伴關系和對話關系的建構,是生態自然觀的本質內涵,為人與自然之間倫理關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應當成為綠色文明時代的倫理共識和文明期待。
[1] (英)J.D.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責任編輯:郭泮溪
“View of Nature” and the Ecological Dilemma in Light of Philosophy
NIU Qing-yan
(Dept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
The ecological dilemma is becoming a major global problem threatening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human race. By inspecting the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view of nature” with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it is found that after “legislation for man by nature” of ancient times and “artificial legislation for nature” of modern industrial times, it is time for “legislation by man for himself”. Moreover, the “ecological view of nature” is not only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t the present time, but also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basis to alleviate and even to re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which should become the ethic mutual recognition and the civilized anticipation in times of green civilization.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dilemma; moral philosophy
B82
A
1005-7110(2011)01-0032-06
2010-12-30
本文系江蘇省教育廳2009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09SJB720007)階段性成果。
牛慶燕(1978-),女,山東泰安人,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哲學博士,研究方向:道德哲學、生態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