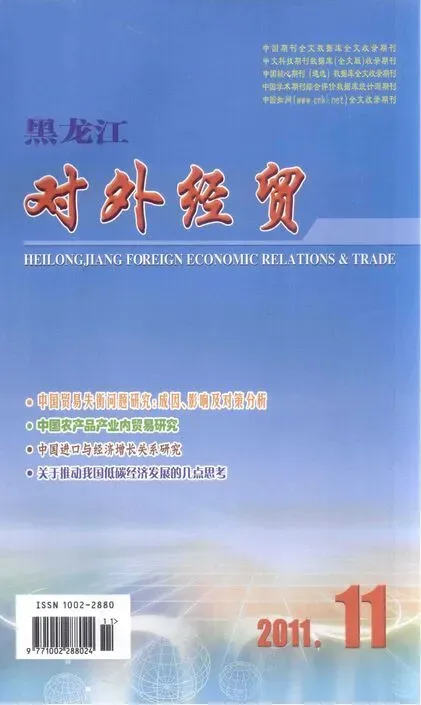農地非農化過程中土地增值原因及其分配方式研究
田 旭
(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沈陽工程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一、農地非農化的原因分析
農地非農化是任何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必然經歷的過程,農地非農化過程伴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社會經濟的增長。
(一)城市經濟的發展
任何國家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必然要發展城市經濟。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對城市原有的經濟布局和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和升級。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城市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吸引了大量資金投資,大量投資使土地需求上升;同時原有的工業企業面臨環境壓力需要向外遷移,城市向外擴張的壓力大,對城市近郊土地需求增加,城市郊區的農村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城市經濟的發展,土地價值上升,城市中心地區寸土寸金。城市中心區域土地價值的上漲,導致土地使用轉向效益高的商業用地,原有居民只能向城市周圍遷移,城市面積不斷擴容。同時城市的發展對基礎設施的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市基礎設施的大量建設,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
(二)城市人口的增長
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提高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大量的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成為農村的富余勞動力,農民的隱性失業率上升。農村大批富余勞動力需要向城市轉移,他們紛紛離開家鄉土地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城市經濟的發展為大量外來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同時這些外來人口的勞動又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隨著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遷移,城市人口在不斷增加。城市要為外來人口提供居住條件,而外來人口由于從事的職業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收入,他們只能把家暫時安置在城市周圍。城市人口的增長,需要大量的土地來吸收和安置新增的城市人口。同時老城區的改造、城市環境的改善、人均居住面積的增加等,必然導致城市面積的擴張,加劇了城市周邊農地的非農化速度,城市周邊大量的農地轉為城市土地。
二、農地非農化過程中土地增值原因分析
農地轉為建設用地,土地價值增加幾倍到數十倍。國內不少學者都對土地價值增值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章植(1934)認為,影響土地需求和土地供給的因素都能導致地價的漲落。張德粹(1979)認為對地價發生影響的諸因素可分為三大類:土地本身所具備的自然條件、土地所處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及一般的經濟情況。周誠(2003)認為,土地增值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供求性增值,二是用途性增值,三是投資性增值。綜合國內學者的研究,本文認為農地非農化過程中土地增值原因如下:
(一)農地非農化使土地的用途發生改變
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遠遠高于農村,工業生產效率也高于農業生產效率,市地的邊際收益高于農地的邊際收益。農地被政府征收后轉為國有建設用地,其用途發生根本改變,從農業用地轉為城市用地,土地價值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土地的使用價值決定土地價值,商業和工業用地使用價值高于農業用地使用價值是由于商業和工業用地的土地邊際產出高于農業用地的邊際產出。由于農地轉非,土地用途的改變使土地使用價值上升,產生土地增值。
(二)城市發展對土地需求的增加
土地的需求與經濟發展成正向關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對土地的需求增加。由于土地的數量固定,主要在市地和農地之間分配,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對土地的擴張需求,人口增長對土地的居住需求,這些都導致土地需求的上升。而土地數量的固定,決定了土地供給增漲的有限性,西方經濟學土地價格取決于土地的需求,土地需求增加土地價格上漲。土地供求之間的矛盾,推動了土地價格的上漲。
(三)經濟發展推動土地價值上升
隨著經濟的發展,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出不斷上升,提高了土地的使用價值。土地的使用價值決定土地的價值,使用價值的上漲必然導致土地價值上升。同時,經濟發展使城市土地越來越稀缺,城市土地價值的上漲,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和居民的居住成本。企業開始向城市周邊轉移,居民也向周邊轉移,對城市周邊土地的需求上升,也帶動了城市周邊土地價值的上升。
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論研究
(一)“漲價歸公”理論主要觀點
持“漲價歸公”論的學者認為:征收農地過程中產生的土地收益增值部分應全部歸于社會,即政府所有,用于全社會的建設與發展。亨利·喬治(1879)認為土地的價值之所以增值,是人口的集聚和生產的需求,而非某個人的勞動或投資引起的,因此土地增值的收益應收歸全社會所有。孫中山提倡土地“漲價歸公”,主張土地收歸國有,對于一時政府財力不夠而不能收歸國有的土地,應該通過征稅將土地收益收歸政府所有。臺灣經濟學家林英彥指出“目前之土地市價,除了土地所有人申報應歸其個人所有的地價以外,尚包含龐大的自然增值額,這是應當屬于社會全體的。所以,如果按照市價補償,那無異于將自然增值部分也視為個人財產給予補償,其不合理之情形至為明顯。”
(二)“漲價歸農”理論主要觀點
“漲價歸農”觀點認為:農地征收過程中產生的土地收益增值部分應全部歸于農民,這種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是普遍存在的。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在中國失地農民被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體系之外,政府征地補償標準低,是農民收入增長慢、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其前提是農民擁有完整的土地產權,即土地所有權、土地收益權、土地處置權、土地發展權等,政府要對失地農民的所有權益進行完全補償。
(三)“公私兼顧”理論主要觀點
周誠先生認為,“漲價歸公”論只看到農地的自然增值來源于社會經濟發展,國家應當擁有整個農地發展權,從而忽視了失地農民作為農地所有者也應當分享此項權利;“漲價歸農”論只看到失地農民應當享有農地發展權,而根本忽視國家和其他農民也應當享有土地發展權。通過對以上兩種觀念進行修正,周誠先生提出了“公私兼顧”理論觀點。“公私兼顧”就是要在農地非農化過程中價值增值的分配中,應在土地利益相關各方之間進行合理分配,保護利益相關各方的農地權利。
四、農地非農化過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
我國的“二元”土地制度下,土地的最終發展權掌握在政府手中,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人沒有農地發展權。這樣的權益安排雖然能使政府從宏觀角度保護基本農田,但也是對農村集體土地權利的侵占,使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受到損害。我國可將整個農地發展權分解為失地農民的農地發展權和國家的農地發展權,實行公平分配農地非農化所產生的土地增值,在公平補償失地農民的前提下,用于全國的農村建設。
(一)失地農民享有農地轉非增值收益
我國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者為全體農民,每戶農民對其承包經營的土地擁有使用權、收益權和發展權等權益。政府征地使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土地上的權益,農民有權獲得“保障性補償”的權利。土地用途發生改變,商業和工業用地的邊際效益遠遠高于農業用地的邊際效益,土地用途改變所帶來的土地價值增值是土地發展權價值。現行的征地補償規定中,土地補償款實質是對土地產值補償;安置補償實質是對土地保障功能補償,對土地的發展權沒有任何補償,這是對失地農民權益的剝奪。要提高現行的土地補償標準,從農地轉非過程中所產生的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為失地農民建立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系統,使失地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上無后顧之憂。
(二)國家享有農地轉非增值收益
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都對土地需求上升,土地需求的增加使土地價格上漲,土地發生增值。這部分增值與農業生產和農民投入無關,這部分的增值主要得益于社會發展,土地增值收益應由社會分享。國家作為土地的最終所有者,享有土地發展權,有權代表全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這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要用于農業建設和環境建設等民生項目,讓這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惠及整個社會。
(三)在耕農民享有農地轉非增值收益
農村集體內每一塊土地都應享有相同的發展權益,土地發展權本應屬于農民,但由于國家的土地利用規劃和用途管制使大部分農地所有者失去了土地開發機會。這部分土地的發展權實際上掌握在國家手中,在耕農民失去了土地發展權益,國家要對在耕農民失去的土地發展權給予補償。我國可以參照美國的土地發展權交易形式,即國家從在耕農民手中購買農地發展權。可以從農地轉非增值收益中劃出一定比例用于補償在耕農民失去的土地開發機會損失,將部分農地轉非增值收益作為農業種植補貼,既能提高農民種植的積極性,又能實行農村集體土地權益均衡。
[1]周誠.關于我國農地轉非自然增值分配理論的新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06(12).
[2]周誠.“漲價歸農”還是“漲價歸公”[J].中國改革,2006(1).
[3]鄒秀清.農地非農化:兼顧效率與公平的補償標準[J].經濟評論,2006(5).
[4]周誠.論土地增值及其政策取向[J].經濟研究,1994(11).
[5]黨國英.土地級差收益如何分配—農村土地問題系列談(3)[N].21世紀經濟報道,2003-12-22.
[6]于恩和,喬志敏.重新認識級差地租及其與土地收益分配的關系[J].經濟問題,1997(3).
[7]楊繼瑞.地價上漲機制探析[J].經濟研究,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