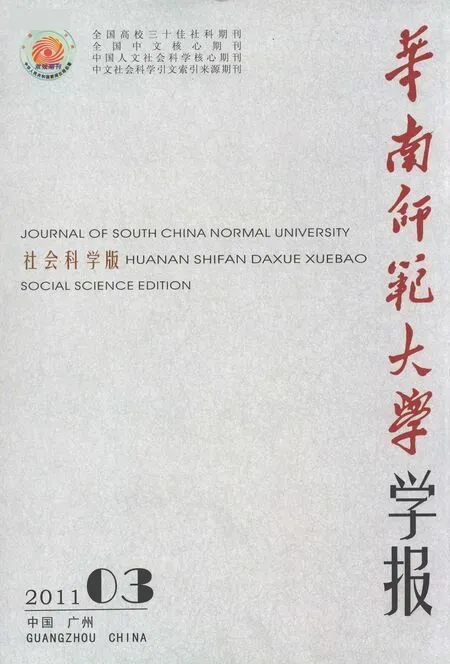女性主義認識論視野中的知識生產
呂春穎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女性主義認識論視野中的知識生產
呂春穎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知識生產是在社會歷史和文化中展開的人類活動,它受多重維度的影響。女性主義指出了傳統認識論的客觀性在實質上是男性中心主義的。女性主義認識論則表明知識生產領域中的男性中心主義所存在的固有缺憾,并探討如何重建客觀性與人類知識生產的框架。
女性主義認識論 知識生產 男性中心主義 客觀性
當代女性主義的研究不但深入到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領域,也深入到哲學認識論領域。女性主義認識論不僅重新審視既有的知識生產體系,而且在揭露它所存在的問題的同時,力圖發現人類知識生產的新形式和新規律。
一、女性主義認識論的特點
廣義的知識,涵蓋了從日常經驗到抽象理論的各層面、各形態的系統,是人類的創造物,所以才有所謂知識生產。知識生產是人類的行動。從狹義講,它意指專業人員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但廣義的知識生產卻是指人類作用于客觀世界的創造性活動,它要達成的是對人與世界的秩序化領會,其成果就是知識。知識不是事物的性質,而是人類的能力,對此,諾奇克(Robert Nozick)曾說:
求知就是擁有追蹤真的信念。知識是與世界聯系的一種特定方法,具有與世界特別的和真實的正確聯系:追蹤它。[1]178
認識論探究知識的本性與信念的證成,是對知識加以評估的學問。而女性主義認識論則是女性主義從社會性別視角對傳統認識論的反思與批判。女性主義者在多元文化、全球化以及性別差異的社會歷史圖景中重新審視知識的社會性內涵,指出當今知識生產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義,并力圖糾偏之,以期達成為女性爭得合法知識生產者地位的目標。
女性這個群體名詞所指涉的個人,其實際身份是多樣的,她總是身屬不同的民族、種族、階級和文化傳統。因此當前的研究不會將女性視為具有同一本質的主體。但在理論研究中,之所以仍然可以合法地使用女性一詞,其原因在于:女性是一個針對歷史和現實問題的“理想類型”,盡管它不能對事實進行完全概括,也不能解釋所有的現實問題,但卻是有益的啟發手段和創造性視角。此外,“知識生產”同樣意味著多元的和異質的知識生產樣態。[2]247
誠然,女性主義主要是政治的和社會的運動及其理論,但認識論卻是它們的思想根基:
一切社會理論,包括女性主義者對社會生活的解說,都意味著某種知識理論,某種如何去知曉社會生活的理論。所有女性主義者都關注女性的知識如何才能最好地生產出來,關注那些知識該是什么樣子。這些都是認識論問題。[3]73
盡管凱恩(Maureen Cain)的說法有些絕對,但卻表明認識論問題與女性主義者的政治追求和現實行動息息相關。作為被壓迫者的女性有必要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對既有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作出批判與解構,力爭結束知識生產體系中制度化的“男性中心”。
女性主義者認為,知識生產是歷史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活動,它受到以對性別的理解、規范和認可為載體的社會性別的深刻影響。由于帶著問題意識進入認識論領域的研究,女性主義者研究認識論問題具有鮮明的特色。
首先,反抗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女性主義者帶著政治立場和政治目的介入認識論問題,即反抗性別壓迫。她們認為,在知識生產中存在著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她們“贊同女性主義的社會理想和政治目標,在回答性別是什么以及怎樣影響認知的差異時,將性別壓迫同追求知識的實踐聯系起來。”[4]189
其次,關注社會性別如何影響人類的知識及其生產。“女性主義認識論是關于社會性別以何種方式影響那些我們視之為知識的東西的。考察那些專屬于學院的客觀理論及科學知識。西方社會將這些知識打上了‘男性的’標簽,而且不許女性獲取并生產這樣的知識……”[5]312女性主義者力圖打破在知識生產領域對女性的種種限制,終結知識生產領域的性別不平等現狀。
最后,女性主義者重視知識生產主體的身份解析,并批評現代認識論中的知識創造者是個不可能的抽象主體。展開對認知者的考察意味著“對我們而言,研究者就不再以無形、匿名與權威的聲音出現,而是表現為一個有具體和特定欲望與利益的真實的、歷史的個體”[6]9。她們認為,現代認識論中那個抽象的、作為主體的認知者實際是男性,進而還提出了“它是誰的知識”這樣的根本問題。[7]370
由于具有以上的特征,女性主義者所進行的研究特別注重對客觀性問題的研究,因為傳統的認識論將客觀性實際地歸于男性,它導致對女性參與知識生產活動能力的懷疑,并視女性為不合格的認知主體,最終造成對知識生產的諸多限制。
二、女性主義認識論對傳統客觀性的揭露
研究認識論的女性主義者均反對帶著中立、超然、純粹與形式化名義的客觀性。知識生產是需要主體參與的過程,因此無法擺脫社會、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傳統知識觀念之所以忽略這些方面對知識生產的影響,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設定的客觀性上。
傳統的客觀性被視為是價值中立的,但實際上卻被歸于男性,因此它遠離了自詡的“客觀”。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指出:傳統認識論中的客觀性實際上至少會被用于以下四種情況:第一,某些個人或其團體所有的屬性,因為在“婦女(或女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環保主義者、黑人、東方人、享受福利者、病人等等)身上更感情化,更難以做到無偏見,太多的政治承諾使之難以得出客觀的判斷”;第二,知識假說的屬性,陳述的屬性;第三,人們覺得很公平的方法或慣例的屬性;第四,某些知識探索社群的結構屬性,典型的代表就是現代自然科學。[8]171-172
哈丁對客觀性所做的女性主義分析打破了傳統認識論的客觀性神話。所謂的客觀性一詞具有不同的屬性,它可以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在人們展開對實在的研究來進行知識生產時,難免會受到主體的某些屬性的限制,所以客觀只能是帶有偏見的。[9]389而所謂客觀的知識則是以某種概念框架的政治見解即特定的共識為基礎。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知識所描繪的圖景會與實在相符合,讓人們覺得它是公平的方法或者慣例。這意味著知識所描述的實在對特定的共同體來說是客觀的,它出自、也符合特定共同體的人們的共識。
哈丁指出:知識與特定的社會之間存在不可脫離的關系,“科學與其社會之間是一種共建關系”[8]2。這種關系說明:在惟有男性的立場和知識生產手段才能得到肯定的社會里,女性作為認識主體的地位和女性對經驗的陳述與表達,很難受到真正的重視。因為人類的社會結構不僅約束個人和群體的道德思想,還會約束作為社會子系統的知識生產系統。①羅伯特·金·默頓的《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范岱年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是研究科學與其外部環境之間關系的著作。該書研究了十七世紀英格蘭地區出現的近代科學的社會和文化環境,它表明:科學的社會文化結構受到社會因素的巨大影響。因此,近代以來傳統認識論之下賦予知識的客觀性,只是一廂情愿的說法。知識起碼受如下幾個基本因素的影響。
首先,知識生產總會受到公共秩序的影響。馬克思曾說:“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0]18人受社會的塑造,接受的是特定社會的公共秩序和內在于其中的公共價值,因此個人的思想會受到公共秩序的約束,哪怕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是如此。[11]129男/女的二分法是社會公共秩序的一部分,它有效地約束著知識生產者,而且使得系統性的兩性分工與分化的社會秩序得以維系。
其次,知識總是在特定文化中得以確立,文化是“科學技術的工具箱”(哈丁語)。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知識創造者的文化背景發揮者重要作用:最初的理論資源“必然是從科學家一般的文化資源中獲得的,或者從這種資源中獲得了靈感”[12]16,它使得知識生產不可能盲目進行。所謂的現代知識則是在現代文化或曰歐洲文化中獲得最初理論資源并得以確立的相對信念,而這種文化始終帶有性別偏見,即認為“某些種族、階級、民族和性別的成員被認為比其他人更具有客觀精神。在嚴格地遵循科學方法的規則方面,人們并不認為所有的群體具有同樣的能力。男性氣概就被比認為女性氣質更能產生客觀性。”[8]185
最后,對知識生產這一獨特的領域來說,它沒有擺脫語言的二分法。語言在現代知識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是語言界定了歷史階段中某一社會的主要知識生產的范圍。一般而言,知識生產的傳達需要借助語言,人類對知識的接受也主要依靠語言。其中,人類幾乎處處都用到了男/女相對立的二分法,并因此確定了客觀性的觀念。伊麗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就曾這樣說:
女性主義者指出,幾乎沒有什么概念的二分法不是跟隨并運用了男性化/女性化這對概念的,例如,心靈/肉體、文化/自然、理性/情感、客觀/主觀、堅強頭腦/脆弱心靈,等等。這些令人反感的隱喻組合派生出知識、科學與理性的追求以及與這些追尋活動相關的客觀性概念,它是一個部分地被性別主義觀念所認定的適當男女關系塑造出來的觀念。[5]326
語言隱含著社會與文化的觀念性支撐,而我們所用的語言,始終充滿了男性中心,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下,現代知識生產過程也總是男性中心的①查菲茨(Janet Chafetz)指出:那些想當然的概念、語言和寫作風格等都是由男性創建的、疏遠婦女的、支持父權制的統治關系或統治秩序的。在這點上,它與女性主義者的學術關懷相對立。(查菲茨:《女性主義理論與主流社會學理論的貢獻》,濮亞新等譯,載《國外社會學》2001年第1期)。因為,盡管人類用秩序化的知識來表達對世界的認識,但知識同樣也是人類對世界的秩序和規定,現代人的知識生產所面向的主要是被語言約束了的實在,而帶著性別偏見的客觀性讓“男性觀點作為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被強加在世界本身了”[8]188。
傳統知識論中的所謂客觀性并不能做到普遍有效,所以,女性主義者轉而采用歷史的和社會的視角去看待客觀性問題。
三、女性主義認識論對客觀性的建構
女性主義者強調知識的建構性,她們將作為知識基本特征的客觀性本身作為必須加以探討的問題,以明確其所指。其中有部分女性主義者依然堅持著啟蒙時代的知識與客觀性信念,并認為知識生產不是相對主義的,它的目的始終是達成真正的客觀性。例如,哈丁、哈拉維(Haraway)②例如,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in Human Geography:an Essential Anthology,ed.by John A.Agnew,David N.Livingstone,Alisdair Rogers.MA: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1996:108-128.、朗基諾(Longino)③參見 Helen E.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和納爾遜(Nelson)④參見 Lynn Hankinson Nelson.Epistemological Communities”,in Feminist Epistemologies,ed.by L.Alcoff,E.Potter.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3:121 -159.等人均主張在女性主義的范圍內達成更好的客觀性。這方面的成果,以哈丁的從女性主義立場論(standpoint theory)出發形成的“強客觀性”(strong objectivity)理論為代表。
哈丁指出客觀性的多種情況,它表明客觀性并非如傳統所信賴的那樣不言自明,但她還是主張保留客觀性的概念,并提出客觀性的“強綱領”,以期達成“強客觀性”[8]167-196,這不同于以往的“弱客觀性”(weak objectivity)。[13]138-163強客觀性是哈丁采用社會理論的分析方法來解構知識生產中立的傳統信念的結果,它表明知識生產必然帶有特定立場,但人類具有反思能力,可以分析出哪些因素影響它們,并由此判定哪些因素阻礙了人類達成真正的客觀知識。此基礎上,人們可以創造新的社會條件,并達成更為客觀的知識。“強客觀性”意味著用研究異文化(foreign culture)的社會分析方法來分析自身知識生產的社會背景和立場。[13]98
哈丁認為,知識生產的最佳模式是社會科學,而不是自詡中立、客觀的“弱客觀性”所推崇的物理學。哈丁批評傳統認識論所宣稱的客觀性觀念,但她也主張不采用相對主義去看待它,而是認為既存的各種知識生產都是社會化的。哈丁主張注重性別視角,并提倡一種地方性、情境性和多元主義的知識觀念,它意味著:在知識生產領域,無法達成絕對意義的客觀。這樣的觀念首先可以讓知識生產者避免將自身的視角普遍化和客觀化,從而造成一種強勢話語;同時也使認知者可以采取謙遜的態度看待自身的知識生產活動,避免建立新的知識生產特權。如果當代知識生產能夠不再標榜自身具有絕對的客觀立場,而是能認識到自身所蘊含的性別偏見、立場及其根源性的深廣社會結構,所謂客觀性只不過是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那它們也可以成為具有“強客觀性”的知識。
“強客觀性”理論在保留客觀性的同時,又強調了知識生產活動的社會歷史性、知識生產主體的歷史性、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互動關系,強調了知識生產主體對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自覺,即對自身生產活動的種種局限性的意識,它為女性主義者強調女性的生活經驗對知識生產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政治訴求奠定了理論基礎。強客觀性的提出,意味著任何認知者并沒有超越既定歷史條件與社會環境的特權。它進而強調:從女性的生活經驗出發,將會生產出較為中立的知識。因為傳統的客觀性自稱價值中立,名義上的絕對化和普遍化令其無法反省自身的男性中心。而女性則清楚自身的立場和局限性,不會將自身的觀點與立場絕對化為普遍性,因此有利于達成更為客觀的知識。
“強綱領”是一種認識論的理想目標,因此,哈丁在知識的普遍性與相對主義之間的調和立場遭到了后現代女性主義者的批評。她們認為,這是在重復啟蒙運動要建立具有普遍性元知識準則的主張。后現代女性主義者表現出對現代女性主義的反動,她們將男/女、平等/差異等二分法視為形而上學的強制范疇,并反對經典的二元劃分模式,提倡多元模式。但哈丁認為,這是放棄了知識對實在作確定描述的目標。盡管知識生產可以與文化和社會歷史相關,但人們依然可以判定,怎樣的社會環境有助于生產出更為客觀的知識:
立場論的認識論要求認識歷史的、社會學的和文化的相對主義,而不是判斷的和知識上的相對論主義。她(他)們認為,凡是人類信念,包括最突出的對科學的信念,均受社會環境的制約,但她(他)們也要求能批判地評估何種社會環境才能產生最為客觀的知識陳述。與判斷上堅持相對主義的人不同,她(他)們要求科學地說明受歷史制約的信念與最大客觀信念之間的聯系。[13]142
后現代主義的女性主義者的思想與科學和高度重視科學理性的社會所支持的認識論中心的哲學相對立。[14]536但哈丁認為,立場論可以調和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間的沖突,因為立場論的邏輯與自身的現代起源有一定距離,并且指向了某些后現代主義的目標。[14]504
四、女性主義認識論對推進知識生產的意義
“在女性所參與的日常經驗與‘理論語言’之間,存在著持續性的分裂。理論語言對經驗施以帝國主義。事實上,理論和經驗之間存在著權力關系,其中一個后果就是,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中,女性都被排斥在外。”[15]162在現代知識體系中,共識基本上由男性成員達成,它有意無意地排斥了女性的經驗和女性對自身經驗的解說:“在社會中,男女兩性占據著差異的(differences)位置,并因而具備差異的經驗。此外,在以男性為主的知識生產者中,這些差異被典型化了。這些批評轉而又強化了多數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自稱的客觀性。”[16]1這個現代知識生產體系的框架和傳統都建立在男性經驗的基礎上,未曾充分顧及眾多女性在世界中的獨特經驗,在所謂的知識客觀性和普遍性背后,隱藏著男性中心的價值觀。①例如,可參見Lynn Hankinson Nelson,Jack Nelson編輯的Feminism,Science,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一書中的Harding的“Feminist Philosophies of Science”一文。在該文的第三部分尤其是第279-280頁,哈丁集中指出了現代科學的男性中心和歐洲中心所主導的價值觀。(Lynn Hankinson Nelson,Jack Nelson,Feminism,Science,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therlan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7.)
女性主義認識論從性別立場出發,揭開了知識生產過程所戴著的普遍性面紗。正因為知識出自特定的標準和特定的人群,所以它只具備相對的有效性:“盡管我們可以在原則上斷言科學對所有理性生物是潛在地有說服力的,但這在實踐上不具有可能性。科學團體被賦予代表所有人創造和批評公共知識,在合理的期望中,其判斷不會遭到挑戰。”[11]127
在認識論領域,女性主義“力圖理解既有社會秩序,并力爭發明有效的策略去改變它”[16]1。女性主義者批判傳統認識論當中的男性中心,并認為它導致對女性經驗和立場的忽視,使人類的認識活動無法取得更大的普遍性。一方面,如果不打破它的統治地位,男性中心就會在認識上排斥和壓制邊緣群體的觀點,由此所得到的知識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普遍與客觀;另一方面,既然男性中心所創造出來的知識只是“弱客觀性”的,那就不可能帶來民主。知識的發展還很可能在社會權力體系的作用下,加深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信息鴻溝(Information Gap)和科技鴻溝(Technology Gap)②參見 M.Andrea.Matwyshyn,“Silicon Ceilings: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ty,the Digital Divide and the Gender Gap am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in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Vol.2,No.1),Fall 2003,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p.35-75.另外還有 Sue Curry Jansen,“Gender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A Socially Structured Silence”,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9,No.3)Summer 1989,p.196 -215.。
如果知識生產要真正為所有人謀福利而不是僅僅維護男性中心,那就必須兼顧公正原則,必須尊重不同群體的知識權利和話語權力,并真正建設出以平等對待多元價值、多種文化、多樣群體為基本要求的、對人類來說公正而善意的知識生產體系。
女性主義認識論是對既有思維方式的顛覆,同時也反映了當代知識生產的需求。在對傳統認識論的批判中,女性主義者從社會性別視角出發,對蘊含著性別偏見的知識權威發出挑戰。在此基礎上,她們探討提出了新的知識范式,并希望可以在此基礎上生產出具備“強客觀性”的知識。這些富有創新性的努力,為建立更為客觀的知識生產方式作出了貢獻。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王宏維教授的多次悉心指導,在此謹向王老師深致謝忱。)
[1]Robert Nozick.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2]王宏維.誰來講出關于女人的真理?——哲學視域下的性別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3]Maureen Cain,Foucault,Feminism and Feeling:What Foucault Can and Cannot Contribute to Feminist Epistemology∥Caroline R.R.Up against Foucault: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London and New York:1993.
[4]E.Heidi.Grasswick,Mark Owen Webb,Feminist Epistemology as Social Epistemology,Social Epistemology 2002,Vol.16,Issue 3.
[5]Elizabeth Anderson,Feminist Epistemology:An Interpretation and a Defense∥K.Brad Wray.Knowledge and Inquiry:Readings in Epistemology.Ontario:Broadview Press,2002.
[6]Sandra Harding,Feminism and Methodology:Social Science Issu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1987.
[7]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桑德拉·哈丁.科學文化的多元性: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和認識論.夏侯炳、譚兆民,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9]Sandra Harding,Comment on Hekman’s‘Truth and Method: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Whose Stand Point Needs the Regimes of Truth and Reality?Signs,Winter 1997.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約翰·奇曼.可靠的知識:對科學信仰中的原因的探索.趙振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2]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魯旭東,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13]Sandra Harding,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4]哈丁.什么是女權主義認識論∥佩吉·麥克拉肯.女權主義理論讀本.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5]Liz Stanley,Sue Wise,Breaking out Again:Feminist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16]Kathleen Lennon,Margaret Whitford,“Introduction”,Knowing the Difference: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Epistemology.London:Routledge,1994.
呂春穎(1975—)女,吉林吉林人,哲學博士,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后。
2011-01-15
B023.2
A
1000-5455(2011)03-0095-05
【責任編輯:趙小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