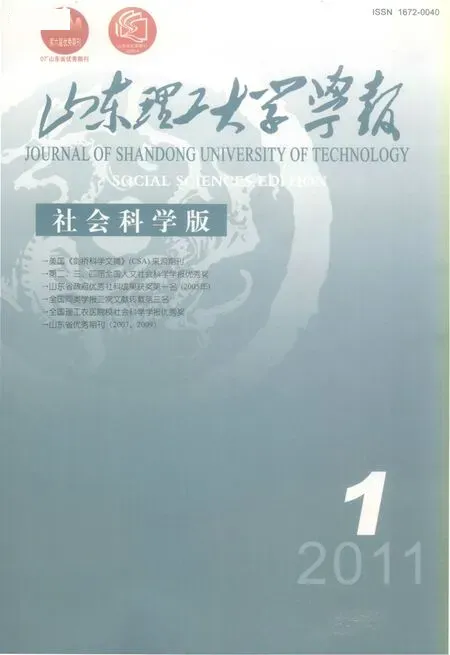中西古代遺囑繼承比較研究
夏 婷 婷
(沈陽(yáng)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遼寧沈陽(yáng)110034)
一、中國(guó)古代遺囑繼承的含義
唐咸通六年(865年)敦煌尼靈惠唯書(shū)
咸通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尼靈惠忽染疾病,日日漸加,恐身無(wú)常,遂告諸親,一一分析。不是昏沉之語(yǔ),并是醒生之言。靈惠只有家生婢子一,名威娘,留與侄女潘娘。更無(wú)房資。靈惠遷變之日,一仰潘娘葬送營(yíng)辦。已后更不許諸親汯護(hù)。恐后無(wú)憑,并對(duì)諸親,遂做唯書(shū),押署為驗(yàn)。
弟金剛
索家小娘子
外甥尼靈皈
外甥十二娘 十二娘指印
侄男康毛(押) 計(jì)計(jì)索甥外
侄男福晟(押)
侄男勝賢(押)
索郎水官
左都督成真[1]565
上面所列舉的是一份唐咸通時(shí)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遺囑原件,該遺囑不是以財(cái)產(chǎn)繼承為核心,而是將人作為繼承標(biāo)的囑于他人。在古代漢語(yǔ)里,遺囑又做“遺屬”、“遺書(shū)”、“遺言”、“遺命”、“家約”、“唯書(shū)”、以及“先令”等稱(chēng)呼,顯然,古代遺囑的含義要比今天我們所說(shuō)的專(zhuān)門(mén)的法律術(shù)語(yǔ)“遺囑”廣泛得多。遺產(chǎn)繼承型的契約有別于一般的契約形式,尤其是在宗法等級(jí)制度突出的封建社會(huì)中,這種契約不是由雙方或多方協(xié)商締結(jié)的,而是由財(cái)產(chǎn)所有者或家長(zhǎng)單方?jīng)Q定其遺產(chǎn)繼承人及繼承的方式。寫(xiě)作本文的目的,就是想讓大家對(duì)我們古代遺囑這一特殊的契約形式有所了解,并且通過(guò)與羅馬法中關(guān)于遺囑繼承制度的比較,對(duì)我國(guó)古代遺囑的效力問(wèn)題作深入的探討。
二、羅馬法中遺囑繼承制度的規(guī)定
羅馬法中的遺囑繼承,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作了詳盡的規(guī)定。除規(guī)定了一般意義上的遺囑繼承以外,還存在著戰(zhàn)爭(zhēng)時(shí)訂立的遺囑、被俘虜或者是被判刑時(shí)訂立遺囑的效力問(wèn)題。在這里,只將羅馬法中關(guān)于一般意義上的遺囑繼承制度與中國(guó)古代的遺囑繼承作一比較。
莫德斯丁:《學(xué)說(shuō)匯纂》第2篇“遺囑(testam entum)是我們對(duì)希望在自己死后做的事情的意愿之合法表示(iusta sentential)。[2]251這是羅馬法中對(duì)遺囑下的明確定義。意思就是說(shuō),立遺囑人在生前對(duì)自己死后想做的事情或是愿望所作的預(yù)先意思表示,并且這種表示行為要具有合法性。立遺囑人可以是對(duì)自己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處分,可以是解放自己的奴隸,也可以是對(duì)某種行為的處理,抑或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只要是合法的表示,即視為遺囑有效。
那么什么才算是合法的表示呢?羅馬法對(duì)此作了更為詳盡的規(guī)定。
第一是對(duì)立遺囑人能力問(wèn)題的規(guī)定。蓋尤斯《法學(xué)階梯》第2編:“如果我們考察一個(gè)遺囑是否有效,首先應(yīng)該注意遺囑人是否有立遺囑的能力;其次,如果他有能力立遺囑,則我們將進(jìn)一步考察他是否是依市民法的規(guī)則立的遺囑。”以此為條件,聾啞人、在發(fā)病期間的精神病人、對(duì)自己的身份存在誤解或者是疑惑的人,都不具有立遺囑的能力。在年齡上,男性滿(mǎn)14歲、女性滿(mǎn)12歲才可以立遺囑。但接下來(lái)的一個(gè)條款中明確了家子處于父權(quán)之下,沒(méi)有遺囑權(quán),也就是說(shuō)即使男性滿(mǎn)14歲、女性滿(mǎn)12歲,如果是在家父權(quán)之下,那也不可以訂立遺囑。即使家父允許他立遺囑,但他亦不能合法地為之。這一硬性條款,即便是家父同意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與立遺囑人能力相對(duì)應(yīng)的是依遺囑獲得的繼承能力。彭波尼《論規(guī)則》單編本:“可以肯定,家子、他人的奴隸、遺腹子和聾者都有繼承的能力。盡管他們不能夠立遺囑,但是,他們能夠通過(guò)遺囑為自己或者為他人獲得遺產(chǎn)。”
第二是遺囑人的意愿。拉貝奧《由扎沃拉諾整理的作品》第1編:“遺囑人設(shè)立遺囑需要的是大腦思維的完整性而非身體的健康。”也就是說(shuō),立遺囑的時(shí)候,遺囑人要有真實(shí)的意思表示。如果一個(gè)遺囑人在訂立遺囑時(shí)變?yōu)榫癫∪?那么他所立的遺囑無(wú)效。但是,如果是在他神智清醒的時(shí)候訂立的遺囑或者表達(dá)了最終的意愿,而在臨終前他的精神病尚未治愈,那也應(yīng)認(rèn)定他所立的遺囑真實(shí)有效。
第三是對(duì)證人資格的要求。在羅馬,女性不能作為證人為遺囑作證。奴隸在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莊嚴(yán)的儀式前,也被認(rèn)為不能作證。誰(shuí)在遺囑中被指定為繼承人,誰(shuí)就不能成為同一遺囑的證人。此外,證人的職責(zé)只能是對(duì)遺囑行為作證,烏爾比安《論薩賓》第2編:“在遺囑中,被指定為證人的人不能被要求對(duì)非遺囑行為作證。對(duì)這一原則應(yīng)這樣理解:如果證人被要求對(duì)立遺囑之外的行為作證,而后他們又被告知要為立遺囑的行為作證,那么,他們只能對(duì)立遺囑的行為作證。”
第四是對(duì)遺囑形式要件的規(guī)定。羅馬法中明確規(guī)定,訂立遺囑時(shí),必須要有七個(gè)證人在場(chǎng)作證,如果遺囑人不會(huì)寫(xiě)字或者不能寫(xiě),那么,還要由第八個(gè)證人代為簽字。烏爾比安《論告示》第39編:“當(dāng)從同一個(gè)遺囑人處得到封印并對(duì)遺囑加以蠟封后,如同用他人的封印進(jìn)行蠟封一樣,遺囑有效。”而對(duì)蠟印的解釋是最好用希臘人所講的刻有字符的環(huán)形印章,若沒(méi)有環(huán)形印章也可以用其他東西壓印。如果遺囑中有人的簽字不清晰,但是蠟封上的印章是清晰的,那么遺囑仍視為有效。如果對(duì)蠟封好的遺囑啟封進(jìn)行修改后,遺囑被重新封好,且加蓋了七個(gè)證人的印章,那么遺囑仍然有效,如果其中一名證人沒(méi)有出席,抑或是當(dāng)著遺囑人的面,全體證人沒(méi)有重新加封遺囑,那么該遺囑將被視為無(wú)效。
三、中西古代遺囑繼承制度的同和異
(一)相同之處
首先,兩者都反映遺囑的真精神。“因?yàn)檫^(guò)分拘泥于形式規(guī)則的遵守而導(dǎo)致死者的遺囑和最終遺愿變成無(wú)效是不公道的”,“忽視死者意愿的告示,裁判官要保護(hù)死者的意愿,要對(duì)抗由于忽視立遺囑意愿而通過(guò)無(wú)遺囑繼承占有遺產(chǎn)或者遺產(chǎn)一部分的人的狡詐行為。這些人通過(guò)無(wú)遺囑繼承占有遺產(chǎn),并以此來(lái)欺騙依死者意愿應(yīng)獲得遺產(chǎn)的一部分的人,對(duì)他們的起訴,裁判官但接受之。”[2]353
這也正代表了中國(guó)古代明官審理有關(guān)遺囑案件的真精神。在馮夢(mèng)龍所著《智囊補(bǔ)》一書(shū)中,就有杭州知州張?jiān)仈嗬淼囊患z囑案件。一個(gè)杭州城里的富翁,將不久于人世,他只有一個(gè)三歲的兒子。他就讓女婿來(lái)主管他的家業(yè),并寫(xiě)下了遺書(shū),說(shuō)日后分家,把十分之三的家產(chǎn)留給他的兒子,十分之七給予他的這個(gè)女婿。后來(lái)分家時(shí),富翁的兒子告到官府,女婿則拿著遺書(shū)來(lái)應(yīng)訴。張?jiān)伩戳诉z書(shū)后,把它扔在地上,說(shuō):“你的岳父是個(gè)聰明人。當(dāng)時(shí)他的兒子年幼,所以把兒子托付給你,不然的話(huà),他的兒子早就死在你的手里了。”于是命令把富翁家產(chǎn)的十分之三給他的女婿,十分之七留給了他的兒子。[3]951也許故事中省去了對(duì)女婿人品的調(diào)查,很可能他也是個(gè)奸佞之人,有私吞家產(chǎn)的意圖,這也使得法官在作出判決時(shí),傾向于對(duì)富翁兒子利益的保護(hù)。
中國(guó)古代官吏與古代羅馬司法官在審理遺囑案件時(shí),在思想認(rèn)同上有著驚人的相似,這不僅僅是巧合,更說(shuō)明無(wú)論是中國(guó)官吏還是羅馬的法官,在審理遺囑案件時(shí)都把握著一個(gè)相同的準(zhǔn)則——尊重死者訂立遺囑的真正意圖。
其次,都重視遺囑人在訂立遺囑時(shí)的意思表示。中國(guó)遺囑中經(jīng)常會(huì)出現(xiàn)“不是昏沉之語(yǔ),并是醒生之言”,還有“聞吾醒悟,為留后語(yǔ)”等相類(lèi)似的話(huà)語(yǔ)。這就是強(qiáng)調(diào)遺囑人在立遺囑時(shí)意識(shí)是清醒的,而且沒(méi)有受到脅迫,是自己的真實(shí)意思表示。這與羅馬法中所強(qiáng)調(diào)的遺囑人的意愿要真實(shí)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古羅馬時(shí)期,在家父權(quán)的影響下,兒子的立遺囑權(quán)遭到了限制,中國(guó)古代亦是如此。兒子在父親沒(méi)有去世之前,對(duì)家庭的財(cái)產(chǎn)只存在承繼期待權(quán),而沒(méi)有真正的實(shí)體性權(quán)利。自然也就沒(méi)有真正屬于自己的財(cái)產(chǎn),所以立遺囑的可能性也就很小。
復(fù)次,在遺囑人的指定上,兩者間也存在著相似之處。在現(xiàn)存的遺囑原件中,每份都寫(xiě)明了繼承人的名字,沒(méi)有無(wú)繼承人情況下的遺囑。羅馬法中也有一條這樣的規(guī)定:“沒(méi)有繼承人名字的遺囑無(wú)效”。仔細(xì)閱讀前引案例,還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樣一句,“靈惠遷變之日,一仰潘娘葬送營(yíng)辦”。就是說(shuō)在這個(gè)遺囑中還附有一個(gè)條件,在遺囑人死后,要由被遺囑人來(lái)操辦喪事。在羅馬法中也存在著附條件的遺囑,只是所附條件的成就與否關(guān)系到遺囑的效力,而在中國(guó)的遺囑中,沒(méi)有這方面的限制。
(二)相異之處
首先,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形式上的要求。如上所述,羅馬法對(duì)遺囑的形式作了嚴(yán)格的要求,無(wú)論從證人的人數(shù)還是蠟封的樣式。有時(shí),由于形式上的不符合規(guī)定甚至?xí)绊懙竭z囑的效力。而中國(guó)的遺囑其特點(diǎn)就是重實(shí)質(zhì)輕形式,從出土的遺囑原件看,沒(méi)有一件寫(xiě)明證人的人數(shù)、簽字畫(huà)押,遺囑應(yīng)該怎樣保管,由誰(shuí)保管等形式上的規(guī)定。而且,每件遺囑中證人的人數(shù)都不相同,有的僅一兩人,有的多則八九人,并不是所有的證人都畫(huà)押。此外,羅馬法中不允許女性作證,而在中國(guó)這方面的限制是不存在的,有大量的女證人出現(xiàn)在契約原件中。
其次,羅馬法中對(duì)遺囑的時(shí)效作了規(guī)定。尤士丁尼皇帝致大區(qū)長(zhǎng)官尤里安:如果一個(gè)人依合法的方式立了一份遺囑,十年過(guò)后如果他沒(méi)有任何新的表示,或者沒(méi)有任何不同于他過(guò)去的安排的想法,該遺囑有效。可見(jiàn),在羅馬,遺囑的時(shí)效期是十年。也就是說(shuō),遺囑人在生前只要是符合法律關(guān)于立遺囑能力的規(guī)定,在任何時(shí)候都可以立遺囑,而且它的時(shí)效長(zhǎng)達(dá)十年。在中國(guó),沒(méi)有這方面的規(guī)定。從保存下來(lái)的這些原件或樣文中,開(kāi)頭都有這樣的隱諱詞語(yǔ),“忽染疾病,日日漸加,恐身無(wú)常”,“吾今桑榆已逼,鐘漏將窮,病疾纏身,暮年不差”等這樣的話(huà)語(yǔ)。大多立遺囑的人都是在身患重病,預(yù)感不久要離開(kāi)人世的時(shí)候,才立下遺囑,所以也就不存在時(shí)效這方面的規(guī)定。
再次,中國(guó)遺囑的內(nèi)容要遠(yuǎn)比羅馬遺囑的寬泛。羅馬法中的規(guī)定,更多的是對(duì)實(shí)物的處分。而在中國(guó)訂立遺囑的目的則不僅僅是關(guān)于家族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轉(zhuǎn)移的問(wèn)題,還包括通過(guò)對(duì)自己一生經(jīng)歷的描述來(lái)教誨卑親屬,有時(shí)是傳達(dá)某種價(jià)值觀念,有時(shí)甚至是出于對(duì)卑親屬的保護(hù)而故意立遺囑給他人。清代著名文人袁枚的遺書(shū)中,開(kāi)篇就是對(duì)自己童年家境如何艱苦,又是怎樣通過(guò)努力走上仕途之路的敘述。并用這樣的方式對(duì)晚輩作最后的教誨。[4]1-4上面所舉的出于對(duì)年幼孩子的保護(hù)而將遺囑立給外姓人案例,則很好地說(shuō)明了立遺囑人對(duì)卑幼和家產(chǎn)的保護(hù)。
第四,羅馬法中規(guī)定,在宣讀遺囑時(shí),要求裁判官督促參與簽名的證人們聚集在一起,并辨認(rèn)自己的簽名,之后,遺囑要當(dāng)著眾人的面啟封并宣讀之。而在中國(guó),這樣的形式好像極少出現(xiàn)。遺囑人在書(shū)寫(xiě)遺囑時(shí),就把遺囑的副本交給繼承人,作為憑證。只有在打官司的時(shí)候才把遺囑拿出來(lái)作為證據(jù)使用,如果沒(méi)有遇到財(cái)產(chǎn)分配上的爭(zhēng)議,那么就沒(méi)有必要到官府宣讀遺囑。
四、中國(guó)古代遺囑繼承的效力
中國(guó)古代的遺囑繼承有兩種類(lèi)型,即“戶(hù)絕”和“非戶(hù)絕”。《宋刑統(tǒng)》在吸收了唐《喪葬令》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一個(gè)新的有關(guān)遺囑繼承的“戶(hù)絕”條貫,該條規(guī)定了“身喪戶(hù)絕”情況下的法定繼承順序,但遺囑的效力優(yōu)先。換句話(huà)說(shuō),遺囑繼承是以“戶(hù)絕”為前提的,遺囑不得剝削配偶、子嗣的繼承權(quán)。這種情況到了南宋又有了新的變化,遺囑的前提由喪葬令、戶(hù)絕條貫的“身喪戶(hù)絕”改為“財(cái)產(chǎn)無(wú)承分人”。這樣,不但兒子的繼承權(quán)得到了保障,女兒的一般法定繼承權(quán)也得到了保障。對(duì)遺囑的確認(rèn),也由立遺囑人死后“證驗(yàn)分明”,改為立遺囑時(shí)的“自陳,官給公證”。這樣就減少了遺囑糾紛的發(fā)生。可見(jiàn),在“戶(hù)絕”條件下,遺囑的法律效力是毫無(wú)疑問(wèn)的。
但就“非戶(hù)絕”情況下遺囑有無(wú)效力問(wèn)題卻是存在著爭(zhēng)議的。一位歷史學(xué)家認(rèn)為,在非戶(hù)絕情況下,遺囑是沒(méi)有效力的,他寫(xiě)到:“中國(guó)古代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遺囑繼承制度。遺囑繼承制度的產(chǎn)生,以單存的個(gè)人所有權(quán)的普遍化和血親關(guān)系的相對(duì)淡化為前提條件,而中國(guó)古代不具有這些條件;中國(guó)古代的法律僅允許繼承人在‘戶(hù)絕’時(shí)適用遺囑,有子時(shí)則必須實(shí)行法定繼承,與普通意義上的遺囑繼承制度相去甚遠(yuǎn);雖然中國(guó)古代有實(shí)行遺囑繼承的個(gè)別實(shí)例,但不能據(jù)此認(rèn)為中國(guó)古代存在遺囑繼承制度。”[5]本人覺(jué)得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錯(cuò)誤在于將古代的遺囑繼承制度放到了現(xiàn)代法律背景下進(jìn)行討論。這樣才得出中國(guó)古代沒(méi)有“非戶(hù)絕”情況下的遺囑繼承制度的結(jié)論。
在中國(guó)古代,遺囑繼承這種“私約”是一直存在著的,而且效力也得到了官府認(rèn)定。遺囑和其他類(lèi)型的契約一樣,官府一般都遵循“民有私要,官不為理”的契約自由精神。“情理”觀在遺囑繼承案件中的運(yùn)用,《名公書(shū)判清明集》中有一個(gè)很好的例子。一個(gè)叫曾千鈞的人,有兩女,無(wú)子。于是就過(guò)繼曾文明的兒子秀郎為子。臨死前,立遺書(shū),將錢(qián)八百文給二女,當(dāng)時(shí)包括秀郎一等親屬均在場(chǎng)作證,并到官府作了公證。后來(lái),曾文明誣告說(shuō)遺囑為假,欲占有千鈞所有家產(chǎn)。判書(shū)云:“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況文明尚欲子其子,乃使千鈞終不得女其女,于理合乎?”[6]237對(duì)于這種于情于理都說(shuō)不通的案子,判官最終還是肯定了遺囑的效力,對(duì)曾文明等人也作出了嚴(yán)厲的懲處。雖然,法律條文作出了某些限制,但是遺囑不違背倫理和法理精神,官府一般也是承認(rèn)其效力的。那么,何為倫理、何謂法理精神呢?本人認(rèn)為就是中國(guó)古代的那種“情理”觀,這是遺囑的效力得以實(shí)現(xiàn)的大前提。在符合這個(gè)前提下,遺囑是被承認(rèn)的。
現(xiàn)代民法學(xué)中,對(duì)遺囑繼承的定義是:遺囑繼承是法定繼承的對(duì)稱(chēng),它是繼承人按被繼承人生前所立的合法有效的遺囑進(jìn)行繼承的一種繼承制度。遺囑繼承是一種指定繼承,它的效力優(yōu)先于法定繼承,也就是說(shuō),遺囑指定的繼承人也可以包括法定繼承人在內(nèi)。換言之,在有法定繼承人的情況下,也并不排斥采用遺囑繼承的方式。
我們無(wú)論是從中國(guó)古代的遺囑原件還是從案例上,都可以看出遺囑人對(duì)繼承人的指定是有范圍的,一般指定繼承人多是法定繼承人或是家族成員,甚至?xí)龇ǘɡ^承人的范圍。但只要是在古人所認(rèn)定的“情理”之中,中國(guó)古代的遺囑繼承效力是應(yīng)該得到承認(rèn)的。
[1] 張傳璽.中國(guó)歷代契約匯編考釋[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5.
[2] [意]桑德羅·斯奇巴尼.婚姻·家庭和遺產(chǎn)繼承[M].費(fèi)安玲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
[3] 馮夢(mèng)龍.智囊補(bǔ)[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4] 袁枚.袁枚全集(第2冊(cè))[M].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5] 魏道明.中國(guó)古代遺囑繼承制度質(zhì)疑[J].歷史研究,2000,(6).
[6]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點(diǎn)校.名公書(shū)判清明集[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