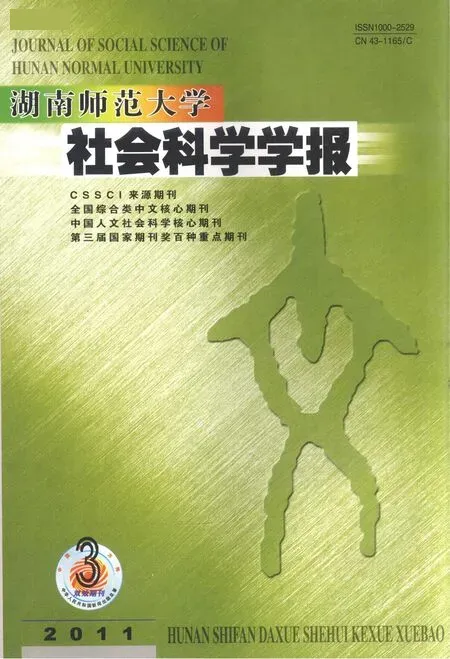存在主義文學的反證式形態:對50-70年代文學的另一種解讀
楊經建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存在主義文學的反證式形態:對50-70年代文學的另一種解讀
楊經建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存在主義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種世紀性思潮已被學界所初識。借助阿多爾諾的“否定辯證法”觀之,50—70年代中國文學其實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反證式形態。這種反證式形態首先體現在藝術哲學理念上理性主義對非理性主義的否定;其二是審美思維方式上呈現為文學反映論與主體間性寫作之分;其三是歷史詩學上的樂觀主義精神與悲觀主義傾向的差異;其四在創作的人文價值立場上或人道主義話語內涵上兩者亦表現出雙向悖反的張力結構:群體共在世相的再現/個體此在本相的敞開,現世建構意識/現實批判理性。
50—70年代文學;存在主義;反證性形態;否定性肯定關系
20世紀中國文學具有存在主義傾向已逐漸被學界所初識,[1]在此基礎上筆者以為存在主義實際上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種世紀性思潮并對其進行了嘗試性探詢。問題在于,20世紀50—70年代是否表征著中國式存在主義文學的創作斷裂期,這是探究中國式存在主義文學作為一種世紀性文學思潮時難以回避的問題。筆者試圖從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是對存在主義及其文學的一種反證式形態進行辨析和解答。這就關涉到阿多爾諾的“否定辯證法”。“否定辯證法”的核心話語概念是“非同一性”。“辯證法傾向于不同一的東西”。[2](P150)在阿多爾諾看來,“同一性”作為傳統哲學的基礎在本體論上表現為對終極實在的尋求,其實質就在于主體和客體的分離。而主體和客體是不可分離的:沒有客體,主體不可想象;沒有主體,客體沒有意義。這恰恰意味著二者的不同或非同一性。[3]在阿多爾諾那里,“不同”是一種分立、平衡、轉瞬即失、有差異的東西,傳統哲學陷入對同一性的沉迷之中,陷入將一切東西還原到一種原始性存在的還原主義之中。[4]阿多爾諾意在將辯證法從歷來的肯定性質中解放出來,因此,通過否定之否定不是達到綜合而是固守于矛盾階段以便努力對其進行思考,依此保留非同一性事物甚至欠缺概念的事物的位置,“辯證法是始終如一的對非同一性的意識。”[2](P3)阿多爾諾之所以“揭示非同一性的存在,是為了確立客觀事物本身具有的特性和力量。個體性的主體需要做的,是在認清體制化強力介入思辨化強力的同時,感受和確信同強力對立的客體本身的力量。因此否定辯證法的籌劃不以主體的解放為目標,而以客體的解放為目標”[5](P299)。
正是憑借以“非同一性”為旨歸的“否定辯證法”觀之,中國式存在主義文學并沒有在50—70年代出現創作上的斷裂,只是以一種反證性形態——“否定性”形態存在于文學創作中。它能使人以反舉對證的方式最終認同一種異己性存在,其實質是構建起對被否定的“不在場”對象的價值重現,即所謂“以客體的解放為目標”。由這種認知邏輯出發可以發現,50—70年代文學對存在主義文學的否定性(肯定)關系的結構大致表現在以下方面。
藝術哲學理念上的理性主義對非理性主義的否定
存在主義的先驅者克爾凱郭爾被認為是使歐洲哲學發生方向性轉折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實現的轉折主要是以孤獨的、非理性的個人存在取代客觀物質和理性意識的存在,以個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特別是厭煩、憂郁、絕望等悲觀情緒代替對外部世界和人的理智認識的研究,特別是代替黑格爾主義對純思維、理性和邏輯的研究。在隨后的尼采哲學中,非理性思維表現為“強力意志”。這種把哲學的本體、認識的對象從客觀世界轉移到人的意志上來的觀念正是非理性主義思維的最典型論證。而將哲學追問的著眼點從西方傳統的實體轉向東方式的“道”,從“什么”轉向“是”,這在海德格爾那里完全自覺和成熟了。海氏的工作就是要讓哲學從存在者回到存在本身,對“存在”的領悟是生存狀態上的領悟——更具體說在“沉淪”、在“煩”和“畏”中領悟“存在”。薩特認定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現象的本質,現象本身就是“存在”;而“存在”的現象是不能靠思維的力量揭示出來的,只能通過諸如“煩惱”、“厭惡”、“焦慮”等非理性體驗來顯示。
存在主義文學因此用非理性的世界觀和美學觀對世界、人生進行自省與觀照,卡夫卡一向被視為克爾凱郭爾以來存在主義思想體系在文學創作中的轉述,其小說反映了諸如充滿荒誕性的現實、非理性和自我存在的徒然、苦痛、孤獨感等存在主義的主題。加繆的《局外人》與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則用截然不同的手法描述了“荒謬”這一生存狀態;兩者相通處在于,最終事理邏輯(理性)被情理非邏輯(非理性)“摁倒”:戈多似乎沒有來,莫爾索似乎被處決。存在主義文學因而探索世界超驗本體的真,揭示生命個體心靈奧秘,展現世界的荒謬或不可理喻的存在及其意義。
而對存在主義文學的非理性主義的否定性體現是50—70年代中國文學的政治理性主義的價值訴求。顯然,50—70年代中國文學的理性主義的價值依據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真理性”的解釋:“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6](P698)這段論述已不單單是一個“政治文化范疇”,還是一個“文學審美范疇”。“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性”的歷史任務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當中國的現代性選擇了“革命”這種激進的歷史實踐方式,50—70年代文學對“革命”的審美敘事和對“繼續革命”的形象演義被視為神圣的藝術使命。如果說,其時的“革命歷史題材”創作通過講述“革命歷史”來提供新的現實秩序賴以成立的合法性資源,解決“革命”從哪里來的問題,那么,“農村題材”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則回答了“革命”向哪里去的問題,或借助主體本質的建構來建立現實意義秩序。正是在極其明確的政治理性主義的導引下,文學創作生發了一整套話語體系和情感結構并成為一種完整的文化理念,它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情感結構以至生活方式、表達方式,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構建了一種強烈的政治認同感和文化整合感,質言之,文學創作的政治理性主義實質上揭示了中國從“現代民族國家認同”到“無產階級國家認同”的歷史進程中的現代性宿命。也可以說,蘊含著強烈的政治理性主義的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極大的本土性、時代性和原創性,因為它僅僅屬于那個時期的中國。
問題也許在于,以崇高的信仰發動的“文革”中所衍生的野蠻愚昧的反理性現象不僅徹底粉碎了文學中曾經有過的種種烏托邦夢想,也使一廂情愿的政治理性主義信仰受到質疑。正是這種政治理性主義的衰落終于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存在主義文學創作的契機。
審美思維上文學反映論對主體間性寫作的否定
就哲學認識論來說,人們面對當前的事物有兩種認識把握方式:一種是“主體—客體”結構方式,由此出發實現由感性到理解的追問;意圖超越感性具體的現實對象而達到抽象的概念世界以把握事物的“相同”。另一種是“人—世界”結構的方式;它主要經由想象、體驗乃至直覺讓隱蔽的東西得以“敞亮”而顯示出事物的意義。顯然,后一種方式具有現代哲學意義上的“主體間性”性質。
存在主義從現實生存活動出發去探索存在的基本方式,強調人的本源的生存方式是“世界”、“人”以及“人與世界關系”的奧秘和深層根據,從而為人類生存提供意義與價值支撐。尤其是,從海德格爾開始存在不再被視為主體性的存在,而是自我主體與世界主體的共同存在。正是在主體與主體的平等關系中人與世界互相尊重、互相交往,融合一體,一種主體間性的存在或存在的主體間性。[7]海德格爾據此提出“詩意地棲居”、“天地神人”和諧共在的思想,這就由認識論哲學轉入存在論哲學亦即構建了本體論的主體間性。由于堅持一種“存在的真理”而非一種“認識的真理”,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學說可視為頗具現代性意味的自我本體論的主體間性。
對問題的進一步審視可以發現,存在論的主體間性對藝術審美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存在論的主體間性關注的是審美何以可能的問題,即審美作為生存方式的自由性或超越性問題。在審美中世界的意義、存在的意義得以顯現,特別是在藝術活動中由于超越了世俗的觀念深入到人類生存層次在對象中體驗了自我,在自我中體驗了對象,從而領悟到了生命存在的全部意義。這樣,由存在的本體論就推導出審美的本體論。所有這些表現在存在主義文學中就是一種智性化寫作的藝術思維方式,即昆德拉所謂“關于存在的詩性沉思”[8](P36)。卡夫卡在《城堡》中一開始便給“城堡”的意象預設了雙重含義:既是一個實體的存在,又是一個虛無的幻象——像一個迷宮,所以這部小說一開始就營造了近乎夢幻的氛圍,這種氛圍對于讀者介入小說世界有一種總體上的提示性。這根植于這樣一種理念:文學寫作通過設置生存的極限情境來觀察人類的存在形態,人類的詩性智慧同人性的本真以及生命的存在形態之間的關聯,正是通過對生存極限情境的勘測而抵達更高層次上的人類生命形態的圓融。“在這里,作為本體性言說的文學與作為本體性言說的哲學具有了同一性,它們都是關于人的生存的本體性情感體驗的言說,即都是對于我們的生存本體的覺與悟……而生存本體言說的文學要能夠作為哲學存在,則應該更清醒地意識到,在充滿生命的、豐富的感性體驗之中,必須有著更為深沉,更為整體性的領悟、悟解,亦即本體之思。”[9]
相反,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的創作思維方式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上的文學反映論。可以說,視文學為反映文學之外的現實的反映論模式在藝術史上源遠流長。即便在“五四”文學時期,寫實主義之“實寫”等于“真文學”的觀念便構成了新文學真實論的理論基礎。不過,“五四”新文學對于反映論的認識與闡述是比較單純的,其主觀目的在于文學具有文化啟蒙和思想革命的實際效用。及至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對列寧式反映論進行了本土化轉譯,但同時也是對“五四”新文學中反映論的合理延伸與自然進化:溝通兩者之間聯系的恰好是傳統文化的集體理性精神和“五四”寫實主義文學的社會實踐品性。這種文學反映論以“主體—客體”分立的認識模式為普適性思維原則,將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反映論作為理論原型。之所以說是“辨證唯物論”的反映論是因其并非被動的鏡像式再現而是主觀能動性的反映,可以表述為邏輯推理的三段式:文藝是客觀生活的反映——強調文學內容的再現性,導致生活決定藝術的結論;文藝是社會生活本質的集中概括的反映——強調文學的認識性、真理性,導致思想先行、內容第一的結論;文藝是按照一定的階級利益和政治路線對生活的能動反映——強調文學的社會意識形態性,導致世界觀決定創作的結論。于是,50—70年代的作家都信奉于唯物論哲學觀基礎上的反映論,并以此作為文藝創造的美學原則。
對于其時文學的主導性創作原則“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來說,唯物辯證法為創作主體宣稱自己所認識的事物是必然而本質的提供了話語根據,而寫出事物的“本質”就是“真實地去表現現實”。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化了的現實主義,它必然要強調另一個根本原則——典型化原則。典型化創作之所以重要全在于只有在典型中現象與本質、個別與一般的辯證關系才能得到藝術上的解決,從而使藝術區別于把本質和一般從現象和個別中抽象出來的各種科學。文學通過典型創造把偶然性和必然性、個性和共性都融為一體,所以使“本質性”的“真實”得到了充分的藝術表述。
問題的實質在于,典型化的思維仍然是由“對立而統一”的唯物辯證法演化的,在典型化過程中革命與反革命、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進步與落后、正確與錯誤、美與丑等壁壘森嚴,黑白分明,鮮明對立,沒有過渡(反對寫中間人物);如果孤立地看,50—70年代的文學作品中雕塑的一個又一個的典型形象可能是動人的甚至是精彩的,但是,如果聯系起來審視必將是,它們將個人與集體、公與私、革命理念與個體情欲、完美無缺的英雄或正面人物與丑陋兇殘的惡棍或反面人物……等歷史和現實生活中人情事理所涵蓋的諸多方面都抽象為二元對立式模式中進行書寫。在這個意義上,回顧50年代末60年代初批判“寫中間人物”以及圍繞“中間人物”的爭論被指認為意識形態立場問題,再將其與哲學界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就很清楚,所謂意識形態立場指的無非是,“中間人物論”這種“合二而一”的思維方式違反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必須反映本質真實的辨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基礎。
歷史詩學上樂觀主義對悲觀主義的否定
無疑,存在主義是西方現代文明危機的產物。而作為一種文明危機意識的存在主義在其世界觀上展現為一種悲觀主義的人生態度和歷史取向。存在主義認為人是世界唯一真實的存在,并從非理性的個人視角出發去審視現實,進而體驗人的存在的孤獨、厭煩、壓抑、恐怖與絕望,感受到世界的荒謬、人生的痛苦、社會的無序與歷史的虛無,領悟到人正在逐步喪失其自然家園、人際家園與精神家園,因而駁斥所謂樂觀主義不過是“對人類無名痛苦的惡毒諷刺”[10](P447)。
由于叔本華把生命意志本身絕對化、神秘化,并使之與現象的個體人生(表象)相隔,而且把道德視為個人自我的生命意志的否定形式,因而他必然導致悲觀主義的結論。海德格爾既否定人生——人生在世是非真正的存在,又否認人死后有任何依托——否認個體與類的統一,人生的出路在于通過心理上“畏”的情緒的震驚才能從非本真的存在狀態中擺脫出來達到本真的存在狀態,保持真正的自我。而“畏死”是達到此狀態的唯一途徑。所謂“畏死”就是要求人在活著的時候,充分認識到死亡是人的終極的、不可逃避的可能性,每時每刻都要有死亡的準備,預先去體驗人面臨死亡的威脅。當海德格爾試圖從死亡中發掘生命存在的意義時,其存在主義則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悲觀主義哲學。薩特50、60年代在絕望之際轉向了“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在《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薩特認為在人的實踐中包含著歷史的總體化。但是,薩特認為歷史的總體化同時又是人的異化,所謂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無非是歷史的總體化和人的異化無限循環的空間。當薩特認為異化是人的永恒的存在狀態時他不啻于一個歷史悲觀主義者。
有論者指出:“卡夫卡的藝術一方面是建立在十九世紀叔本華的極端悲觀主義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又出自尼采對生活和藝術的想象,而這種想象又源于對叔本華悲觀主義的認可。”[11](P110)質言之,存在主義及其文學體現出一種悲觀主義的人生態度和歷史傾向。
相對而言,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的樂觀主義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社會發展觀上,具體表現為政治浪漫主義和文學理想主義精神的結合。
顯然,哲學話語層面的世界觀關注的是存在與意識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核心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馬克思堅信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一種從低級到高級的不斷進化,進而對人類的未來寄予了無限美好的希望。當它與中國的“革命”實踐進程結合之后就構成了一種有關社會發展的神話。這種神話般的存在形態與一種具有歷史終極目的或形而上意義的主題“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糅合在一起,構成了50—70年代中國文學的理想主義的哲學根基和革命樂觀主義的藝術基調。
進而言之,革命樂觀主義文學是一種人對世界與現實的理想主義把握,它排除了人和社會的對立因而呈現出“一元化價值”的文學世界:在內涵上以社會“理想”取代了個人情感。這種樂觀主義的審美情趣不僅是感受主體對外在客體是否符合自己需求而作出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性反應及價值評判,還具有把世界美化的功能。總之,在“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革命終極目標和政治浪漫主義的烏托邦式追尋上,50—70年代的中國也因物質生產的相當貧乏而愈益將(純粹的)精神高揚作為一種廣義的審美解放并把政治浪漫主義與革命理想主義發揮到極致。可以說,“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對已逝的“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描述和表現正是對現實心理的一種提煉與催化。它們使歷史的“理想”基調復活:最終的勝利是屬于革命者的,歷史因此變得無比壯麗。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社會歷史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確立之后,它本身所包含的對生活、對社會、對人生的解釋也就變成了一個思想模式提供給作家;而作家一旦把握了這一思想模式,其樂觀主義的基調就發揮到了極致——革命浪漫主義。革命浪漫主義之不同于一般浪漫主義就在于它的理想是從必然的現實發展中引伸出來的,是有現實根據的,因此,它的理想就是現實,現實也就是理想,這實際上仍然是“存在決定意識”的世界觀使然,也是它不同于一般浪漫主義的地方——與革命現實主義“結合”之處。比如50—70年代中國文學中的“典型形象”何以如今被人貶責為“扁平型”形象,其緣由就在于作家個人的創作超越必須以共同體(階級、人民乃至共產主義)的理想為前提。當人們確認社會主義的現實激發了新的審美理想,由這種審美理想生發的樂觀主義精神便成為文學創作的風格基調,作家們盡情抒寫出舊時代的“終結”、革命的“勝利”、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的“解放”,同時也催生了諸如激昂、壯美、崇高、熱烈、樂觀的美感基調。可以說,文學創作承載的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
人文價值立場上的人道主義的雙向悖反
不言而喻,存在主義是從人的個體生命意識體驗所作出的哲學審視,它起因于現代西方人遭際的文化困境,這種文化困境體現在:一是技術理性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滲透到一切生存領域中的、總體性的、內在的操控和統治機制;二是文化的統治所形成的物化和異化生存樣態也不僅局限于某些被統治階級的命運而是越來越表現為現代人的普遍境遇。社會沖突的焦點從單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擴展到人的生存的意義、價值和根據所代表的文化層面。存在主義作為一種非理性主義哲學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事實上,“存在主義的某些核心問題——如人為什么活著?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個體如何達到本真的自我獲得完美而豐富的存在?以及生命、死亡、自由、孤獨等對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事實上是一些古老而常新的人本問題,是人類普遍關心的問題,對人類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義。而存在主義則在新的歷史文化背景上,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強度重新提出了這些問題,作出了深刻、嚴肅和獨到的解釋。”[12](P241)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也曾經說過:“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就是把人當作人,不當做物,是恢復人的尊嚴。”[13](P2)卡夫卡的創作就企圖用荒誕去暴露人性冷漠的罪惡,并用“人道主義”去關愛生命去為痛苦中的生存吶喊、訴說。而這觸到了20世紀人類文明演進的核心問題。
50—70年代中國文學當然也離不開對人的存在的書寫和表現,不過由于時代語境特別是其意識形態本色,因此只與政治文化領域的革命人道主義發生意義關聯。革命人道主義在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把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起來的產物。“馬克思是擁有著真正的人道主義觀念和思想的,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不是西方哲學中的人道主義哲學的歷史觀的抽象構建,而是對現實的人的發展歷程的倫理關懷和價值訴求……馬克思把這種觀念貫穿于他的整個哲學思想,并希冀無產階級能夠作為這種徹底的人道主義觀念的實踐者之主體,實現對資本主義社會抑制人性的否定以建立真正符合人性和人類發展的社會。”[14]50—70年代中國文學的人道主義是以“建立真正符合人性和人類發展的社會”的現實政治經濟生活為基礎、以人的社會實踐活動為起點、從人的現實本性和歷史本性出發對人自身和社會的發展史進行解說的共產主義原則和唯物主義觀。它消解了存在主義式人道主義觀念。并且,通過這種消解重構起一種新的、革命的、實踐的人道主義思想。當然,所有這些建構在群體性原則的價值立場上——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
如果說,存在主義人道主義強調的是個體性人的存在本體論——對個體“此在”本相的敞開,那么,革命人道主義注重的恰恰是社會關系本體論——對群體共在世相的再現。而對群體共在世相再現的價值準則在50—70年代文學的創作實踐中被強化成工農兵大眾的人性標范(人民性與階級性的結合)和有緣有故的愛和恨——從毛澤東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引申。即如《白毛女》從一個民間傳說到歌劇、電影、舞劇的改編,也就是將世俗化或民間化的善/惡倫理、私人間的恩怨情仇通過“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提升為革命人道主義的意義訴求。
對個體“此在”本相的敞開和對群體共在世相的再現固然是存在主義人道主義與革命人道主義之間否定性關系的識別標志,然而更重要的還在于,這種張力性關系狀態更為實質性的展現則是現實批判理性與現世建構意識之間的反證性對應。
馬克思在論述人的本質時特別提及“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15](P46)。廣義的人是指相對于物而存在的有意識和思維的類,由此可以將其劃分為“類的個體”、“類的群體”及“類的整體”。很明顯,“此在”個體本真狀態的敞亮和自由意志的選擇是存在主義人道主義的價值追求,因而自由從根本上是個人的自由,個人的自由是合乎人性存在的基礎。在這里,個人和群體具有本然對立性,個人自由始終和群體自由構成沖突,存在的自由意志正是在這種沖突和矛盾中演進和發展的。存在主義人道主義以“類的個體”的視角從不同的層面展示現代人的困境、人的存在與本質及對人的終極關懷。進而表現為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文化批判意識,承擔的是個體關懷精神與社會批判功能。
如前所述,存在主義原本就是文明危機意識的體現,而存在主義人道主義對于危機意識的認識基點就是“異化”。異化這一概念一直是現代西方人道主義批判現存制度的一種有效的話語表述。而由異化問題體現出對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關懷所導致的社會批判意識概括起來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是源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異化觀,它把異化與私有制度聯系起來考察并抨擊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現象,寄希望于歷史的總體運動來克服異化。另一類源于海德格爾的人的生存狀態的普遍異化說,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主要著眼于“自己與他人”的共在關系,從他人對自己的異化角度談人的非本真生存方式;晚期的海德格爾則主要從“自己與他物”的共存關系角度談人的非本真生存方式,重點研究人在技術中的異化。而無論是他人對自己的異化還是人在技術時代的異化都著眼于從個體的人,或,海德格爾從“此在”出發去論述存在的歷史性,把異化領受為人之存在的命定形式——是人的普遍而永恒的存在狀態。簡言之,存在主義人道主義的異化論是對現存制度與現實存在狀態的一種文化批判。而藝術作為一種人性在異化狀況下復歸正是存在主義人道主義對現存秩序進行文化批判的審美轉述。
50—70年代文學的革命人道主義是審美觀與倫理觀的兩位一體——文學再現與政治文化理性的交融。它以社會群體——反映在文學上則是具有階級性和人民性的的典型形象為“權力主體”構設人道主義的現實性的價值內涵,從而構建一種一體性的、彰顯歷史進步論意義上的道德實用化社會人倫秩序,并在審美浪漫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的融合下完成烏托邦式人道主義——馬克思預言的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的本質的全面發展的藝術訴求。嚴格地說,這種人道主義訴求并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因而更多地屬于一種藝術審美境界。惟其如此,它才與存在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相反:它言說的是一種“盛世恒言”——旨在文化建設或創世意識。
問題的實質還在于,革命人道主義文學是對群體共在世相的再現,在這里階級性和人民性是“類的群體”的實然屬性。客觀地說,革命人道主義的社會關系本體論源于馬克思主義的的“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8](P18)。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人就是人的世界。”[19](P18、1)更因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是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主導性話語,在這樣的現代性語境中,存在主義式的自由、個人、權利、利己等具有個體性質的話語概念逐漸被集體性質的話語體系所取代,由純粹的個人范疇變成了個人與群體關系的范疇,從而具有限制、責任甚至服從的意味。比如文學對典型形象的塑造就是如此。在典型化過程中集體與個人,公與私,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宏大敘事”與個人化的小敘事,革命理念與個人情欲互不相容。也因此,工農兵大眾的人性標范以及有緣有故的愛和恨在肯定文學創作的人性書寫的現實合理性中,既構建了革命人道主義的藝術審美理念又喻示了革命人道主義的社會倫理法則和文化道德秩序。
[1]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張清華.從啟蒙主義到存在主義: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J].中國社會科學,1997,(6):132-146.
[2][德]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張 峰譯)[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3]王鳳才.為什么說否定辯證法是“瓦解的邏輯”[N].學習時報,2004-03-24,(9).
[4]余治平.差異:《本質與辯證法的誤讀——本體論對認識論的抗爭》,[J].寧夏大學學報,2003,(2):33-39.
[5]張 弘.西方存在美學問題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6]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楊春時.本體論的主體間性與美學建構[J].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2):19-24.
[8][捷]昆德拉.小說的藝術(唐曉渡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9]金 岱.文學作為生存本體的言說——百年來中國文學的反思[J].學術研究,2002,(3):117-121.
[10][德]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沖白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1][英]布雷德伯里,麥克法蘭.現代主義(胡家巒譯)[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12]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13][法]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周煦良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
[14]周 峰.人道主義的超越: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思想研究[J].合肥聯合大學學報,2002,(3):2-9.
[1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責任編校:文 一)
On the Counterevidence Forms of Existentialism Literature: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1950s~1970s Literature
YANG Jing-jin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As a historic trend of 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existentialism has been initially recognized.With the help of Adorno’s“Negative Dialectics”,it should be argued that th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50s to 1970s was a counterevidence form of existentialist literature.First,it is manifested in the negation of rationalism against irrationalism in arts philosophy;second,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of reflection an inter-subjectivity writing in aesthetic thinking;third,the divergence of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historical poetics;fourth,the tensile structure of bi-directional antinomies manifested in terms of cultural value standpoint:representation of the group in objectivity/the individual’s openness in inwardness,secular constructionist awareness/realist critical rationality.
1950s~1970s literature;existentialism;counterevidence form;negative affirmative relations
D091
A
1000-2529(2011)03-0124-05
2011-01-20
楊經建(1955-),男,湖南瀏陽人,湖南師范大學現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