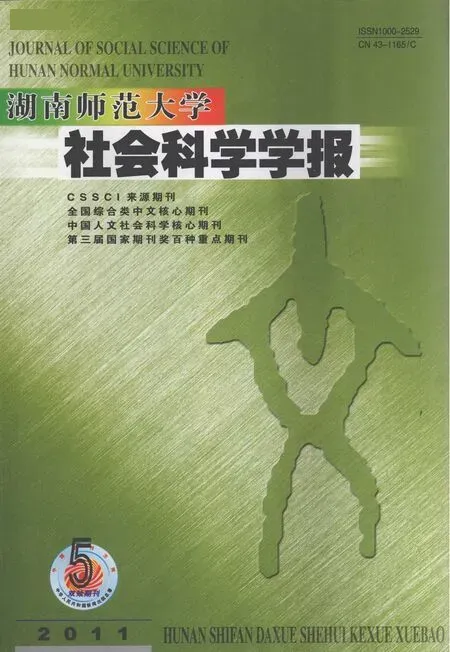尋找公共行政的價值
楊冬艷
(鄭州大學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河南 鄭州 450001)
尋找公共行政的價值
楊冬艷
(鄭州大學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河南 鄭州 450001)
公共行政價值研究既是公共行政倫理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公共行政實踐的現實需要。對公共行政價值的研究基于以下兩個前提:思想基礎和理論前提——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消解;實踐背景——對官僚制工具理性的超越,而運用倫理學方法構建以公共行政正義為核心的公共行政價值體系是公共行政價值研究不容忽視的路徑與方法。
公共行政;價值;二分法;官僚制
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公共行政,效率是其最基本的“善”。“行政科學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人力和材料消耗來完成手頭的工作,因此,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價值尺度中的頭號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學的大廈得以建立起來的價值基石。”[1](P123)然而,這種效率至上的官僚制行政模式摒除管理中的人性化傾向,實行對行政人員的非人格化管理,對道德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持懷疑態度,忽視或摒棄平等、公平、民主等價值,體現為對公共行政“工具性價值”的極端追求,而對公共行政“目的性價值”的極端輕視的行政模式,在實踐中導致了種種弊端,如行政人員在行政過程中出現的人格沖突,行政機構內部官僚主義之風盛行,政府管理社會事務的能力和威信受到質疑等。20世紀60年代末與70年代初,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連續發生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也使得這種效率至上的公共行政模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西方不少學者試圖采用一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論以克服傳統公共行政的弊端,如新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等,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也不斷嘗試著行政范式的變革。我國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目前正處于關鍵時期,對于行政價值的選擇直接決定了我國政府公共行政的模式。一方面我們要學習借鑒西方官僚制所取得的一切積極成就,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西方的行政官僚制,為政府公共行政注入倫理價值,實現公共行政工具性價值與目的性價值的統一。而明確公共行政價值研究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前提,研究公共行政價值體系構建的路徑與方法則是公共行政價值研究的關鍵。
一、尋求公共行政價值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前提: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消解
作為一種思想和方法,事實與價值二分法形成于20世紀初西方理論界的形式主義思潮,直接受到19世紀末新康德主義弗萊堡學派的文得爾班和李凱爾特的影響。然而其基本的思想和方法可以追溯到17世紀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在休謨看來,價值判斷完全在理性的領域之外,因為價值判斷是主觀的。“事實陳述”是能夠“客觀為真的”,而且同樣能夠被“客觀地保證”,相反,價值判斷不可能成為客觀真理和得到客觀保證。因此,當一個“是”判斷描述一個“事實內容”時,那就無法從中導出“應當”判斷。休謨的這種“事實內容”的形而上學構成了從“諸是”(ises)到“諸應當”(oughts)的所宣稱的不可推導性的全部根據[2](P16),從而也蘊涵了事實與價值分屬于兩個相互分別的領域。但正如希拉里·普特南所言:“說到底,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并不是一種區分,而是一個論題(thesis),即‘倫理學’與‘事實內容’無關的論題。”[2](P21)以后這一理論經過邏輯實證主義者的秉承,并進一步地使世界相信“事實”與“價值”的分離是如何地有效和不可或缺,從而認為傳統規范倫理學不是理性討論的主體,盡管他們所秉承的思想家休謨本就是一位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倫理學家。按照希拉里·普特南縝密和細致的思考和研究,無論是在休謨還是卡爾納普那里其理論構建的基礎——關于“事實”的界定都是不能成立的。邏輯實證主義的事實與價值二分法是根據對于什么是“事實”的狹隘的科學想象得到辯護的,正如休謨式原型是根據關于“觀念”和“印象”的狹隘的經驗主義心理學得到辯護的。休謨事實與價值二分法背后的“事實”概念是一個狹隘的概念,在這種概念中,事實就是與感覺—印象相符合的某種東西。而邏輯實證主義的事實與價值二分法不是奠基于對價值或評價的本性的任何嚴肅的考察,他們所考察的“事實”的本性是根據狹隘的經驗主義進行的。用普特南的話說,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概念上看,那些論證起源于一種貧困的經驗主義(后來是同樣貧困的邏輯實證主義)的事實觀。希拉里·普特南不僅從抽象的層面論證了事實與價值二分法何以是拙劣的,作者還從現實世界中無處不在的事實與價值的纏結的重要現象來否定那種二分法。并將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多年以來一直在倡導和捍衛的一種強有力的論證——關于福利經濟學中的倫理問題的理性論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為顛覆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充分的論據,表明評價與事實的“確定”是一種相互依賴的活動。事實與價值是不可分離的,正如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論文集》中所指出的,經濟學的貧困化是與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我曾一再強調,通過更多地關注倫理學,福利經濟學可以得到極大的豐富;同時,倫理學與經濟學更緊密地結合,也可以使倫理學的研究大受裨益”[3](P89)。
對于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產生與顛覆的回顧,是因為“公共行政”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問世正是基于“事實領域”與“價值領域”的分離,當然還有公共行政體制實際運行中存在著的民主與效率之間的沖突這一直接根源。但公共行政與政治的分離在思想根源上直接受到20世紀初科學化思潮的影響,不僅倫理學、政治學內部出現了“事實”與“價值”二元對立的格局,而且將公共行政學從蘊涵價值目標的政治學中分離出來也得益于這種思潮影響下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在某種意義上說,至少從公共行政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問世和研究來說,這種分離是有著其積極性的一面的)。近代以來,政府從混為一體的國家機器中分離出來,專門從事相對獨立的國家意志的執行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行政管理與傳統的統治管理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具有統治性和政治性特征。19世紀末,伴隨著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向城市化、工業化的過渡,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日趨復雜,原有的行政管理越來越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為了適應政府行政從消極走向積極的轉變,以緩和、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穩定并促進社會的發展,迫切需要有一門科學理論來指導政府行政管理活動以使政府更好地履行這一職責。1887年,美國學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基于政治與行政二分的主張,將公共行政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從政治中分離出來,其《行政學研究》一文的發表標志著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威爾遜的行政理論的直接的思想淵源來自當時德國集權政府建立在政治與行政分離基礎上的行政管理理論,因此威爾遜認為公共行政是“一門外來的科學”。之后,美國著名行政學家古德諾(Frank J.Goodnow)為了更進一步闡述政治與行政之間的協調關系以及如何協調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并在他1900年發表的《政治與行政》中明確指出:“政治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4],從而使威爾遜開創的公共行政學更加明確地從政治學中分離出來。馬克斯·韋伯對官僚制的研究,以及20世紀初泰羅對科學管理原理和方法的創設,為威爾遜實現對公共行政的科學化、技術化管理提供了具體的組織安排和管理模式,標志著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形成。在行政學家們看來,政治所體現的是國家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制定是一個價值判斷與價值取舍的過程,離不開政治價值和道德目標的指導”[5](P11),而政府行政不是對政治價值和道德目標的追隨,僅僅是執行已經制定好了的政策,是一個純粹“形式化”、“技術性”的“事實”過程,用威爾遜的話來說,行政管理是一個“實用性的細節”、是“技術性職員的事情”[6]。因此,“行政中立”成為政府行政的基本原則,公共行政只是執行決策的一個“事實領域”,與政治學、倫理學等“價值領域”無關,公共行政所關心的只是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履行行政職能。
但是,不管學者們的意愿如何,也不管實踐者是否承認價值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事實上,公共行政自產生以來,其理論與范式越來越突顯其價值訴求。公共行政作為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活動,無論是哪種理論指導下的行政范式都離不開社會倫理精神的導引,都是一定時代倫理精神的體現。行政與倫理、事實與價值,一直是彼此伴生和互動的兩個方面。由傳統公共行政的以工具性的效率作為核心價值,到新公共行政對公平、民主等人文價值的追求,再到新公共服務以公共利益為核心的價值取向,公共行政越來越蘊涵著對倫理精神的訴求,也越來越傾向于用倫理的視角去審視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倫理精神也越來越成為政府行政乃至整個社會治理體系的靈魂。誠如美國著名行政學家戴維·K.哈特所說:“公共行政并非一項專業技能,而是一種社會實踐道德的形式。”[7]正如阿馬蒂亞·森論證倫理學與經濟學的不可分離一樣,公共行政是不能與價值無涉的,20世紀70年代公共行政倫理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的產生,正是這兩個領域溝通與融合的結果。公共行政倫理學的產生不僅是對公共行政產生之思想基礎——政治與行政二分理論的消解,在其思想淵源上更是對于事實與價值二分這一思想方法的消解,也為我們從倫理的角度審視公共行政、研究公共行政價值開辟了道路。
二、尋求公共行政價值的實踐背景:對官僚制工具理性的超越
“官僚制”,亦稱科層制。“官僚制”的英文為bureaucracy,由法語bureau和希臘語cratos復合而成。bureau的原意是指寫字臺,后引申為官員辦公的地方。后綴cratos的意思是管理、治理、統治。bureaucratie在18世紀已逐漸成為一個普遍的政治學詞匯,并具體指稱實施管理的政府行政機構。官僚制作為一個國家對社會實行統治和管理的組織和行為體系是社會分工的結果,無論是在東方或是西方,作為組織形式的官僚制在古代中國、埃及和晚期羅馬帝國就已經存在。中國古籍中最早出現“官僚”一詞的典籍是《國語·魯語(下)》,文中有“今吾子之教官僚”之說。中國古代的“官僚”與古埃及、羅馬官僚的產生一樣,源自于國家大型工程建設的需要。根據馬克斯·韋伯(Max·Weber)對于中國官僚制的研究,“家產官僚制最初起源于對初潮(vorflut)的治理與運河的開鑿,也就是說起源于建筑工程”[8](P64)。韋伯將官僚制在中國產生的原因歸結為公共工程建設的需要,但中國的官員資格的獲取卻不是由技術或財富決定的,而是以人文素養作為評價標準。“中國歷來最為突出的是將人文教育作為社會評價的標準,其程度遠超過人文主義時代的歐洲和德國的情形。”[8](P127)中國古代的官僚由于缺乏抽象的、成文的規范為基礎的法理程序,行政實施是以理想上的公道觀念為基礎的,所以,中國歷代王朝的行政機構,用韋伯的話來講,是前官僚制的[9](P128)。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中國難以發展出現代官僚制的原因。在現代漢語中,“官僚制”一詞往往帶有貶義,與行政的“低效率”同義,強調該制度下產生的煩瑣公事程序、拖拉工作作風以及泛濫成災的各種公文和會議記錄等狀況[10](P52)。這與馬克斯·韋伯所研究的現代“官僚制”有著本質的不同。在韋伯看來,現代官僚制只能產生于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只有在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才擁有既具合理性又具合法性官僚制的“土壤”——法理型統治的理性國家,中國古代所缺乏的正是這種“合理化”的因素,而表現為一種徹底的世俗主義精神,這樣體制下的官僚制只具有合法性而缺乏合理性。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對于古代中國和歐洲官僚制的比較研究,其目的就是為了他對于現代官僚制的合理性作一種“合理性”的論證。
韋伯對官僚制的分析視角主要是考察官僚制的結構和作用,從分析社會組織結構入手,指出任何組織都是以某種形式的權威為基礎的,并提出歷史上存在著三種類型的權威:個人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和法理型權威。前兩種類型的權威以及依據這兩種權威而作出的支配行為和建立在其權威基礎上的組織都屬于非理性范疇,不宜作為現代官僚組織及其行為的基礎。只有法理型組織才兼具合法性與合理性的特征。作為一種理想的行政組織形式,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型權威基礎上的最有效率、“最純粹類型”的組織形式,其特征表現為:(1)固定的、正式的權限范圍,這一范圍一般由法來加以規定;(2)權威由組織的層級結構和各種等級授予,有一種固定而有秩序的上下等級制;(3)管理有章可循;(4)管理人員專業化;(5)官員有較強的工作能力;(6)公務的管理遵循一般的規律[11](P65)。由上可知,韋伯設計的官僚制是一種理性化、技術化和非人格化的組織體制,為了避免權力濫用,拋棄了人治因素,體現了科學精神與法制精神,在功能與效率上遠遠優于非理性的行政行為。然而正是這樣一種建基于合理性與合法性基礎上的行政組織和管理理論,從它誕生以來,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行政實踐過程中都遭致諸多的詬病,甚至這個理想化的行政模式還被指責為是現代政府失靈的根源。面對公共行政實踐中的諸如政府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政府機構日益臃腫、效率低下、公眾對政府能力失去信心等一系列問題,人們開始對韋伯官僚制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反思,“一方面,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根據韋伯官僚制原則而不斷修繕、建構起來的官僚體制出現了結構性危機;另一方面,也說明韋伯官僚制理論本身存在著邏輯斷裂帶”[12](P60-61)。對于官僚制在實際運行中和官僚制本身存在的這兩個問題,我們需要進行客觀地分析。韋伯是在歷史的敘述中建立其“理性官僚制”的理想類型的,這種理想類型秉承了法理型權威的“理性”要素(形式理性),并將歷史和現實中的具體的個別的官僚制的某些主要特征抽取出來綜合而成,是對現實官僚制的一種抽象與綜合,是思維構造的一種完美理想境界。韋伯在建構官僚制的理想模型時就知道這種模型與現實的差異性,而且在他建構官僚制的理想模型的時期,官僚制也未得到充分的發展并遭遇到結構性危機,因而對于韋伯官僚制的反思,不能僅從經驗事實入手,以經驗觀察的結果來指責概念建構對經驗世界的偏離,這種指責恰恰是對韋伯“理想類型”方法論的偏離。因此,值得反思的根本問題應該是對現代官僚制得以建立的合理性概念的反思。
韋伯從實證主義出發,把社會行為分為合理性行為和非理性行為,其中合理性分為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或稱為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在韋伯看來,實質合理性是價值判斷的基礎,它對行動的目的和后果作出價值評價,是一種關乎倫理主義或道德理想的一種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強調行動的社會道德評價,忽視行動的效率,是一種主觀性的合理性,是傳統社會的本質特征。形式合理性作為一種工具理性是消解了價值判斷、祛除巫魔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以計算為手段并盡可能對于行動本身以及行動所能達到的預期目的進行計算,是一種科學高效、純粹客觀的合理性,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一種合理性。韋伯對于合理性的論說是為建構其現代官僚制服務的,韋伯割裂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之間的關系,將其官僚制理論建立在“純粹客觀的”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的基礎之上。而這種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對立伴隨著理性主義的發展在實踐中又進一步表現為信仰倫理與責任倫理的沖突。韋伯所建構的官僚制在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原則下,片面追求行政責任的制度化設計,官僚制的科層體系僅僅表現為行政官員按章程辦事、受規則約束的運作體系,它遵循的是“形式主義的非人格化的統治”,它“不因人而異”[13](P243,251)。以這樣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合理性是一種“形式合理性”,而不具有“實質合理性”,行政過程是不包含價值、信念的純粹的技術過程,行政官員在這個體制和過程中只是一個工具,只對其所承擔的崗位負責。然而事實上,一個健全的社會必須是建立在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統一之上的,以官僚制作為組織形式的公共行政作為社會構成的一個部分,其產生和運作必定包含著一定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精神,存在著倫理評價和價值判斷,政府行政官僚體系應該是一定社會政治、倫理精神的有效載體。另外,作為公共行政主體的個人也不應該是一個“單向度”的人,尤其是擁有公共權力的行政官員,在行政事務越來越趨于多樣化、復雜化,行政管理的專業性、技術性不斷增強,行政自由裁量權不斷加大的現代社會,其行政過程中“有許多事情非法律所能規定,這些事情必須交由握有執行權的人自由裁量,由他根據公眾福利和利益的要求來處理”[14](P99)。能否及時、公正、有效地行使行政權力,就在于行政主體是否堅持社會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而且行政主體的行政責任不僅源于法律、組織機構、社會以及公眾對于行政主體角色的理性設計和合理期待,而且還源于行政主體出于信念、良知而對于自己角色責任的主觀認同,是一種客觀責任和主觀責任的統一。因此,將公共行政科層體系中的行政主體當作一個沒有良知、沒有價值判斷的“工作機器”顯然是有失“合理性”的,必然會在實踐中遭致種種詬病。
在20世紀后期西方各國的政府改革和諸多“摒棄官僚制”理念的浪潮中,人們已開始注意到官僚制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的中立性帶來的問題,開始了超越官僚制工具理性的思考,西方公共行政理論與范式的不斷發展與變遷,以及行政倫理學的產生都昭示著公共行政倫理價值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斷為公共行政組織注入價值理性。
三、公共行政價值研究的方法和路徑選擇
20世紀70年代以來,雖然伴隨著新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興起,公共行政學界越來越重視對于公共行政價值的研究,公共行政倫理學的應運而生就是對傳統公共行政忽視價值研究的回應。然而,總體上來看,公共行政倫理學研究較為關注對行政實踐問題的倫理探討,缺乏對行政倫理基礎理論形而上的思考,對于行政價值的研究也往往是基于學者各自不同的學術立場,尚未形成完整、統一的行政價值體系。筆者認為,研究方法是存在于理論體系之中的,一方面理論體系通過方法來表達,另一方面,方法本身也是理論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行政學、公共行政倫理學研究上的不足,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上的滯后與不完備。即使是公共行政倫理學,雖然關注公共行政價值的研究,但價值只是作為其研究內容被考量,缺乏用倫理學的方法去探究和建構公共行政價值體系的嘗試。因此,無論是公共行政學對于價值研究的關注,還是公共行政倫理學基礎價值體系的構建都不能忽略倫理學方法。只有充分利用人類歷史上豐厚的倫理學資源,不僅要在公共行政研究中貫穿倫理精神,更應該將倫理學方法應用于現實的公共行政研究來表達公共行政本身的倫理特征,倫理學方法和路徑選擇是公共行政價值研究不可或缺的維度。
博登海默在他的《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的前言中說道,“對一般法律理論的實質性問題所作的論述,乃是以某些蘊含在我研究法理學問題的進路中的哲學假設和方法論假設為基礎的”[15](P11)。同樣,對于公共行政價值的研究也應該將倫理學方法作為表達公共行政價值的實質性內容的基本立場、維度和視野。不僅如此,對于公共行政價值的研究必然與人類社會關系中最為重要的價值訴求——正義相聯系,正如博登海默緊接所指出的,“這些假設中最基本的一點也許是這樣一種觀點,即任何法理學專業論著都不應當回避或忽視那些與在人際關系中實現正義有關的重要問題,盡管任何企圖用客觀的標準處理這個問題的做法都會遇到困難。我們認為,法律的功能乃在于促進這些人類價值的實現,因此,如果法律理論和法律哲學忽視這些人類價值,那么它們肯定是貧乏的、枯燥無味的。”[15](P11-12)公共行政作為一個“與在人際關系中實現正義有關的重要問題”,公共行政價值研究必然是與正義價值緊密相關的一個研究領域,雖然形成客觀的標準解決處理公共行政價值問題是有困難的,但倫理學方法必然成為公共行政價值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且公共行政價值研究必須體現正義的主題。也就是說,對于公共行政價值的研究,應該將“正義”作為其核心而展開,公共行政正義是公共行政首要的、核心價值。
倫理學是一門哲學理論科學,“倫理學研究社會道德現象不能停留在簡單的道德事實的記錄和單純的描述上,而是要深入到道德現象內部去揭示其本質和發展規律”[16](P9)。公共行政價值研究中倫理學方法的運用必須緊緊圍繞公共行政產生、發展的客觀基礎——公共行政權力而展開,通過揭示公共行政權力的本質特征和內在矛盾,抽象出“公共行政正義”的一般概念。在此基礎上運用倫理分析的工具進一步闡發“公共行政正義”的多元倫理維度。因為公共行政正義具有綜合的品質,能夠具體表達其他公共行政的重要價值,如效率、平等和公共利益等價值。公共行政正義作為公共行政首要的核心價值,它的功能是幫助官僚制通過普遍接受的和為統治政體價值所認可的合法的實踐服務于社會正義的目的。也就是說,當官僚機構以追求正義的目標行動時,正義要求他們為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有分歧的倫理和價值提供一種統一的分析視角,并在最終的價值追求上達成一致。公共行政正義不僅表征了行政本身的價值訴求,也體現了對行政主體的倫理要求,既體現了公共行政的工具性價值也是其目的性價值的體現,是公共行政正義的義務論、目的論和德性論三重倫理維度的有機統一[17]。不僅如此,“倫理學是一門特殊的實踐科學”[16](P12),對公共行政的倫理學闡釋不能脫離開公共行政的實踐本身,現實中公共行政正義的客觀存在本身就是多重維度的,只有采用不同的倫理視角去關照才能夠客觀地反映其實際存在,才能避免研究方法上的偏執并保持理論構建的完備性。公共行政正義作為行政倫理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公共行政實踐的核心價值要求,對于社會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18]。因此,對于公共行政價值研究的路徑選擇除了倫理學分析方法外,還必須克服西方有些學者在研究中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立場、各自為政的現象,必須對公共行政自身價值內涵進行深入挖掘,并整合公共行政正義不同維度的指向,形成以公共行政正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研究路向。
[1]Robert A.Dahl.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ree Problems[A].Jay M.Shafritz and Albert C.Hyde (eds).ClassicsofPublic Administration[C].MoorePublishingCompany,inc.OakPark:Illinois,1978.
[2][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實與價值二分法的崩潰(應奇譯)[M].東方出版社,2006.
[3]Amartya Sen.On Ethics and Economics.Oxford:Blackwell,1987.
[4]Frank J.Goodnow,Politicsand Administration:A Study in Government.New York:Russell&Russell,1900.
[5]郭夏娟.公共行政倫理學[M].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
[6][美]伍德羅·威爾遜.行政學研究[J].國外政治,1987,(6):32-37.
[7][美]戴維K.哈特.善良的公民,光榮的官僚與“公共的”行政[J].公共行政評論,1984,(44 卷):116.
[8][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9][英]馬丁·阿爾布羅.官僚制(閻步克譯)[M].北京:知識出版社1990.
[10]丁 煌.西方行政學理論概要[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11]H.Gerth and C.Wright Mills.Essays in Sociology.Oxfoed :Oxfoed University Press,Inc.1946.
[12]張康之.尋找公共行政的倫理視角[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
[13]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14][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16]唐凱麟.倫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7]楊冬艷.西方公共行政及其正義價值[J].倫理學研究,2007,(2):102-106.
[18]郭漸強,劉 薇.實現政府公共性的倫理思考[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2):37-40.
In Search of the Valu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G Dong-yan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China)
The valu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ics,but als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lue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premises: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dissolution of the dichotomy between fact and value;the practice context——surpassing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bureaucratic system.The application of ethics for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s value system which takes justice as the core,is the route to research the valu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at can’t be ignored.
public administration;value;dichotomy;bureaucratic
B82-051
A
1000-2529(2011)05-0039-05
2011-04-18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公共行政核心價值研究”(09BZZ026);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服務型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優化研究”(2010-JD-008)
楊冬艷(1964-),女,湖北云夢人,鄭州大學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哲學博士。
(責任編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