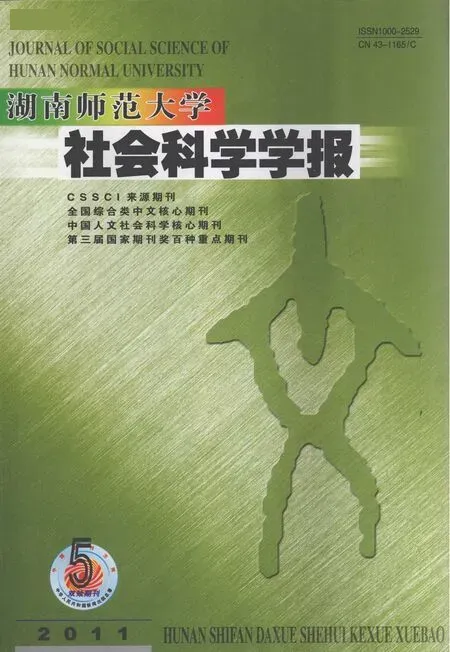新世紀“底層寫作”對在鄉農民的生存觀照
鄭明娥,田中陽
(1.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2.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新世紀“底層寫作”對在鄉農民的生存觀照
鄭明娥1,田中陽2
(1.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2.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新世紀文壇上“底層寫作”日趨興盛,對“在鄉農民”生存狀況的觀照和深刻揭示成為當下文學創作的一個新亮點。對個體在鄉農民的物質和精神困境的展示,主要體現在精神愚昧的時代特征、城鄉差異以及新的干群關系沖突等方面,讓讀者看到了新世紀作家強烈的現實關懷意識和悲憫情懷。
在鄉農民;生存書寫;城鄉差異;現實關懷
“底層寫作”在新世紀文壇上漸成熱點并日益顯出其活力,其中底層“在鄉農民”群體也是新世紀文學關注的重點,作家對他們的生存現狀、命運遭遇及所處的現實環境的書寫,流露出作家對弱勢群體的悲憫情感和現實關懷。
一
自90年代的市場化社會轉型以來,尤其是在新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曾經是改革的受益者的農民,在這新一輪的變革中被邊緣化。農村雖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在鄉農民的相對貧困依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貧困是相對于同時代不同階層的生活水準而言的,或者說,它更多的是人們的一種貧困感,而這種貧困感切實影響著人們實際的生存狀態。首先,對于這些以務農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低收入群體來說,其生存的貧困與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緊密相關。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小說”被譽為底層寫作的代表,其作品在展現神龍架大山中種種令人望而生畏的自然環境的過程中,更揭示出在鄉農民被無情逼迫到狹小生存縫隙的現實。其小說《望糧山》向我們展示了蠻荒、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農民命運的沉重和生存的窮苦。在那個土地貧瘠、天災不斷的鄂西北的望糧山,村民始終固守那片苦澀的土地,為了生存,他們種麥子、栽苦蕎,甚至不惜冒著跳崖斷命的危險去侵犯國家財產,砍伐原始森林。“賺錢”是他們對生活的唯一渴望,“求生”是在鄉農民生命的本能。但主人公金貴不僅與土地抗爭失敗,進城及其種種嘗試和掙扎也是屢試屢敗,從而留守土地、安于殘酷的生活現實和生存的窘境,成為他唯一的無奈選擇。
其次,在鄉農民深情眷念家鄉熱土,希冀在對土地的真誠堅守中實現自己求生的愿望,但鄉村惡勢力和腐敗權勢卻往往成為扼殺他們的淳樸愿望的“劊子手”。關仁山《傷心糧食》講述的是“豐收成災”、“谷賤傷農”的悲劇。村里催交提留款,豐收的糧食卻積壓賣不出去,主人公王立勤在艱難地利用農民協會賣糧換錢之后,卻又落入假化肥制售者的陷阱,而呼風喚雨、見風使舵的“地頭蛇”和鎮書記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更令他傷心絕望,最終導致他憤而燒掉糧食,背著母親逃離家園。固守土地的農民在惡劣的環境中,以生命的毅力來求得豐收,但豐收并不能讓他們幸免某種人為的苦難。
與生活艱難、貧困相伴隨的,還有其思想意識的落后和麻木。本來,新的農村政策足以讓農民感受到生存的新前景,但在某些地方,國家的“扶貧”往往會釀成荒唐的鬧劇。夏天敏的《好大一對羊》就是這樣的一個明證。木訥憨厚的德山老漢是千千萬萬底層農民的縮影,他居住在大山高寒地帶,環境惡劣,生存所需毫無保障,總是處在半饑餓狀態;面對扶貧官員的“恩寵”,他感激涕零,在近乎面對神靈般的敬畏中更感自己卑弱渺小。“奴性使農民德山產生了超乎他生命本身價值的幻覺,他始終以報恩的心態去償還劉副專員的恩德。”[1]在盲目的憧憬中,他將養羊作為高于女兒生命甚至高于全家生命的神圣使命來完成。送給他一對羊本來是為了讓他脫貧,但在鎮領導的功利追求中卻無聲地演變為一場災難和空前的痛苦:養羊成了有名無實的荒唐鬧劇,德山老漢也成了犧牲品,不僅沒有致富,反倒變得更加貧窮。這一方面深刻反映出農民思想意識的愚鈍、閉塞、落后、盲目,但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現實的另一面,即官員的權利欲望與蒙昧農民對權力的膜拜,加速了這種生存悲劇的釀成。向本貴的《農民劉蘭香之死》與此異曲同工。作品圍繞縣領導欲幫助農民脫貧致富的扶貧行動卻反而將農民劉蘭香逼上死路一事而展開,通過對事件來龍去脈的描述和“追問”,農村的現狀和“潛規則”駭人聽聞。劉家因為沒用豐盛的飯菜招待扶貧人員而得了壞名聲,受到村主任的批評和村里人的嘲笑,這個貧苦卑弱的女子無力承受村人惡毒的話語攻擊與侮辱。鄉間倫理和權勢腐敗的交易共同構成了悲劇的同謀:前者反映出封建殘留思想對農民意識的深刻影響,后者又將它進一步引向愚昧的迷途,二者的無意合謀便成為主人公生命悲劇的“無形殺手”。作家不但寫出了在鄉農民生存環境的惡劣和物質生活的艱難,也從一個側面深刻地反映出精神的貧困和蒙昧更是在鄉農民不幸和苦難的癥結。
二
作家對底層民眾懷有深刻的同情和熱切的關注,是諸多底層敘事小說最鮮明的情感傾向。作家在以悲憫為情感基點的真實呈現中體現出濃厚的現實關懷。這種樸素直白的關切之心和悲憫之情,深深震撼著讀者的心靈。“對于處于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充滿由衷的同情、關懷、熱愛甚至敬意,永遠是偉大作家的基本態度,是一個時代文學精神健康和成熟的基本標志。”[2]現實關懷是文學至關重要的情懷,當下中國作家能夠聽到農民的嘆息,看到農民的淚水,書寫農民的辛酸。在那些關注底層的作家筆下,“生存的現實和悲劇的命運已經上升為創作的第一需要了。”[3]作家們對底層在鄉農民的深情書寫就是一個最好的詮釋。有學者曾說:“文學到底是維系著人生的,它總是人生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具象的或抽象的畫圖。”這是有道理的,但他認為“之所以重提‘現實關懷’這一‘古老’的命題,是有感于時下文學的嚴重缺失”[4]。這就不符合時下文壇的真實狀況了。
在鄉農民的生存書寫,讓我們感同身受農民生存的舉步維艱;同時也由于觸及了時代敏感問題而引起了人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這種現實觀照可謂尖銳而厚重。《望糧山》中的金貴輕易相信外地人的話,剛剛嘗到賺錢的“甜頭”便被人騙走了十多斤黃連素粗粉和一些現金,他們得知事情真相后狂追不舍,可騙子早已逃之夭夭。金貴在感到現實無路可走時,不遠萬里“尋娘”,遭到已身為煉鋼廠經理的母親的無情奚落,還被工友痛打,現實給主人公的生存似乎布下了天羅地網。這張無形的現實之網默默影響和制約著人物的現實生存,讓他無法擺脫物質的貧困和思想的局限。而《傷心糧食》中的王立勤想利用豐收的糧食為民謀福利,但他沒想到村上霸王王福山與村長、鎮長勾結,又買通了新來的鎮書記,讓鎮農協一夜之間成為烏有,而他王立勤瞬間也就變成了無業游民,他也由于理想破滅而不得不選擇放棄。作家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盡情捍衛底層人物的利益,原本想給農民一條求生的出路,但在殘酷的現實中,主人公義憤填膺地踏上了逃離家園之路。作家的救贖意識中也就包含了一種對鄉村的失望。夏天敏、向本貴等作家將目光聚焦在鄉村亙古不變的倫理和至高無上的權力腐敗上,提出了一個在底層鄉民生活中亟待解決的敏感的社會問題。“扶貧”的初衷是讓農民脫貧致富,孰料在實行過程中卻上演了荒唐的鬧劇和慘不忍睹的悲劇。德山老漢對權勢莫名崇拜,使他盲從地任憑“官員”和村里“領導”擺布,自己的努力只為迎合和討好權勢者的扶貧政績,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他的悲劇的發生。而農民劉蘭香可謂“不識時務者”,忽略鄉村的倫理,沒拿好飯菜招待縣鄉訪貧問苦的領導,受到村領導的責難和懲罰。層層權力織成了一張嚴實的現實生存之網,讓身在其中的他喘不過氣來。壞名聲意味著失去領導的青睞,意味著很大的經濟損失,壞名聲意味著鄉、村領導“治民”無方,所以要不惜一切去洗清。傳統的鄉村倫理與現實的權力腐敗相聯姻,共同催生了一幕幕荒誕的鄉村悲劇。相比之下,閻連科則是把農民爭先恐后替領導“頂罪”的鬧劇,以及城里人“認干兒子”的巨大反差,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手法揭示農民生存的貧窮、悲慘。在這里,作家們不僅僅是為農民的遭遇辛酸而慨嘆,更能激起讀者對腐敗權勢的憎惡以及對這一社會問題的反思。這種現實關懷與之前的“新寫實小說”相比,多了一份擔當與厚重,少了一份旁觀與淺薄,多了一份溫情與悲憫,少了一份冷漠與無奈;可以說,作家們是摒棄了“情感零度”的敘事新潮,以親身體驗底層生活的經驗為基礎,并以主動介入的姿態,在對苦難的書寫中實現對底層民生的人文關懷。
三
在底層寫作中,我們會無一例外地認為作家的寫作立場不再是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而是與作品中的人物處于同等位置的“平視視角”,也就是說,作家以“民間立場”去關注那些在極度窘困的生存境況中艱難掙扎的在鄉農民。正如張韌所言,作家面對底層不是居高臨下的俯視,也不是站在邊緣的觀賞和把玩,而是以平民意識和人道精神對于灰暗復雜的生存境況發出質疑和批判,揭示底層人物的悲劇人生與人性之光[5]。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感受到作家滿懷對農民的深情以及殷切的現實關懷,同時也不難體會到另一種社會現象即城市與鄉村、貧窮與富裕、農民與知識分子之間某種程度上的差距和矛盾,以及這種差距和矛盾對農民生存產生的潛在影響。
在中國這個有幾千年農業文明傳統的國家,在現代化、城市化轉型期出現城鄉對立現象是必然的。這自然會引起作家的關注。比如在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中,探礦隊長和九財叔的關系,其實就反映著這種特定時期的城/鄉、貧/富、農民/知識分子的矛盾關系。這種關系在作品中甚至還表現為雇傭者與被雇傭者、強勢與弱勢之間的隔閡與沖突。最終導致的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案,就與這種隔膜和沖突逐漸加深和惡化直接相關。但作家已跳出了長期以來盛行于文壇的那種“文明與愚昧的沖突”的思維窠臼,主觀傾向的重心在向不無“愚昧”的弱勢者傾斜。小說塑造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勘探隊隊長這個“城市人”形象,突出了他那種對鄉下人的精神上的絕對權威感和優越感,以及由此而來的多疑、缺乏同情心的心理特征。而以兩位挑夫為代表的農村人,承受了城市化進程中的利益被剝奪,尊嚴受損,由此逐漸惡化為失去理智,其瘋狂的復仇行為最終導致生命悲劇。這種傾向在《好大一對羊》、《農民劉蘭香之死》等作品中也有大致相近的表現。農民在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中處境頗為尷尬,在經濟、文化及人格諸方面都處于弱勢地位。而身處工業化、市場化中心的“城里人”與處于其邊緣地位的“在鄉農民”之間,身份的懸殊以及文化思想之間的距離依舊明顯。這種城鄉差異、貧富差距,再加上干群關系的失衡等,都是造成德山老漢傾家蕩產、劉蘭香生命悲劇的深層因素。閻連科的《黑豬毛 白豬毛》中的在鄉農民的精神悲劇,就是在深層次上反映出他們不僅是現實物質利益的受損者,也是城鄉差異的直接受害者,更是特權和封建意識殘余的犧牲品;新世紀的農民依然難以跨越和繞過這種種差異沖突對他們的有形和無形的鉗制,而這種鉗制又直接影響著在鄉農民的精神愚弱和生存的窘迫。
綜上所述,新世紀文壇的底層寫作不僅在關注著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生存現狀,也及時而敏銳地發現了在鄉農民所遇到的各種新的困擾。新世紀的農民在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而多有獲益的同時,也有種種新出現的以及傳統的、殘留的難題,種種外在的局限和自身根深蒂固的弱點,依然頑固地橫在他們面前或滯留在他們的意識深處,依然是他們擺脫物質貧困和精神愚昧的巨大障礙,甚至成為他們依然作為“弱勢群體”的一種標志。底層寫作對在鄉農民的這種關注和書寫,也從一個側面昭示著新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堅毅的延續和拓展。
[1]王 劍.夏天敏的悲憫情懷[J].名作欣賞,2006,(3):61.
[2]李建軍.寫作的責任與教養——從《中國農民調查》說開去[J].文藝爭鳴,2004,(2):68.
[3]丁 帆.論近期小說中鄉土與都市的精神蛻變[J].文學評論,2003,(3):33.
[4]謝 冕.重提文學的“現實主義”[N].解放日報,2000-10-16(3).
[5]劉 震.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的兩種范式與新的可能性[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82.
“Bottom Writing”of the New Century Concentrates on the Living of the Countryside Peasants
ZHENG Ming-e1,TIAN Zhong-yang2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2.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i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Focusing on and revealing the survival condition of township peasants,it has become instantly a new high light,with the“bottom writing”of the new century’s literary flourishing.The individual township peasant’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will be disclosed from several aspects.It mainly reflects in the times features of the ignorant spirit,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the conflicts of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dres and the masses etc,which allows readers to see the new century writers’deep realistice care and sympathetic feelings.
township peasant;survival writing;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realistic care
I207
A
1000-2529(2011)05-0128-03
2011-03-20
鄭明娥(1975-),女,湖南懷化人,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田中陽(1954-),男,湖南湘鄉人,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校: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