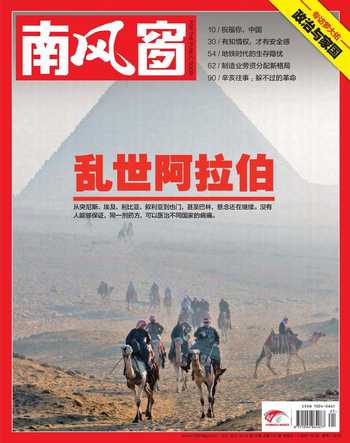基層民主參與為什么重要
張洪彬
不少人把民主等同于選舉代表。這種熊彼特式的看法,歷來批評不斷。盧梭早就批評過:“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王紹光嘲諷代議制民主只是投票選出主人的“選主政治”,也可謂一針見血。在政治冷漠席卷全球的今天,這些批評就尤其值得認真對待。然而,在現代社會提倡直接民主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現代民族國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根本不可能聚集到一起議事。代議制幾乎是唯一可能的選擇。
不過,代議民主必須是有根基的,否則如上種種批評就很容易不幸言中。托克維爾考察美國的民主,非常敏銳地看到了美國民主政治深深植根于新大陸殖民地的鄉鎮。復旦大學任軍鋒在哈佛大學訪問期間,就此主題深入研究,并充分汲取相關研究成果,寫成《民德與民治:鄉鎮與美利堅政治的起源》一書,全面考察了新英格蘭鄉鎮的起源、政治建制、對美國建國的影響、與現代政治理論的關系,要言不煩,且處處可見其對中國現實的關懷,因而頗具啟發性。
新英格蘭的鄉鎮宛如一個個小型的自治共和國,其政治建制包括鄉民大會、行政理事會、專門委員會,其功能頗類于議院、國務院及政府各部門。通過鄉民大會的討論和協商,鄉鎮居民在所有關涉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務上發揮影響力,諸如橋梁的興建、街道的命名、公共墓地的位置、垃圾的處理;即使其意見最終未被采納,也因知道被采納的意見理據何在,而更容易服從。行政理事會和專門委員會獲得鄉民大會的廣泛授權,同時受到全面的監督和制約,憲政觀念深入人心。在鄉鎮的政治建制中,統治與被統治合二為一,這也正是民主自治的本義所在。這些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政治實踐,使民主成為具體可感、可參與的民主;對公眾事務的持久參與使公民學會務實、負責、積極、自律、傾聽、溝通、協作、服從,長期的政治實踐教會公民如何授權,如何限權,因而鄉鎮的民主參與是最好的公民訓練課。
小共同體中充分而廣泛的民主參與,是美國代議制民主的深厚根基。若非如此,選舉“代表”可能就真的容易淪為選舉“主人”,民主也就變得抽象、邈遠。所幸的是,新英格蘭鄉鎮的政治精神深深滲透到美利堅建國歷程中,并在政治建制上充分保障了地方小共同體的獨立性,因而國家乃是鄉鎮的自然延伸。
傳統中國皇權不下縣,地方原生社群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自治。然而在建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權力一竿子捅到底,這些自治的小共同體被視為國家建構的障礙,摧折殆盡。在近30年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和鄉鎮急劇凋敝,城市迅速膨脹,人口快速流動,熟人社會解體,原生共同體更近乎蕩然無存。其結果是政治喪失了一個觸手可及的人文尺度,民主很容易被抽干成“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樣的教條,變成投票箱前的儀式,從而淪為“選主政治”;再者,沒有小共同體、缺乏公共參與的人民就像一袋馬鈴薯,彼此擠壓卻又互不相干,在只手遮天的“利維坦”面前,不堪一擊。
普通公民若不能對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公共事務發生影響,一方面感到被排斥,另一方面卻不得不承擔其后果,疏離、冷漠、自私、忍受、怨毒就成為常態,直至忍無可忍,社會就又進入動蕩不安的狀態。我們需要在居民區、企業、學校、社團等層級建立小型自治共同體,為民主政治建立具體而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