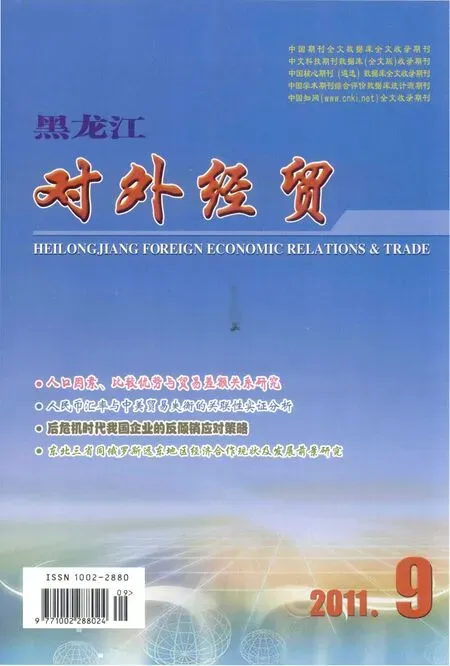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環境效應分析
金 秀 王正宇
(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污染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影響問題,國外理論界有個備受爭議的“污染天堂”假說。其主要觀點是:發達國家非常嚴格的環境標準使得跨國公司生產成本上升,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跨國公司就把這些污染環境嚴重的產品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從而使得資本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更多的FDI會降低環境標準。這個觀點暗含了FDI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雙向關系:較弱的環境管制吸引了污染密集型產業,而污染密集產業的進入又加劇了東道國環境污染的惡化。
Gtossman和Kruege(1991)提出了FDI改變東道國環境的三種效應的影響機制: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Anayotou(2000)進一步補充為四種效應方式: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以及管制效應。本文從這四個方面對FDI對我國的環境影響進行簡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
外資進入我國是從1979年開始的,在三十多年的時間內迅猛發展。1979—1982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額僅有17.69億美元,2002年達到527.43億美元,2010年實際使用外資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057.4億美元。
在地區分布上從少數沿海城市和特區擴展到國內大部分地區,并呈“東高西低”的格局。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地區差異表現得十分突出。當時東部地區吸引FDI為29.7億美元,占比高達93.9%,中西部的比重分別為3.87%和2.26%。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央政府提出了“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采取多項優惠政策鼓勵外商去西部和中部投資。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西部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提高了這些地區吸收FDI的比重。截至2008年底東部地區FDI占全國比重為83.28%,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FDI比重分別為10.64%和6.06%。
在產業領域,允許FDI進入的行業不斷擴大,形成了一個從數量小、范圍窄、限制多的試點階段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全面開放的格局。外商投資企業遍及第一、二、三產業的幾乎所有行業。
到目前為止,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的基本格局是: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很小,第二產業占主導地位,第三產業的投資呈迅速上升的趨勢。由表1可知第一產業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很少,且生產技術和效益都不高,與此同時,在第二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在2008年外商投資項目的產業中,制造業所占的項目為11568億美元,占總項目比重42.01%,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98.95億美元,比重為46.07%。由此可見制造業已成為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第一大產業。在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行業和社會服務業,其次是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業和金融保險業等。

表1 截至2008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情況表金額單位:億美元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環境效應分析
(一)技術效應
FDI的技術溢出效應是指FDI的技術擴散對環境的影響。FDI為那些解決特定的生態問題的環境技術和服務在全球的擴散提供了機會。當使用環境友好技術和有效率的管理技術時,技術效應對環境就表現為正效應,反之就表現為負效應。
Blaekman&Wu(1998)對中國電力工業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環境績效的研究發現,由于先進的發電技術和環境管理以及中國本土企業和FDI企業的競爭,FDI提高了中國電力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廢物利用量。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近代工業發展較為緩慢,技術非常落后。改革開放以來,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引入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這些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落后技術自身的缺陷。以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工業增加值表征工業污染的密集度,歷年工業增加值按照1992年不變價格計算。圖1顯示了1991—2007年我國工業污染密集度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工業污染各個指標都呈現了大幅度的下降。說明這些先進和環境友好型技術的應用降低了我國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降低了我國工業的污染排放水平。因此,在這方面,FDI對我國環境的影響是正面的。

圖1 中國工業污染密集度的變化
(二)規模效應
規模效應是指FDI導致的經濟規模變化所造成的環境影響。通常認為,FDI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帶來經濟規模的擴大,生產和消費規模的擴大意味著需要投入更多的自然資源和能源,排放更多的污染物,對環境產生負效應。其次,FDI會促進當地GDP的增長,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增強人們環境保護的意識和努力程度,從而有利于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對環境產生正效應。
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還處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左側,未跨越拐點,FDI的規模增加只會加重環境的污染。而FDI的二元特征決定了FDI無論在區域上還是產業上都比較集中,區域上主要集中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上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的制造業。這種分布特征加劇了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陡峭程度,使得每個單位的國民生產總值排出的污染量遠遠大于其他同等國民收入的國家。由此,FDI在這方面對我國環境的影響表現還是負效應,尚未顯現出積極的環境效應。
(三)結構效應
結構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行業組成對投資所在地環境的影響。經濟結構升級的環境影響可正可負:如果一國經濟處于工業化階段時,自然資源開發、重化工工業是FDI的主要投資產業,將帶來不可持續資源的加速耗竭,結構效應是消極的;若一國經濟處于后工業化、信息化和知識化階段時,如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將帶來更小的環境壓力,結構效應是積極的。
從行業結構來看,我國的FDI目前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工業各行業污染排放強度差別較大,約有88%的FDI工業增加值集中在污染密集型產業,其中有30%是重度污染密集型產業。這樣的引資結構無疑對我國的環境產生更多的損害,會加劇污染的排放。不過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的經濟結構也漸進合理化。自2006年以來,我國吸引的工業制造業FDI份額和污染密集型行業FDI產值份額都有所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整個工業的污染排放。而且,從長期來看,第二產業的FDI會逐漸飽和,逐漸轉移到第一、第三產業,國家也會對這些重污染的行業采取措施進行限制,減少其負效應。
從區域結構來看,我國的FDI區域分布非常不均衡。2006年,東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569.22億美元,比重為81.94%,而中西部分別只占了5.65%和3.13%。截至2008年底東部地區FDI比重下降到83.28%,而中部地區上升為10.64%,同時西部地區 FDI比重上升到6.06%。FDI區域分布的非均衡性,使得FDI對我國環境的負面效應也呈現出明顯的東高西低的特征。
(四)管制效應
管制效應是指東道國政府的“引資”行為產生的影響。當一國采取嚴厲的環境管制時,污染產業的比重降低,管制效應對環境產生正面的影響;若環境管制寬松,污染產業FDI的流入增加時,管制效應傾向于提高一國的污染水平。即符合“污染避難所”假說,該假說是指污染密集型產業的企業傾向于設立在環境標準相對較低的國家。
在環境管制和環境標準方面,FDI企業遵循我國現有的環境法規和標準要求,但是很多地方政府為了政績,盲目地對FDI企業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包括執行環境政策不嚴格,人為造成了對環境影響的負效應。另外,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各國會競相降低其環境標準,從而陷入國家間制定環境標準的“囚徒困境”。當然FDI企業的存在也對地方的環境標準的制定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使得其所在產業的生產水平大幅度提高,從而產生更嚴格的地方標準出臺。近些年來,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日益嚴重,我國政府已經開始采取一些措施,加大了環境管制力度,逐漸嚴厲的環境管制也阻止了部分污染嚴重的企業進入,對污染排放起到了某種程度的抑制作用。不過由于我國各地區采取的環境標準和管制有所差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工業污染的區際轉移。從長期來看,我國應繼續提高環境標準,這樣會有利于環境的質量改善。
四、對策和建議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技術溢出的正效應
在繼續擴大引進外資規模的同時,要不斷提高外資質量,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特別是環保友好型技術,在財政、稅收等方面給予鼓勵;扶持綠色產品和環保產業,盡快形成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平臺。鼓勵公司承擔環境責任,幫助其合資經營的伙伴等提高環境管理水平,充分發揮外資在提高技術溢出方面的正效應。
(二)制定可持續發展規劃,發揮規模的正效應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應建立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礎上。我國在使用外資與環境保護發生矛盾時,不應為追求經濟上短期、局部的“增長”而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同時,重視環境制度的改革、創新,以盡可能小的環境保護成本實現盡可能好的環境效果,促進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三)調整優化產業引資結構
進一步完善體制政策環境與產業準入政策。制定不同行業的新型工業化評價指標體系,強化招商引資的結構導向作用,采用傾斜的產業政策鼓勵外商去投資生態農業、林業、旅游業、服務業和基礎設施等傳統產業的同時,積極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改變“兩頭在外,污染在內”的產業結構。隨著入世承諾的完成,我國第三產業對外資的開放度大為提升,而進入第三產業的外資的清潔度也將更高,有利于我國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四)進行環境管制的創新
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FDI對我國生態環境的負面效應,除了運用法律手段建立懲罰機制之外,還要運用經濟和政策手段建立適當的環保激勵機制。比如對于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FDI項目的引進,地方政府應給予其一定的政策優惠;對于企業用于治理污染控制和治理的投資,實行稅收抵免等。這些基于業績的激勵措施能影響引資地區整體行為,引導引資活動的良性發展。
[1]于峰,齊建國.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環境效應的經驗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7(8).
[2]張彥博,郭亞軍.FDI的環境效應與我國引進外資的環境保護政策[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4).
[3]沙文兵,石濤.外商投資的環境效應分析——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6(6).
[4]巫雪芬,新華.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環境效應分析[J].改革與戰略,2005,187(3).
[5]李國柱.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污染的因果關系檢驗[J].國際貿易問題,2007(6).
[6]陳凌佳.FDI環境效應的新檢驗——基于中國112座重點城市的面板數據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08(9).
[7]張德強.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保護的沖突與融合——兼論我國如何平衡FDI與環境保護的關系[J].國家貿易問題,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