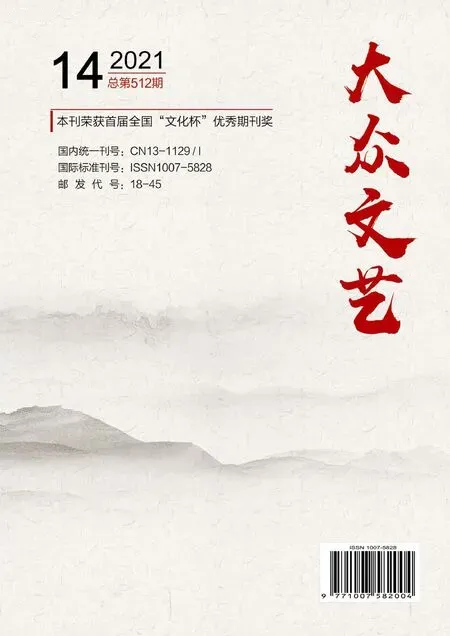假想的存在,文化的表征——對電影《超級戰警》所預設的系統的微議
蔡永強 (河南藝術職業學院 河南鄭州 450002 )
一、作為超現實的電影文化,科幻電影的節點
文化作為一個存在的狀態,時刻作用著人類的社會生活,文學小說作為對社會文化的想象性重現,給讀者營造了一個具體想象空間,讓讀者在思維之城中暢游各種文化現象和社會現實,電影作為一種真實地虛幻之物,將理想或幻想的社會展現在觀眾眼前,讓觀眾通過視覺和聽覺感知想象中的世界,這可以說是電影的獨特魅力所在。社會,作為本真的存在,我們無法超越,更無法改變,但電影卻可以肆意的改變現實的存在,制造未來,改編過去,而這也正是科幻電影的獨特之處。
在經典的電影理論中有兩種關于銀幕的隱喻:愛森斯坦、愛因海姆等形式主義者把銀幕當成影像成形的畫框;巴贊、克拉考爾等現實主義者把銀幕當成包括邊界以外的世界的窗口。而現代電影理論,因為拉康的鏡像理論,把電影看成一面可以從中看到人類自己的鏡子。拉康認為,人類的個體心理具有一種類似于鏡子的功能,而科幻電影呈現的是對現實社會的想象的仿像,也像一面鏡子,在不停的確認“他自己”,并與母體區別開來,然而,這一切在電影中的嘗試又都回歸到社會的元點——原本的存在機制。
作為對未來社會的一種預設和假想,電影人制造了未來的真實。科幻電影作為對現實真實空間的想象的仿像,戰警類電影中罪犯與警探之間的二元對立的結構,歷來是此類電影的敘事原動力。作為一種假設,未來我們無從知曉,但通過這些科幻電影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人類亙古不變的性格,人性的偽善和虛偽。美國導演馬考?布萊姆比拉1993年導演的《超級戰警》(英文名《Demolition Man》),可以說是對未來社會的一種的預設,將現實世界中警匪之間的二元對立結構作出了新的構建,對邪惡和正義之間的斗爭作出了置換性的嘗試,使這部電影與眾不同。
在電影作品開始的序幕部分,第一鏡頭是遠景景別,鏡頭運動方式是推鏡頭,畫面構圖的前景是一排正在燃燒的挺立的廣告牌之類的東西,遠處還有幾處有火光,同期聲是空中的螺旋槳聲音和地面警笛聲音,鏡頭運動的起幅位置是從離地面較高的空中進行的,電影字幕是:1996年——洛杉磯,進而展現神勇了警探突入匪巢抓罪犯的場面,而這一切都在預示著1996年或者當時洛杉磯這座城市時常都是處于這種局面之中,總是有壞人作亂,警察有逼不得已在維護社會治安的過程,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的隱患因素。因此,才有人設計了電子感化教育程序,在零度以下環境中,冰凍肌肉,以潛移默化方式感化人,訓誡人類。
隨著電影作品敘事的展開,轉眼洛杉磯城,已經進入2032年,這座城市已經是科技超級發達的,社會系統中一切都發生了轉換,城市界限趨于消亡,人們進入大同,然而這部著眼于表現警察的作品,在作品主體部分開始的時候,通過赫絲麗警探的口表達了對這種社會狀況的厭倦,警察的工作就是每天的循規蹈矩的問候監獄的典獄長,所謂的罪犯的狀況,而這些罪犯,都是在冰凍狀態之中。
如此有序的穩定的表面化的社會狀態,這一切的根基都是來自于卡陀博士的行為工程學的訓誡感化,表面化的仁慈,對罪犯的訓誡感化都利用電腦設計的感化程序,通過將設定好的機械電子程序數據,輸入到服刑的罪犯大腦中,這些感化教育程序各種各樣,比如在,這些感化教育程序是否真的能夠為人類提供一個未來發展的正確思路呢,電影也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說明這種思路是錯的。因為當社會進入一人獨裁之時,沒有什么力量能夠約束他的權利時,他只會被自己所設定的工具殺死,而殺死獨裁者的工具將構成對人類的危害。在電影結尾,人類社會又回到了矛盾重重,但這卻是真實的世界。
二、穩定的社會系統的預設,對現實的二元轉換
雖然電影作品沒有給我指明未來的發展,但是我們卻在這里看到人類社會文化機制的存在,在罪犯以費尼士(Simon Phoeix)為代表的邪惡罪犯與維護正義的警察之間的二元對抗,以及下水道地下黑暗社會中的所謂正常社會的異類危險分子與卡陀利用電子科技欺騙大眾營造的虛假和平社會之間的種種對抗,都對社會構成系統、文化構成系統及語言運用系統作提出了挑戰。
首先是社會構成系統二元轉換,社會系統是一個社會賴以存在的秩序,穩定的社會系統是大家渴求,但是在電影中存在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地上世界,由卡陀完全控制,這個世界看似很文明,彬彬有禮,秩序井然,但這個世界缺乏活力;另一個世界是艾加?佛南德里領導的生活在下水道里的地下世界,這個世界時一個無秩序的世界,所有人之間是平等的,領導本身也沒有想要成為領袖,只不過是為了尋求食物,在和地上世界對抗的過程中,成為一個領袖。地下世界和地上世界之間的聯系就是——食物,在電影中強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地上文明世界被獨裁了,獨裁者本人充斥著貪婪、欺騙、濫權,而這一切民眾卻一無所知。這構成了民主與獨裁的二元對立。只有當表面的和平和公正被揭穿它罪惡的面紗之后,真正的民主和公正才得以重建。
在電影中我們也感受到了一個詞——革命,被重新定義,一個看似文明世界被一個低劣的世界所推翻,被叫做“革命”。
社會構成系統的轉換,還表現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國家機器——警察身上,在影片中,警匪世界發生轉換,罪犯開著高級、電子時代的警車,而警察開著世紀古董——二十世紀的精品車,與罪犯展開了殊死搏斗,并最終致富了罪犯,維護了社會的和平、安定。
其次是文化構成系統的二元轉換,未來發達社會的文化系統,本應該是豐富多彩,但在電影中展現出來的未來社會的文化卻被毀滅了靈性,消失了很多,只殘存下來二十世紀的大眾文化中的垃圾——廣告歌曲,這在二十世紀卻是可以稱作垃圾的噪聲,但在這部電影中展現出來的卻是截然相反的景象,未來高度電子技術高度發達社會,青年人卻以聽曾經的廣告歌曲為樂,并把這作為對二十世紀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幻想途徑,來感味體驗以前人們的快樂生活。然而這在電影中也被敘說成為一種懷舊的時尚,成為大家廣為互相交通流傳的經典。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對大眾文化與高雅文化的另類解讀,經典是資源匱乏的時代產生的,懷舊是被說成是無知的人,盲目模仿的行為。而這種文化垃圾被保存下來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它不帶有任何具體的實踐性的思想意識形態的表達,所以作為獨裁者的卡陀才沒有禁止人們去領略它的回憶之力,但對于我們每個電影觀看的主體——觀眾,卻會引發閱讀思考的空間,對文化的本身的思考和文化的含義,以及文化的作用的思考。
第三是語言運用系統的轉換。海德格爾說:“所有存在著都棲居于語詞之中”,“語詞缺失處無物可以存在”。語言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語言本身并沒有太大的變化,歷時性的語言的發音和詞語的拼寫方法都是相同的,但共時性的言語本身的規則和限制增多,看似文明的進步,但實質是文明的倒退,語言系統的流失,導致了人對世界認識的錯位。在《超級戰警》里,計算機限制人們的言語規則,但卻使語言沒有生機活力。電腦機制語言與現實人類話語之間的轉換,電腦機制話語已經控制了社會一切,而電腦機制話語完全是由電腦程序控制,操作制作電腦程序的人就是獨裁者——卡陀,在電腦程序中沒有對罪大惡極的罪犯費尼士(Simon Phoeix)作出道德馴化,反而在他的訓誡程序中加入了很多謀殺程序和學習格斗程序,并且指引他去危害社會,從而讓人們更加害怕,更加愿意接受他所制定的穩定社會機制,然而這一切都被喜歡或者習慣說粗話的警察——約翰?斯巴達給打亂了,并且也導致了他所制定的語言運用規則的崩潰。
海德格爾認為,人不是語言的主人,語言也不是人的工具;人不識語言之外,而是在語言之中;不是人支配語言,而是語言支配人。對于無權制定話語運用規則的人,話語權顯然并不重要,因為其操持的話語本身已經失效。因此說“粗話”代表向歷史的回歸,也標識了人的回歸,話語系統的反向傳播,也說明了世界交換的錯位,語言革命帶來了社會革命,
三、結語
社會系統的穩定和發展,是來自構建社會體系的文化本身,文化形成的機制是社會符號化的表征,無論在科幻電影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只有通過對作為社會本身存在狀況的文化現象和社會機制的理解,來把握社會構成系統的變化。科幻電影是由當下的人們在現實的基礎上所作的改編和另造,如此預設的社會系統不具有任何實踐性和革命性,但是在作品內容呈現的意識形態的卻具有一定的實踐性,對現實的社會具有相當程度的反思。
[1]《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法].克里斯蒂安?麥茨著.王志敏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2]《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英].斯圖爾特?霍爾 徐亮.陸興華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一版.
[3]《分析傳統下的電影研究——敘事、虛構與認知》.黎萌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4]《現代電影美學基礎》 王志敏著.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