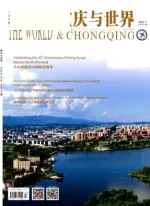論倒置的法律推理①
齊建英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哲學所,鄭州 450002)
一、倒置法律推理的實質在于主體對邏輯順序的刻意顛倒
法律推理的基本邏輯順序是從前提推出結論,前提和結論之間可以是“轉換”的、“跨越”的、“跳躍”的,但作為一種推理形式,它具有從理由得出結論的最本質的特征。要使法律裁決的證立可被接受,在形式向度上,裁決必須從證立所提出的理由中得出[1]。正是因為這種形式上的邏輯限制或要求,法律推理才能實現同案同判,成為保障司法獨立的有效屏障,成為司法判決可溝通性的基礎,成為限制自由裁量的手段,實現司法正義的途徑,成為“通向正義之路”。所謂倒置的法律推理就是先確定結論,然后,依據結論再對前提和理由進行篩選,從而表現為一種邏輯顛倒的法律推理。如在趙作海案中,先有幾個相關部門的協調會上決定的趙作海具備了故意殺人罪的起訴條件,能以故意殺人罪論處,然后,再由檢察院起訴到法院,由法院對前期的證據和線索進行選擇,將有罪線索定位為判決理由,而對無罪線索和證據則視而不見。這樣的法律推理不符合起碼的邏輯順序,是無效的,是掩蓋非正義的煙幕。
要想理清倒置的法律推理的涵義,還必須將之與法官對裁判預測、直覺和法感的依賴區別開來。裁判預測是在裁判中,法官了解案件事實之后,對案件處理結果形成了預測,然后尋找法律依據并最終做出裁判的過程。有倒置的特征。裁判預測客觀存在,有學者指出,裁判預測既不可怕,也不可恨,它能有效避免推理過程中的盲目和無緒。裁判預測到裁判結論的推理邏輯過程為:裁判預測——外部證成——內部證成——裁判結論。倒置的法律推理與預測到結論的推理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忽略了法律推理的外部證成與內部證成這個檢驗的過程[2]。法官的直覺來源于以往的審判經驗,它產生在查明案件事實之后,而且直覺本身只是獲得結果的一個審判指向,隨時準備修正。法律推理倒置過程中所產生的判決結果并不是來源于法官的審判經驗,而是基于其他的考慮基礎上作出的,是先入為主的裁判;法官為了達到該結果而進行法律手段的選擇,甚至是案件事實的調查,完全是一種主觀行為,已經違背了法律的正義[3]。拉倫茨認為:“僅以法感為基礎的判斷,只有對感覺者而言是顯然可靠的,對與之并無同感之人,則否。因此,法感并非法的認識根源,它至多只是使認識程序開始的因素,它促使我們去探究,起初‘憑感覺’發現的結論,其所以看來‘正當’的原因何在。”[4]從比較中可以看出,倒置的法律推理中,前期的結論并不是一個導向,而是最終的結論。它不是一種預測,不是一種感覺,不是認識的起源,而是認識的結論。倒置的法律推理不是客觀的認識現象,而是人為的處理結果。是人為選擇的一種處理案件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倒置的法律推理是利用先期已經確定下來的結論對案件事實及事實與法律之間的關系進行裁剪,而不是在充分掌握、全面考慮案件事實的基礎上的感覺或預測。因此說,倒置的法律推理的實質在于人,人對邏輯的主觀刻意顛倒。這樣的倒置的法律推理,將非正義的力量掩蓋起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它比缺省的法律推理對我們的法治建設具有更大的破壞力和傷害性。因為,缺省的法律推理,它直接就沒有說服力,可以被人們直接對此進行攻擊和批評。而倒置的法律推理在判決書中則被顛倒過來,看似從理由推出結論,是一個完美的具有說服力的判決和結論,殊不知這個結論是在推理前已經定好的,這個理由是根據結論而裁剪的。
從理由推出結論,或者說先有預感或預測,然后通過對預感或預測的檢驗和驗證而得出結論是正常的邏輯順序,那么,為什么會有推理主體對這一基本的邏輯順序進行違背和顛倒呢?
二、語境是法律推理倒置的根源
法律推理是在具體語境中進行的,同樣的前提結合不同的語境就能推出不同的結論。從外在的視角看,語境是非常寬泛而難以捉摸的,它無所不包,無處不在;但從內在視角看,語境是主體建構出來的,每一個推理主體所建構的語境都是具體的,特定的。法律推理是結合語境,在推理主體之間不斷溝通和對話的基礎上動態進行的。對話的過程,也就是說者向聽者明示自己的觀念,聽者理解說者觀念的過程。在對話中,聽者和說者之間的身份不斷地發生轉化。針對聽者而言,語境起到解釋作用。在法律推理中,它可以通過補足被省略的信息,來解釋語言中人為或自然的模糊現象,消除歧義,推斷出說者的弦外之音,進而理解說者所表達信息的確切含義。針對說者和聽者而言,語境都起到制約作用。“語境制約著整個談話過程,對于表達和理解兩個方面都是不可忽視的參數。”[5]語境制約著說者的表達方式、語言形式的選擇,制約著表達的省略程度;制約著聽者對表達的理解;制約著雙方的互動方式。語境建構的過程也是推理主體之間進行對話溝通的過程,即針對各自所建構的語境進行討論,最后得出各方交叉或重疊的語境,即共識性語境,然后再結合該共識性的語境進行合乎邏輯的推理。這時的推理才是恰當的,有效的。然而,從另一個方面講,語境又是法律推理有效性的取消機制。法律推理的有效性包括邏輯有效性、內容的共識性、程序的對話性和恰當性等,其中,恰當性是關鍵所在。恰當性,即與語境的協調性和契合性。當語境發生變化,法律推理與語境的協調性和契合性喪失;原來的共識性語境遭到破壞,共識性失去了現實依托;推理主體之間還需要針對新語境進行新一輪的溝通和協調。在特定的語境下,也許推理主體就失去了語境建構的參與權,漠視推理語境的共識性,推理的基本邏輯形式也可能遭到破壞,甚至顛覆。
依據正常的法律推理,與案件直接相關的利害關系人,是法律推理的最重要的主體。在趙作海案中,公安機關以趙作海與“被害者”一直有過節;趙作海在村里的口碑不好;趙作海曾在“被害者”失蹤前一天與之發生過流血沖突;有人認出現場趙作海家的尼龍袋;趙作海在審訊中做了“有罪供述”等為由,報送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院經審查核實,發現尸源問題沒得到最終確認;壓在尸體上的三個五六百斤的石磙,不可能是趙作海一人所為;難以排除逼供、誘供的行為;肢解尸體的刀具沒有找到,因此做出了因證據不足而退卷的決定。兩次退卷之后,公安系統要么撤案放人,要么變更強制措施[6]。在此過程中,雖然趙作海作為案件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并沒能作為法律推理的主體出場,甚至難以排出被逼供、誘供的可能,但檢察院的立場和觀點在客觀上代表了他的立場,整個推理還基本恰當。但在后來,推理的語境發生變化。公安機關并沒有變更對趙作海的強制措施,而是一直在超期羈押。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強勁的整頓超期羈押的運動,政法委針對趙作海的超期羈押第二次召開協調會,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政法委都作為法律推理的主體出場,他們就自己所建構的語境進行溝通,最后,積極響應國家針對超期羈押的政策,不錯放疑犯成為壓倒性語境。在此語境下,趙作海案具備起訴條件,定性為故意殺人犯的推理結論很快形成。要想實現這樣的結論,必須將從前提到結論的推理形式進行倒置。于是,法官們根據這一結論向前回溯,對原有的案件事實和線索進行篩選和剪輯,演繹了一場從結論到理由的倒置的無效的法律推理。
三、重構推理語境,矯正倒置的法律推理
趙作海案等一些因倒置的法律推理所釀成的冤假錯案不僅殘酷地傷害了當事人及其家屬的身心,而且嚴重地破壞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信度,成為國家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敗筆,應該盡早予以矯正。
矯正法律推理倒置要從重構語境入手。語境不是靜態的,固定的,而是動態的。Mey認為:“語境是動態的,它不是靜態的概念,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它是言語交際時不斷變動著的環境。交際者在這樣的環境里進行言語交際,并且從這樣的環境中獲得對交際言語的理解。”[7]言語交際中的語境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靜態的既定集合體,而是一個隨交際的需要不斷被創造的變動體,是一個隨交際的展開不斷發展的動態系統。“語境是一個心理建構體,是聽者關于世界假設的子集。正是這些假設,而非實際的客觀世界,制約了話語的解釋。”[8]15交際中的語境“不再是一個被適應的對象,它時時處在交際主體的不斷選取中,它完全可以被創造。在交際過程中,人們并非一味適應語境,更多的時候是打破固有語境的束縛,創造語境,創造有利于交際效果的語境”[9]。在法律推理中,推理主體不僅是被動地接受語境的制約和限制,更重要的是可以主動地選擇和建構語境。在語境的創造和建構中,應該注意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語境建構主體的多樣性。推理主體是語境的選擇者和建構者,在語境的創設中起著關鍵作用。法律推理的主體是復數的,包括法官、雙方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法學家、社會大眾等。在具體的案件審理中,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推理主體是法官、雙方當事人及其辯護人,其他的推理主體只能是在法庭外發表自己的評論和意見。只有最核心的推理主體建構出來的語境,才是直接影響審理結果的推理語境。在趙作海案中不難發現,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沒有成為推理主體,沒有參與到語境的建構中來,而是被動地作為語境和推理結論的接受者出現。相反,其他一些不該直接干預案件處理的單位則介入到推理中來,直接地影響甚至決定了推理語境的形成。
其次,語境建構過程的互動性。語境作為推理主體的心理建構體,由于各自所處的立場、掌握的經驗和建構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在各個推理主體之間存在差異。“我們并不能建構同樣的心理表征,因為一方面我們狹義上的物理環境不同,另一方面,我們的認知能力不同……人們說不同的語言,掌握了不同的概念,結果,人們能夠建構不同的心理表征并做出不同的推理。他們也有不同的記憶,不同的推測以不同的方式與他們的經驗相關。因此即使他們都共享同樣的狹義上的物理環境,但我們所稱之的‘認知環境’仍然是不同的。”[8]38然而,任何單一主體所建構的語境都需要接受其他主體的檢驗和審視。語境建構的過程就是各個主體把自己建構的語境表達出來,與別人討論,并在討論中不斷地修正和完善語境的過程。
最后,語境建構結果的共識性。多個推理主體就各自建構的語境進行討論甚至辯論的最終目的是追求共識,達成理解。達成共識的語境才是最恰當的語境。只有結合具有共識性的語境進行的法律推理才具有恰當性和合理可接受性。
[1]菲特麗絲.法律論證原理:司法裁決之證立理論概覽[M].張其山,焦寶乾,夏貞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3.
[2]王慶豐,張尚謙.從裁判預測到裁判結論:“先見”、正確裁判及其過程[M]//呂伯濤.司法能力建設的新視角:司法能力建設與司法體制改革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462.
[3]郭衛華.“找法”與“造法”:法官適用法律的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7.
[4]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5.
[5]周禮全.邏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14.
[6]劉剛.還原趙作海冤案形成過程:鄉村道德審判成推手[EB/OL].(2010 -08 -01).http://henan.sina.com.cn/news/2010 -06 -03/184225788.html.
[7]Mey J L.Pragmatics:An Introduc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Second edition,2001:40.
[8]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Second edition,2001.
[9]胡霞.認知語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