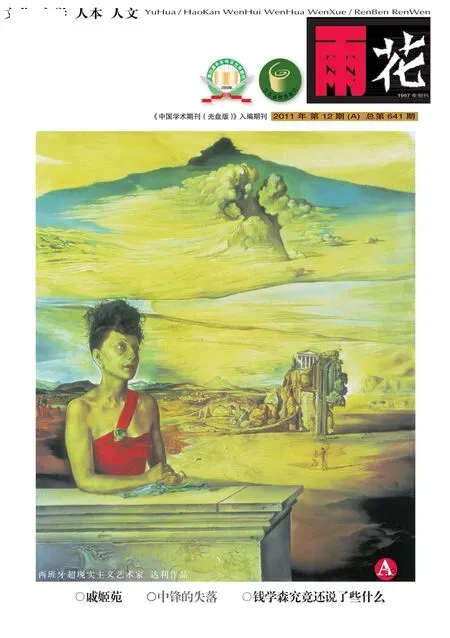番芋粥
● 林 宕
倒毛起先不清楚阿戇家發(fā)生了什么事,待看到滾落在墻邊的那只“樂(lè)果”瓶,就驚叫了一聲,然后撲向已經(jīng)四仰八叉躺在地上的阿戇身邊。
菊花說(shuō):“不要緊,家里的農(nóng)藥我都倒光了,瓶里裝的是水。”

阿戇送給了癩痢八只桃子,癩痢非但不領(lǐng)情,還說(shuō),你這個(gè)戇大,你這個(gè)戇大啊!說(shuō)著,癩痢還用右手掌在阿戇的頭頂上不輕不重地拍了一下,他后面的話也就讓自己的右手掌表達(dá)了。很難得的,阿戇對(duì)這種表達(dá)方式表示了憤怒,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癩痢的光頭,喘息粗重。誰(shuí)都知道,阿戇的憤怒是不可能有任何攻擊性的,誰(shuí)也不會(huì)認(rèn)為阿戇的憤怒是憤怒。
癩痢又嘀咕了一聲,戇大啊。然后,癩痢拎著桃子,臉上浮著心滿(mǎn)意足的神情,走了。
阿戇低下頭來(lái),眼睛定定地看著腳下黑色的泥花。地上的泥花是蚯蚓在地下挖土?xí)r從口中吐出來(lái)的。泥花由一根根鉛筆芯那么粗的泥條彎曲盤(pán)積而成,東一朵西一朵。阿戇的腳邊大概有十幾朵,有的小如核桃,有的大如饅頭。阿戇開(kāi)始用腳踩泥花,那些造型美麗的黑色泥花在阿戇右腳的踩搓下很快消失了,阿戇粗重的喘息也慢慢平復(fù)了。有誰(shuí)知道呢,原來(lái)阿戇的憤怒是有這么一個(gè)出處的,他的憤怒原來(lái)也是有攻擊性的,只不過(guò)針對(duì)的不是人。
毛竹棚里的光線有些暗,可阿戇還是看到自己身體左側(cè)的棚壁邊長(zhǎng)著好多碧綠生青的小草,有圓頭圓腦的槳板頭草,有羞羞答答的狗尾巴草。阿戇不會(huì)像踩泥花一樣去踩這些小草的,他是把這些最近突然出現(xiàn)在毛竹棚里的小東西看作自己的客人的。來(lái)他的毛竹棚里做客的還有二鳴子、三鳴子、織布娘、小飛蛾等小昆蟲(chóng),現(xiàn)在就有一只二鳴子在一棵狗尾巴草邊鳴叫呢。鰥夫阿耿踏著二鳴子的叫聲跨進(jìn)了毛竹棚。
“阿六頭呢?”
阿六頭是與阿戇搭伴賣(mài)桃子的,是隊(duì)長(zhǎng)健龍的弟弟。今天中午過(guò)后,突然拉肚子了,一次一次地往毛竹棚后跑。后來(lái),阿六頭就對(duì)阿戇說(shuō),我早點(diǎn)回家,這些桃子你總守得牢的吧?阿六頭和好多橫涇村人一樣,在跟阿戇講話時(shí)常常是話里有話的。
哦,阿六頭拉肚子回家了。阿耿嘀咕著在阿戇面前的桃堆前蹲下來(lái)。阿戇面前只有兩小堆桃子了。阿六頭走的時(shí)候共有六小堆桃子。阿戇對(duì)來(lái)這里的人說(shuō),今天的桃子不用付鈔票了,送。對(duì)方先是用狐疑的眼神看著他,然后笑了,說(shuō),阿戇真大方,什么都送人。阿戇不理會(huì)對(duì)方話中的話,又說(shuō),只是、只是四點(diǎn)鐘的辰光你再來(lái)一次,這里。對(duì)方的眼睛里就又有了狐疑的神色。阿戇說(shuō),反正你來(lái)。對(duì)方受了好處,當(dāng)然連連點(diǎn)頭,點(diǎn)頭的同時(shí),再次開(kāi)口,又要送我們什么了?
阿耿上次在這里裝了半籃桃子后,沒(méi)有付鈔票,阿六頭想奪回他的籃頭,他就擰住了阿六頭的胳膊,說(shuō),誰(shuí)規(guī)定要當(dāng)場(chǎng)付鈔票的?阿六頭咽口氣,讓果園的會(huì)記把這半籃桃子的鈔票記在了他自己的經(jīng)濟(jì)往來(lái)賬上。今天,阿耿又帶來(lái)了一只竹籃頭,他裝了半籃子的桃子后,出乎意料地要過(guò)秤。
“送你,耿叔。”
阿耿瞪圓了眼睛,“你以為我是貪圖小便宜的人?你以為我是欺軟怕硬的人?”
“阿六頭不在,只有你阿戇在,我反倒要當(dāng)場(chǎng)付鈔票。”阿耿堅(jiān)持要過(guò)秤。阿戇想去阻擋阿耿,阿耿像上次擰阿六頭一樣,擰住了阿戇的胳膊。
結(jié)果,當(dāng)天從生產(chǎn)隊(duì)桃園里摘來(lái)的桃子中,就只有阿耿的這一籃付了鈔票,其余的都被阿戇送光了。
阿戇送光桃子后,就走出了毛竹棚,站在村道上。西斜的陽(yáng)光照在阿戇的身上,讓他有點(diǎn)暈眩。村道北側(cè)又傳來(lái)了秋英、春芳兩妯娌的爭(zhēng)吵聲。
秋英說(shuō):“你做的事情以為別人不曉得?”
春芳說(shuō):“你自己的屁股還沒(méi)擦清爽,就急五急六地去管別人的事了?”
“誰(shuí)想管你的事!好事不出門(mén),丑事傳千里,你的事是自己跑出門(mén)的。”
她們兩人的爭(zhēng)吵其實(shí)已經(jīng)開(kāi)始了一個(gè)多鐘頭。在毛竹棚里時(shí),阿戇還聽(tīng)不大清爽爭(zhēng)吵的內(nèi)容,現(xiàn)在聽(tīng)清爽了,卻仍舊只聞其聲不見(jiàn)其人。發(fā)出爭(zhēng)吵聲的兩個(gè)女人都待在屋子里,她們是對(duì)著窗戶(hù)在相互較勁。她們肯定是邊做著手里的生活邊爭(zhēng)吵的,手中的生活是她們的爭(zhēng)吵得以不斷持續(xù)下去的一個(gè)重要原因。
阿戇看到一只癩團(tuán)在地上蹦跶,蹦跶幾下后,慢慢地爬進(jìn)了路旁的一蓬枸杞叢里。鄰村的一位背籃頭的老太在向阿戇走來(lái)。這里的人都把背著一只竹籃、走村串戶(hù)販賣(mài)粗鹽、肥皂等家用品的人叫做背籃頭的。背籃頭的經(jīng)過(guò)阿戇身邊時(shí),腳步一點(diǎn)也沒(méi)有放慢,甚至看也沒(méi)有看阿戇一眼。背籃頭的肯定是認(rèn)識(shí)阿戇的,肯定知道在橫涇村里阿戇是一個(gè)啥也沒(méi)有用的影子,是他自己身體的影子。這個(gè)影子突然抖索了一下。
“菊花還要比你好呢,菊花只跟隊(duì)長(zhǎng)健龍一個(gè)人睡。你呢?”
菊花就是阿戇的老婆。
“我比你好。你給你男人生了個(gè)別人的孩子。”
“是你男人的孩子,你沒(méi)有看出來(lái)?”
“是誰(shuí)的孩子你最清爽。只有你家男人這個(gè)窩囊廢不清爽。”
“你家男人才是窩囊廢,阿戇一樣的窩囊廢。”
秋英和春芳的爭(zhēng)吵好像達(dá)到了一個(gè)高潮,她們的聲音清晰而響亮,可她們的人影還是被兩垛灰墻擋在了里面。一垛灰墻的下面,一只花貓瞇縫著眼睛在打盹,貓的體態(tài)是懶散的,表情是平靜的,對(duì)于妯娌倆的爭(zhēng)吵,這只花貓也早已經(jīng)習(xí)慣了,早已見(jiàn)怪不怪了。
眉毛長(zhǎng)反了的倒毛在空蕩蕩的毛竹棚里轉(zhuǎn)了一圈后,就在毛竹棚西側(cè)那棵高高的苦楝樹(shù)上看到了阿戇。他起先還以為蹲在苦楝樹(shù)兩根枝杈間的是一只大鳥(niǎo),嚇得原地跳動(dòng)了一下,手中捏著的幾張毛票差點(diǎn)兒落地上。阿戇送他桃子時(shí)要他四點(diǎn)鐘再來(lái)一次這里,阿戇這個(gè)嘟噥似的要求起先讓他摸不著頭腦,后來(lái)看著半籃子白白拿來(lái)的桃子,他想,四點(diǎn)鐘差不多正是隊(duì)長(zhǎng)健龍、婦女隊(duì)長(zhǎng)菊花等隊(duì)部的人回家路過(guò)毛竹棚的時(shí)間,說(shuō)不定健龍這一次又要親自進(jìn)毛竹棚去收賣(mài)桃的鈔票,所以,阿戇這是在做兩手準(zhǔn)備,如果真出現(xiàn)了這種情況,倒毛就要補(bǔ)交上買(mǎi)桃子的鈔票。都說(shuō)健龍是看在菊花的面上讓阿戇賣(mài)桃子的,可如果阿戇真的不賣(mài)只送,估計(jì)健龍也不會(huì)饒過(guò)他。倒毛這么想著,就在阿戇講的那個(gè)辰光重新來(lái)到了毛竹棚邊。
尾隨在倒毛身后來(lái)到苦楝樹(shù)邊的一根也看到了阿戇。
一根說(shuō):“大家來(lái)看啊,阿戇要做猢猻啦。”
一根的話音剛落,阿戇真的學(xué)起來(lái)了猢猻,他的兩條腿掛在了枝杈上,身體倒掛了下來(lái)。
其實(shí),當(dāng)天聽(tīng)了阿戇的話再次來(lái)到毛竹棚邊的就倒毛和一根兩人。一根的到來(lái)是不是出于倒毛相同的目的不知道,可他看到阿戇蹲在高高的苦楝樹(shù)上后,顯然興奮了起來(lái),意外遭遇了一場(chǎng)免費(fèi)的好戲讓他情緒高漲,他簡(jiǎn)直在原地跳起了三尺高,揚(yáng)起脖子朝阿戇喊:“你年紀(jì)一把了,還學(xué)猢猻做啥?”
一根的聲音終于把兩個(gè)女人的爭(zhēng)吵聲壓了下去,這兩個(gè)女人竟然也來(lái)到了苦楝樹(shù)附近。
阿戇開(kāi)始微微晃動(dòng)起倒掛著的身體來(lái)。春芳在樹(shù)下驚呼了一聲。
一根又嚷:“不要怕,阿戇是猢猻投世的,沒(méi)有危險(xiǎn)的。”
春芳說(shuō):“誰(shuí)不是猢猻投世的?”
阿戇很快收縮了一下身子,重新恢復(fù)了原樣,蹲坐在了兩根枝椏間。雖然他只讓自己的身體倒掛了短短的一會(huì)兒,可還是有不少人被吸引了過(guò)來(lái)。癩痢也來(lái)了,癩痢問(wèn):
“這個(gè)戇大在做啥?”
倒毛說(shuō):“在捉天牛。”
喜歡鉆樹(shù)干的天牛是所有樹(shù)木的天敵,所以每到春夏兩季,橫涇村上有時(shí)會(huì)有個(gè)別爬樹(shù)高手爬到樹(shù)上去,捉天牛。
春芳捅了一下一根的腰眼,“不要出事了啊,你們就不要再說(shuō)啥了,快叫阿戇下來(lái)。”
倒毛在樹(shù)下仰起了臉。這棵苦楝樹(shù)差不多是橫涇村最高的一棵樹(shù)了,有二十來(lái)米高。阿戇蹲著的兩根枝椏在樹(shù)干的當(dāng)中,即使這樣,阿戇也被人感覺(jué)到已經(jīng)是一只遠(yuǎn)離地面的猢猻了,一根講得沒(méi)錯(cuò)。苦楝樹(shù)的樹(shù)冠一半在橫涇河的上方,另一半在碎石路的上方。現(xiàn)在,阿戇就蹲在了碎石路的上方,他的下面,就站著一根一個(gè)人,其余的人都圍成一堆,站在碎石路一邊的一塊泥地上。
春芳說(shuō):“阿戇,你下來(lái)。你忘了前年二傻在這棵樹(shù)上摔下來(lái)的事了?”
她突然感到后面的那句話是不吉利的,眼神多少有些惶恐地看了一下自己旁邊的人。前年春天,二傻就是從這棵樹(shù)上摔下來(lái)的,頭著地,死了。
阿戇在樹(shù)上說(shuō):“我就是要跟二傻一樣。”
他說(shuō)著轉(zhuǎn)了轉(zhuǎn)腦袋,往樹(shù)下的某一個(gè)地方看了看,再次迅速地把自己的身體倒掛了下來(lái)。也就是在這時(shí)候,隊(duì)長(zhǎng)健龍和婦女隊(duì)長(zhǎng)菊花一前一后地走近了過(guò)來(lái)。
健龍的眼睛瞬間轉(zhuǎn)了一圈,亮起來(lái)。
“一根,不要站樹(shù)下,當(dāng)心砸死你,快走開(kāi)。”健龍說(shuō)。
菊花尖叫了一聲,把眾人往樹(shù)下推,“快,快。”
大家都懂了菊花的意思,在菊花的連推帶拽下,幾乎所有的人在一瞬間里集中到了樹(shù)下。健龍的眼神已經(jīng)暗下來(lái),也慢吞吞地走到樹(shù)下。
“你松腿吧,你這個(gè)戇大。”癩痢仰著頭朝上嚷。
眾人的腳步稍稍散開(kāi)來(lái),都伸展開(kāi)手臂,不同人的手指相互交錯(cuò)住,于是樹(shù)下就有了一張由手臂相連而成的網(wǎng)。
“你就松腿吧,你這個(gè)戇大。”癩痢又往上嚷。
阿戇卻在樹(shù)上再次收縮了一下身體,重新蹲坐在了枝椏間。
樹(shù)下的網(wǎng)松了一下,很快又緊了。接著再次在松、緊之間轉(zhuǎn)換了一下,在轉(zhuǎn)換的過(guò)程中,眾人幾乎腳步一致地往北移動(dòng)了幾步。
“操那,你倒是快點(diǎn)往下跳呀。”癩痢惱怒了。
阿戇爬到了橫斜在橫涇河上面的一根枝杈上,他做出了要往河里跳的姿態(tài),卻又往回爬了。然后,他的身體慢慢地順著樹(shù)干滑下來(lái)。
樹(shù)下的網(wǎng)算是白搭了,眾人罵罵咧咧地散開(kāi)來(lái)。
“我要讓你們白忙乎。”到了地上后,阿戇說(shuō)。他的臉上有著一些勝利者的神色。
阿戇把頭埋在番芋粥碗里,剛吸溜了一口湯水,菊花就開(kāi)口了:
“胃口那么好,是想自殺的樣子嗎?”
阿戇重新抬起了腦袋,一雙蒙上了湯水汽的眼睛有些茫然地看著菊花。粥碗里的熱湯水仍舊在往上冒著熱汽,帶著番芋的清香。隔年的番芋有幾個(gè)已經(jīng)霉?fàn)€了,菊花就慌忙地把沒(méi)有霉?fàn)€的番芋從柴屋里搬出,在太陽(yáng)光里曬了一天,然后把番芋切成小塊,和粥熬在一起吃。
菊花又說(shuō):“你倒有種了,把大家玩弄了一下。”
阿戇把碗放到了桌上,說(shuō):“你以為我不敢自殺?”
菊花愣了一下,想說(shuō)啥,卻又沒(méi)有說(shuō)出口,只是咽了一口唾沫。
菊花臉上一時(shí)浮現(xiàn)的愣怔表情像是鼓勵(lì)了阿戇,阿戇又開(kāi)口:
“你們都以為我不敢自殺?”
這下,菊花臉上終于再次浮上了狠氣,說(shuō):
“有種你昨天不應(yīng)該等別人到樹(shù)下,沒(méi)人的時(shí)候你就應(yīng)該跳下來(lái)。”
阿戇轉(zhuǎn)了一下頭頸,眼神又變得有些茫然了。可很快,他渙散的眼神又重新聚攏了,他說(shuō):
“你們都以為我不敢自殺?”
阿戇說(shuō)著往屋門(mén)外走,走進(jìn)了柴屋。很快,他手里拎著半瓶“樂(lè)果”走回了屋內(nèi)。他邊看著菊花邊擰農(nóng)藥瓶的蓋子。
“我倒到碗里。”
“樂(lè)果”瓶已經(jīng)半斜了起來(lái),瓶口也已經(jīng)對(duì)準(zhǔn)了番芋粥碗。
“我倒到碗里后,再喝掉。”
阿戇看著菊花,手有些抖。
到了這個(gè)地步,菊花臉上反而啥表情也沒(méi)有了,她也不接阿戇的話。
農(nóng)藥瓶的瓶口里終于流出了液體,緩緩地流進(jìn)了番芋粥碗里。
阿戇端起了番芋粥碗,哭一樣地說(shuō):“我喝了啊。”
菊花把臉轉(zhuǎn)到了別處。
“我要喝了啊。”
阿戇把碗放下,突然坐到了地上,嗚嗚嗚地哭起來(lái)。哭聲把隔壁的倒毛引了過(guò)來(lái),在倒毛跨進(jìn)木門(mén)檻的時(shí)候,阿戇舉起手臂,右手摸摸索索地探向桌上的番芋粥碗,他的身體呈現(xiàn)出一種掙扎的姿勢(shì)。
阿戇終于掙扎著站了起來(lái),用絕望的眼神看一眼他面前的兩個(gè)人,然后猛地仰起了脖子。
倒毛起先不清楚阿戇家發(fā)生了什么事,待看到滾落在墻邊的那只“樂(lè)果”瓶,就驚叫了一聲,然后撲向已經(jīng)四仰八叉躺在地上的阿戇身邊。
菊花說(shuō):“不要緊,家里的農(nóng)藥我都倒光了,瓶里裝的是水。”
健龍插上柏木門(mén)的插銷(xiāo),然后走向菊花。他的步子不慌不忙的,可是臉色看上去有幾分凝重。他把手搭在菊花的肩上。
菊花正坐在一條木凳上,她甩掉健龍的手,站了起來(lái)。由于關(guān)緊了門(mén)窗,屋里很暗,這份暗色也使菊花的臉色平添上了幾分凝重。
健龍和菊花現(xiàn)在待著的屋子是生產(chǎn)隊(duì)隊(duì)部旁邊的一間倉(cāng)庫(kù),作為婦女隊(duì)長(zhǎng),菊花平時(shí)的工作卻是在這間倉(cāng)庫(kù)里發(fā)放農(nóng)具、種籽什么的。屋內(nèi)散發(fā)著一股由谷物與泥土混合而成的悶熱氣味。現(xiàn)在是上午,整個(gè)生產(chǎn)隊(duì)隊(duì)部一片沉寂,倉(cāng)庫(kù)里更是只剩下了健龍和菊花的呼吸聲。
健龍突然抱住了菊花。
“所有橫涇人都以為你是我的人了,只有鬼才知道原來(lái)是怎么回事。”
菊花扭動(dòng)自己的身子,很快把自己的身體從健龍的手臂間掙扎了出來(lái)。
健龍喘著粗氣,說(shuō):“放別人,我早對(duì)你不客氣了。”
菊花說(shuō):“放別人,我會(huì)讓你非禮那么多次?”
菊花去開(kāi)門(mén),健龍站著不動(dòng),雙手垂著,臉上顯出了頹喪的神色。
一縷陽(yáng)光從門(mén)檻上方照進(jìn)屋內(nèi),陽(yáng)光里粉塵翻飛。菊花從門(mén)邊走回到了木凳那里。
“坐一會(huì)吧。”
健龍站著不動(dòng)。
倉(cāng)庫(kù)里已經(jīng)變亮堂,那股由谷物與泥土混合而成的悶熱氣味也似乎淡去了不少。
“菊花,”健龍轉(zhuǎn)了轉(zhuǎn)頭頸,“那么多次,我以為你總會(huì)依我一次的。”
菊花已經(jīng)在木凳上坐下,“我,我也想過(guò)要依你一次的。”
“可現(xiàn)在我不這樣想了,”菊花又說(shuō),“從今天開(kāi)始,你就不要再動(dòng)我腦筋了。”
健龍瞪大了眼睛,“可橫涇人都以為你是我的人了,你這不是讓我冤大了嗎?”
菊花不接他的話頭,自顧自往下說(shuō):“阿戇今天早上為我尋死了,你會(huì)為我尋死嗎?”
“阿戇真死了?”健龍?jiān)靥似饋?l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