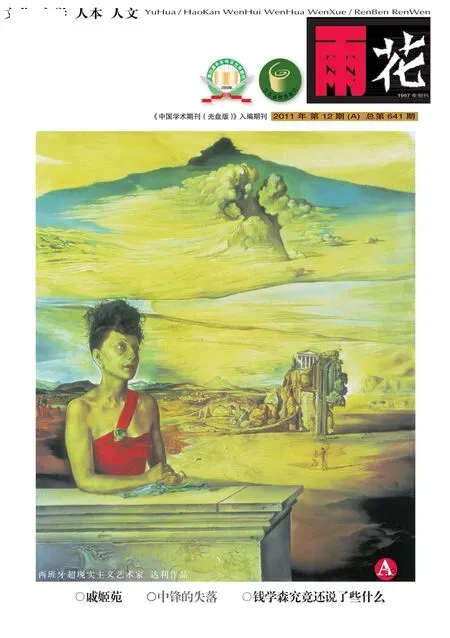愚人說夢
● 朱子南
我們過去常說美國這資本主義大國一切以金錢來衡量,是充滿了銅臭味的,但是,從這則消息中,我們不也可以看到美國社會中的人性化傾向?

招商引資
環(huán)保局的職責是什么?顧名思義,是環(huán)境保護,監(jiān)督監(jiān)測以防止環(huán)境污染吧!但什么時候這些職能部門的工作異化了呢?如安徽省懷寧縣,據(jù)2011年1月12日《報刊文摘》消息,應該是負責環(huán)境保護的部門,卻“招商引資”引進了一家重度污染環(huán)境的企業(yè),致使縣里的高河鎮(zhèn)已被查出有一百多名兒童血鉛超標。
中央已連續(xù)有多少年了,每年的1號文件都是談的三農問題,而懷寧縣每年年初也有一個1號文件,談的是對縣里招商引資任務的分解,即對每個縣直單位以及各個鄉(xiāng)鎮(zhèn)分配招商指標。
這消息并不陌生,好多地方都有。于是這些鄉(xiāng)鎮(zhèn)、單位就不顧應該負責的民生問題而是大力招商了,其景象是,全縣似是變成了一個大招商局。
我倒是在想:這始作俑者,是在哪里?又緣何謬種流傳,把“經驗”傳播到了全國的好多地方?
脫口而出
“我爸是李剛”,這句話或可以成為2010年的流行語之一了。
就這一句話,經人肉搜索,牽出了李剛原來有五套房產,兩處在自己名下,三處在兒子名下,其中還有別墅。一個地級市公安分局副局長,充其量是個科級干部,何以有這么多錢購置這些豪宅?
我的想法卻還在——
“我爸是李剛”這句話是李剛的兒子脫口而出的,可見,用“李剛”的“盛名”來嚇唬人或謀取利益已成為習慣了。
因之,我倒是建議,查一下“我爸是李剛”在李剛兒子的口中吐出過多少次,又有多少次是確實起到了作用,得以“我爸是李剛”而獲得了不當利益的?
“上牌”政策
見2010年11月17日《文匯報》報道,寧波將實行“無車位不上牌”的政策,這同我的想法甚是合拍。
但是,在《文匯報》的這一報道中,也介紹了對這一政策的不同意見,如,有人戲談,計生委可以考慮出臺“生孩子必須先落實好一套房”的政策,等等。不過,這能相提并論么?
有“理論含量”的,則說,百姓要買車、開車,是正當?shù)男枨螅粦芏糁疲欢峁┸囄唬斎皇钦呢熑巍R灿小霸u談”說,這是限制了人民的消費權。總之,是極力反對了,唯恐寧波的這一政策蔓延到其他城市。
又見報道,說我所居住的這個城市汽車擁有量已達120萬輛。這是位居全國第三了,僅次于北京、上海。然而,這個城市比起武漢、廣州、杭州、南京、天津、重慶等等城市,就面積來說,是要小得多的,何況后者還包括兩個直轄市呢!這停車問題又該如何解決?現(xiàn)在是,在馬路上,劃了停車位,有的也承包出去收費,倒也可以解決一些就業(yè)率,但當大街小巷都停滿了的時候,每天凈增幾百輛車子又該停到哪里去?
說消費權不應限制,購車、開車是正當?shù)男枨螅鴮ψ呗返娜藖碚f,這“行路權”又該如何維持?現(xiàn)在,連能夠停車的人行道上也是橫七豎八停滿了車子的,還包括了盲道。
壓縮公車
2010年12月5日《揚子晚報》報道:中國公務車每年支出近2000億元,每年公務用車購置費支出增長率為20%以上。報道中還提到,“現(xiàn)在許多地方科級干部都早已配有專車,更別說一個處長”了。
我至今記得,1981年春,《光明日報》記者理由來蘇州采訪,向我提出能否有車,擬去東山走一圈,以作為寫作的背景材料。我想到了時任吳縣縣委辦公室主任的老范,向他求助。他派來了一輛吉普,我們得以成行。事后知道,老范為派這一輛車,還向縣委書記請示了,當時,縣委連同這輛吉普在內一共才3輛小車。
1985年,我去市委,見到市委副書記老林正要出門,那車,是市委辦公室統(tǒng)一安排的,他并無專車。
又見中央電視臺一位軍事專家訪美歸來談美軍的用車,說是中將級別的才能有專車,且所有的公務用車均無空調。他說,我們這里干部的專車配到了哪一級?那是相當“普及”了。
地方上呢?請統(tǒng)計一下,這里的一個鎮(zhèn)政府有多少車?更別說縣級機關了。
不過,公車改革的消息已經傳了有16年之久了,說要收回公車,而以每月補貼的形式解決;但實際是補貼照拿,公車照用。一個科級干部,憑空又多得了二、三千元。
公車究竟怎么改革,有消息說現(xiàn)在要規(guī)定正部級才能安排專車,如此,作為一個地級市,就無一人能享用專車待遇。這能行得通嗎?
所以,《揚子晚報》報道說,公車使用人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天然反對公車改革。如果不從體制上加以改革,那么公車改革是無從落實的。
生存第一
一個以賣卷餅為生的小販因心肌梗塞猝死。他不富不貴,無職無權,去世后,卻有許多人自發(fā)地哀悼與紀念,《華盛頓郵報》甚至在頭版發(fā)了他的訃告與故事。這件事發(fā)生在美國。2010年10月22日的《報刊文摘》轉摘了這一消息。
我們過去常說美國這資本主義大國一切以金錢來衡量,是充滿了銅臭味的,但是,從這則消息中,我們不也可以看到美國社會中的人性化傾向?如《報刊文摘》中提到的,他們“尊重人,也被人尊重”。
反觀我們這里,2010年11月11日《城市商報》報道,為給兒子掙藥費,趕著毛驢車走了8小時到鄭州賣紅薯,76歲的菜農卻遭執(zhí)法者掌摑。同一天,2010年11月11日《揚子晚報》報道,城管驅趕菜販搶秤,賣菜老太無名指被掰斷。這可是發(fā)生在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號稱要建設和諧社會的解放了61年的中國的大地上。
何以有如此粗野的執(zhí)法?說是這些城管的素質低下,或者說,都是些“臨時工”,但是,為什么不從法制與法治上找原因呢?以曾是中國的最高領袖的“無法無天”慣了,這慣性還在延續(xù)下來。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印度吧,幾十個城市的攤販聯(lián)合會總會狀告印度政府,為攤販討要說法,印度法院判決攤販聯(lián)合會勝訴,因為:生存權第一,市容權第二。這可是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問題。我們不是經常在人權闡述上,把吃飽飯這“生存權”放在最前面,也最引以為自豪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