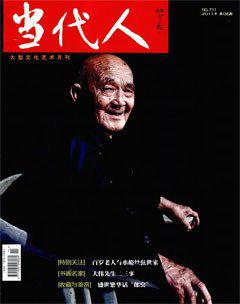內邱牛王廟戲樓
牛之問
邢臺市內邱縣城西十五公里處,是太行山與東部平原的緩沖地帶,這里丘陵起伏,溝壑縱橫,楊柳成蔭。小馬河北岸,王郊臺村南,有一座土臺臨河崛起,古代碑記稱:望之翼然而高,三面環水,一面負村,下石而上土,儼若中流砥柱。臺頂有一座牛王五道三圣廟,俗稱“牛王廟”。和牛王廟相對應的古建筑,是聞名的牛王廟戲樓。
牛王廟戲樓坐南朝北,面向牛王廟廟堂。戲樓左右和廟堂前豎多通石碑,能辨者為清乾隆二十九年、嘉慶十四年、道光十二年、同治十年、民國五年、民國二十二年等重修碑記,莫辨者碑石風化剝蝕,字跡漫漶,或仆于地下,或殘缺不全。道光十二年(1832年)重修碑記載:“牛王廟昔有戲樓一座,所建不知何時,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修后,迄今六十余載。每年三月十五日歌舞祀典。”而乾隆重修碑文僅有“牛王廟修戲臺一座,列于后重(同眾)善人等”若干字,說明該戲樓在清代乾隆年間已無籍可考。現存建筑雖經數次修繕,依然保持典型的明代風貌。
牛王廟戲樓由戲臺和照棚兩部分組成,集磚、木、石于一體,戲臺頂布瓦獸當,單檐卷棚硬山,面闊三間。整個戲臺呈“凸”字形,條石砌就,高出土臺臺面1.20米,戲臺中間立兩根輔柱,兩側砌有山墻,干后墻連接,輔柱間懸掛臺幔,即可圍成后臺。前臺左右外跨一米,名跨耳,齊于照棚,三面敞開,適宜觀眾圍觀,臺口四柱三開間,中間開間較大,適合演員表演,臺底有一券洞,縱貫戲臺,洞壁條石精砌,券頂青磚,白灰抹縫。券洞南口在郊臺峭壁上,原有小門,十分隱蔽。從北端拾階而上,有頂光射入,乃是出口,出口在前臺臺口低部,石板掩蓋,僅見券頂青磚,不知者以為是密室暗道,新版《內邱縣志》記述券洞為排水系統,又是增強嗡音的設備。券洞空間寬大,排水說法十分勉強,從周圍環境看,當為戲班演員臨時住所。
照棚系正卷棚式頂蓋,與戲臺連接,通透剔亮,造型優美。整個照棚由十八根立柱支撐,外圍十根,石制方形,經久堅固,棚內八根,木制圓形,青石柱礎,既有變化又富層次感。照棚木構簡潔樸素,極少雕飾,體現了明式建筑優雅洗練的大家風范。遠遠望去,古柏掩映,陽光斑斕,戲樓照棚如空中樓閣,令人嘆為觀止。
照棚前臉是戲樓的精彩部分,前臉位于半山腰,北跨外突兩米,角檐高高翹起,形似一只展翅欲飛的蝙蝠。檐下有斗拱花三朵,檐兩角各留一鐵鼻,以方便夜間看戲時懸掛燈籠。門廊兩柱上部各置木雕垂花,意寓為照棚入口,以建筑符號限定了內外空間。每年農歷三月十五日,牛王廟會期間,香客云集,大戲連臺,燈籠高高掛起,紅光四射,十里及望。當地有民謠這樣稱贊:南京到北京,唯這兒戲樓掛照棚。
戲樓,又稱“戲臺”,以高臺上露天表演藝技而得名。戲臺由露天到臺上加頂,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據史料記載,戲樓源于唐宋亭閣,四面皆空,稱“戲亭”,金元時期隨著戲曲藝術的進步,其建制逐漸趨于完善并最早在山西一帶流行開來,今山西臨汾、運城等地區保存有多處元代戲樓,即是明證。明清兩代,廟會盛行,戲劇表演空前繁榮,”凡祠廟必造優臺”。尤其到了清代,不僅神廟宗祠,而且同鄉會館、行業祖師廟、富家私園、皇宮大內都大造戲樓,如北京故宮寧壽宮內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暢音閣,上下三層,高達二十多米,是名副其實的大戲樓。清代中期,梨園伶工搭班在戲摟演出,業余時間在京城各酒肆茶樓設臺獻藝,后來演變為各類戲曲表演的固定場所,俗稱“戲園”,即封閉式的戲曲劇場。
戲樓與戲園的區別在于,戲樓的觀眾席為露天,就連皇家的豪華戲樓也不例外,而戲園則是全封閉的,觀眾看戲不必擔心刮風下雨的惡劣天氣。牛王廟戲樓封閉照棚可圍成戲園,即封閉式的室內劇場,應該說是中國戲園的雛形。王郊臺地處偏遠鄉野,遠在明代出現這種戲樓建制,令人驚嘆。清道光十二年”內邱縣志,稱:“牛王廟在王郊臺,院內有戲樓,樣式獨特,實屬罕見。”戲樓的建制,對于今天的世人來說,是一個未解之謎。
牛王廟戲樓的發現,引起眾多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和極大興趣,甚至有學者依戲臺特征將始建時間前推至元代。傳統的明清戲樓,平面呈方形,以屏門隔扇或墻壁分開前后臺,明確功能空間,并設上場門、下場門供演員出入;后臺或設扮戲房,用以放置戲箱道具,供演員扮裝和候臺。牛王廟戲樓沒有隔斷,僅以兩根輔柱虛擬前后臺區域,樂隊伴奏在前臺跨耳,這些特征是元代戲樓的痕跡,表明該戲樓與山西的元代戲樓有淵源關系,是元代戲樓建筑式樣的延續和發展。
牛王廟戲樓帶有元代戲樓痕跡的原因,是明朝山西移民運動所致。元末明初,戰亂迭起,尤其是太行東麓及平原地區遭受“靖難之役”(俗稱“燕王掃北”),河北土著居民被殺戮殆盡,城鄉一片廢墟。自洪武至永樂年間的50年間,明政府數次從山西洪洞縣(今臨汾地區)和山東地區向河北大規模移民,以充實京畿之地。洪洞縣在明朝隸屬平陽府(今臨汾市),是元雜劇發達的地區,河北邢臺的山西移民,正是來自這一地區。他們攜帶故土的生產技術和風俗文化,在河北定居地墾荒治田,立祖建莊。供奉牛馬王,保佑牛馬安康,維系著古代男耕女織的小農生產方式,正如牛王廟殿門上的楹聯語“牛如西山大力士,馬似東海水蛟龍”,反映了普通百姓敬神祀獻,祈福禳災的美好愿望。三月十五日的牛王廟會,酬神娛人,鼓舞歡慶,是祀獻活動的高潮。隨著時間的推移,地域差異性越來越大,山西移民與當地文化相互融合,其后裔則逐漸與故土文化自動脫離。山西臨汾魏村牛王廟戲樓,會期在每年的四月初八日,與王郊臺牛王廟會期相隔二十余天,顯然是地域上的差異造成的,其廟前戲樓,據石柱銘文記載建于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年),即忽必烈執政期間。王郊臺牛王廟戲樓與臨汾魏村牛王廟戲樓有無師承關系,目前尚無定論,但是河北戲樓深受山西戲樓影響并與山西移民有直接關聯,則毋庸質疑,如邢臺縣東石善村戲樓,據村中老年人講,系十八家籌資按山西故土戲樓原樣建造,就是典型一例。由此可知,王郊臺牛王廟戲樓具元代建筑元素不足為奇。
縱觀中國古代戲樓,無論城郭鄉野還是皇宮廟寺,均取坐南朝北或東西向,牛王廟戲樓也是如此。中國傳統禮制以北為尊為上,東西次之,南向下等,建筑形式凡官署祠廟殿堂居北面南,以示尊貴,威嚴地位不可動搖,富家豪宅,北為上房,東兩稱廂房,南稱下房。酒宴就座,北為主席,陪客側列,面主者為下座,直到今天,人們還保持著這樣的社交禮儀。戲樓的方位取向,反映了封建社會嚴格的等級觀念。
郊臺頂地勢平坦,古柏蔥郁,清風習習,曾經鑼鼓鏗鏘的戲樓,歷數百年風雨,如今靜靜地矗立著,像是一幅豐富多彩的民俗歷史畫卷,徐徐展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責編:孫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