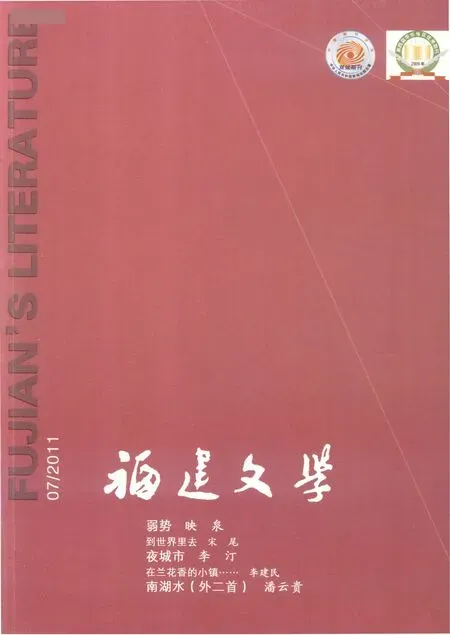到世界里去
宋 尾
到世界里去
宋 尾
父親半蹲在下午的暖陽里,他邊上圍攏了熱心人——那些看熱鬧的鄰居。他們不是來看父親磨刀,而是指望著這次能瞧到稀奇的。哧哧的磨刀石讓他們心煩意亂,人群中不耐煩的噪聲多了起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是想盡快看見結果。哪怕這個結果跟他們并無什么關系。
父親在不耐煩的咳痰聲和咒罵聲里磨完手里的刀,這才回屋,提著那只剛剛斷氣的死狗出來。門口的鄰居們立即像水一樣散開,為他敞開一道順暢的口子。
鄰居們袖手觀望父親費力地把它倒懸在粗壯的槐樹干上,仰起頭,張大嘴,一眼不眨。當刀子扎進它的肚子,霎時,四周一片古怪的安靜——圍觀者全部屏住了呼吸——他們,滿懷嫉妒和期待的復雜心態,急切地等候一個驚人的發現。
在勝利二路,類似的場面很常見。幾乎每戶男人都有這種好手藝,只要有機會一定要當眾表演一番。剝水蛇皮,剝刺猬皮,剝肚子鼓脹的水老鼠的灰皮——但這次不同,這次,父親要剝皮的這只狗,可不是一般的狗。
顯然,鍋爐工父親糟糕的手藝遭到他們的無情嘲笑——在很多方面、很多時刻以及很長時間,這種嘲弄一直在勝利二路持續著。鄰居們又像是惋惜,又像是幸災樂禍,說,茂堂啊,錯嘍錯嘍!你搞錯了噻,該先扎喉管,從脖子那里劃開,才能取下一張整皮——整皮跟破皮的價錢差到哪兒去了喲。
在爭議聲里父親把皮給扯下來了。人群中終于發出一陣帶著輕微壓抑之后的騷動——但解剖后的結果顯然令他們失望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釋然了。去掉皮后,他們沒有在這狗的內部發現什么值得驚奇的東西,沒有珍寶、也沒有可拿來炫耀的東西,沒有!包括狗的內臟和骨骼、乃至軀體的任何一樣東西,看上去跟普通的狗沒有什么區別。
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被剝去皮的狗。
它在我眼里不像是死了,更像是剛剛出生。嫩紅色的肉、四處游走的筋和血管清晰可見,在那種粉嫩的紅色之上包著一層極薄的乳白色的膜。我戰栗著望向它,它是那么陌生,仿佛這根本就不是我熟悉的它。我依然相信它并沒有死,但無論如何,它不可能再重新穿上那身被扎漏了的皮囊了,更不可能讓見到它的人發出嘖嘖的驚嘆了。
我定定地看著那些濺在上面的血污,它們不再發亮,而是慢慢變成一種深黑色的物質,就像被凝固的陰影。
我是在菜市場撿到它的。
那時,它在一堆菜葉堆里找食。那種臟兮兮的,到處可見的癩皮土狗。我注意它,是它只有一只眼,左眼不知被哪個人用什么東西———也許是尖頭的木棍———捅穿了,也可能并沒完全瞎掉,眼皮耷拉,膿汁和眼淚從深黑色的眼眶里滴淌出來,散發出一股腥臭味。當我走近,它用那僅存的眼珠盯著我。但使我害怕的,是那只破碎的瞳仁,就像砸碎的玻璃跟液體渾濁地混合在一起。
憑經驗,我知道這時貿然跑開是不妥的。我小心向側行,試圖繞過這個潛在的危險物。可它不給我逃離的機會,也不知我身上有什么東西吸引了它,它一直攆著我。我走幾步,它走幾步;我停,它也停,蹲下后腿,兩只前爪撐著地面。
它一直跟著我回家了。在門口做煤球的父親發現了它,他沖我吼,“你從哪兒帶了條這么丑的狗回來?嘿!還是個獨眼龍!”
他隨手抓了一根晾衣服的竹篙朝它掌去,嘴里一邊還發出“嗖嗖”的怪聲。人們都習慣用這種聲音來驅趕討厭的動物。竹篙并沒擊中,它倉皇溜出很遠,一邊跑一邊回頭。
第二天放學后,在巷口我又看到它——但前次我體味到的那種兇惡奇異地消失了。它蹲在地上,用惟一那只眼,憂愁地看著我。似乎整晚,它都蹲在那等我。好像它流浪了這么久,就是為找到我。
說不清為什么,我覺得它就是我的。
我領著它,安置在后院的露天壩子上。那里,很安全。無論對它,或是對我。晚上我端了一碗剩飯去,它悄無聲息地從黑暗里走近。吭哧吭哧,那種貪婪又滿足的吃相我從未見過。臨走時,碗底的積垢舔舐得干干凈凈,在夜色里透出一些反光。
這只狗的長相引起了街坊的興趣。
“這雜種也丑得太出奇了吧。”街上的海棠麻子似乎死活不相信這是狗,“這是變種!”
他的跟班,那個討嫌的茍三說,“你看,你們兩兄弟長得太像了,去,找個鏡子來。”
我不同他們爭辯。
因為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已經不大記得為什么會這樣,但記得母親為此帶我去了很多次醫院,朝我血管里灌了許多青霉素,沒用。祖母于是更加篤信勝利二路毛仙人的說法,說是喉嚨眼被一個什么臟東西堵住了,需要“開竅”。但除了燒紙,畫符,喝一些味道發臭的黃水,從祖母手里接過錢,他的方子也并不怎么奏效,我還是那樣。但背著他們,我能跟自己說話。現在,我又多了一個,我能跟它說話。它聽得可仔細了。
這條街上的孩子再次找到樂子了——他們沖它吹口哨,扔石子。把它圍堵起來,撿了很多小石子兒,比賽——看誰能砸到它。
每天,它身上掛著大大小小的腳印兒,有時還滴答著一些唾液。我能分辨出這些口水是誰誰的。其實,就是當著我,也沒什么可避嫌的——茍三最愛干的,就是裝著漫不經心地經過它,突然橫出就是一腳,反皮靴踢得它猛地從地上嗚嗚跳起來。
過了幾天,他不知從哪找來一個人造革的套索,圈在它的脖子上,硬生生地拖著它去找黑豹打架。黑豹,勝利二路最兇猛的狼狗。
它回來時被咬得渾身都是血水,跟灰褐色的毛皮粘連在一起。其實,我遠遠躲在巷口,聽到了它的悲鳴,但我不敢走過去,我怕它看見我,我也怕這街上的人看到我,歡暢地打招呼,嘿,看見么!你的狗!——我心里有一種隱秘的羞恥。但我的確很難受,被撕咬的仿佛是我自己。
眼看著父親結婚的日子一天天臨近,徐云天如坐針氈,決心孤注一擲。2012年2月16日下午,徐云天敲響了父親徐河的家門。開門的是吳麗藻,坐下后,徐云天開門見山地說:“我就是追求你的‘英雄’。”
它艱難又緩慢地走近我,收起四肢,匍匐在我腳下,整個身軀都在發抖,抖得很厲害,像是害了重病的老人,喘息聲很響,很渾濁,黏糊糊的口液大塊大塊地從口腔里掉下來,打濕了地面。我很想伸手去摸摸它。一陣風吹過,從它身上傳來一股強烈的腥臭味,比往常更濃。我縮回了手。
如果不是發生了那件奇異的事情,我仍然跟其他人一樣,也一直認為它是一只狗:一只卑賤的狗,丑陋的狗。我們總被眼前的東西有意無意欺瞞著。
每天,它跟著我去上學。我進到學校,它就在外面。但這個清晨,同學們突然對我有興趣了,確切地說,對我屁股后跟著的這條獨眼狗感興趣了。
早自習的鈴響了,他們依舊圍著我和狗,興奮地討論它那只淌著淚的瞎眼,還有同學把講臺上的粉筆掰成一節一節的,哼著游擊隊隊歌——“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向它投擲——我臉上也挨了幾下,火辣辣的。
有個膽大的男生,捅了一下它那臟兮兮的眼眶——然后飛快地收回自己的手指,將上面的暗紅的黏液擦到我的后背上,惹來背后女生一陣陣快意的笑聲。我很想說些什么制止他們,我越是緊張,越是生氣,就越是一句話也憋不出來。但是,它卻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震驚的事。它突然哇哇跳開,嘴里甕聲甕氣地發出一種聲音,就像裝在土壇子里的那種聲音,“媽拉逼!”包括我,所有人都被這個古怪的聲音嚇到了,男生忙不迭扔下手里的鉛筆頭,一哄而散,女生驚慌失措地跑開,甚至還有人哭了。
這事被幾個好事的女生報告給班主任了。班主任很生氣,首先,她覺得我不應該帶狗到學校來;其次,她認為那句臟話肯定是我罵的——狗怎么可能說人話呢?
我很想辯解,不是我要它進來,是同學用樹枝和木棍,追著它闖進學校的。而且,我也沒說臟話。但我沒說。最后,她讓我請家長來。
我回了家,但沒告訴任何人——上午發生的這件事。我知道,要是告訴父親的話,招來的肯定又是一頓好打。他的巴掌像鐵塊那樣,貼在臉上,能讓你的一切——比如神經、知覺,還有時間,都猛然停頓下來。如果告訴祖母,她必然憤懣地帶著我去學校操場踮起小腳大喊大叫,老師的祖宗八代都要被她一溜罵個遍。相比挨打,我更怕這個。
但這些煩惱對我來說已經不算什么。我心里充滿莫名的興奮,這只狗,居然能罵人,這多奇妙啊!
我特別想知道,除了罵人,它還能說別的什么話嗎?我幻想著,它是個天使,或是一個外星人,它能講幾十種語言,它能看懂每一個人,它可以幫我做每一種家庭作業,還能給我偷來答卷,甚至,它可以長生不老,它是神仙專門派來陪我耍的……
但沮喪的是,無論我怎么逗它、求它,它還是那只沉默的狗,就算踢它一腳,嘴里蹦不出一個詞,哪怕是那句“媽拉逼”。這讓我開始相信老師,懷疑自己的耳朵——難道,這真是錯覺?
我沒請家長,更沒回學校。我們在縣中學的垃圾場玩,這里像天堂。半截的粉筆遍地都是,還有彩色的;有書,作業本,文具盒,塑料的,鐵的,舊的,半成新的。我翻找的時候,它從垃圾堆里噼啪扒拉出一個鐵文具盒,斑駁的花漆已經辨認不出圖案。打開一看,竟然是錢!七塊四毛,靜靜蜷在里面。我們像小偷一樣匆忙逃離。
我苦苦思索該怎么花掉它,連環畫,去公園打氣槍。突然,我想喝汽水,咕咕冒泡的汽水,在小賣部。
在街口的國營理發店前,我們被十幾條腿攔住了。
這里總圍攏很多人,他們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仿佛就是待在那里。下象棋,打牌,吹牛皮,罵架,爭爭吵吵的。現在沒有牌局,他們的屁股全部擠在兩三條烏青發亮的長凳上,好像為什么事爭論不休,手間的煙燼隨著劇烈的肢體動作散落一地。
我跟它經過時,一切突然停頓下來。
“這不是茂堂的兒子嘛!”茍三的父親謝大腳看見我,大聲說,“你不去上學,在街上瞎跑!”我當然不會回應。再說大人們說話,往往并不是真的想問我們什么。
他擺擺頭,對旁邊的人說,“小雞巴,老是不開言。”
“那是,哪像你兩個兒子,好精靈喲。”劉家爹搖頭,“這伢子,這么大,話都不會說。”
“啞巴?”有人問。
雜貨鋪的陳老頭撇嘴說,“原來會說的,說是中邪了。”
“嗬!有鬼氣。”這人驚嘆,“這狗!唷!這是狗嗎?”他說,“這是哪樣品種!”
“還品種?”毛家爹隨便瞥了一眼說,“沒長全的土狗!”
“這是公還是母?”有人問。
“跟你一樣,”毛家爹說,“雞巴打架,關你卵子事!”一群人哄笑起來。
“母的!”另一位老頭笑,“老東西!公母都不分。”笑聲短促,像是被人扼住了氣管。
“放你娘的屁!”毛家爹勃然大怒,指著對方的鼻子,“你敢跟我賭?”
“賭就賭。”對方說。
毛家爹霍然起身,一雙像松弛的橘子皮一樣滿是斑點的手,突然鎖住它的脖子,它被倒提起來,在空中四腳撲騰。“哎喲,”毛家爹大叫,“還真了不得。這是陰陽狗吧?”毛家爹拎著狗,“老謝,你去幫我把推子拿來。”
“拿推子干嘛?”謝大腳問。
“我給它搞個造型。”他叼著煙叫。
“無聊!”他進去把電推子取了出來——惹得理發店的張師傅一陣亂罵——“狗日的,老子的推子是給人剃頭的,不是給狗用的!”
“給它弄個啥標志呢?”毛家爹向眾人發問。
“推抹光!”有人說。
“那推到什么時候?”他擺著手上的推子說。
“推個井字!”有人說,但馬上就有人否決,“這好復雜哦。”
“那么,推個德國佬的標志嘛!!”
馬上又有人跳出來,“復雜!搞個簡單的。快點快點!”
“那……推個十字!”有人建議。
“呃!”毛家爹咧嘴一笑,“來幾個人嘛,幫我按著它的爪子。”
謝大腳幾個人呲著牙按住四個爪子,它開始哀嚎,但它的嚎聲被徹底覆蓋。這群人如同過節那樣,興高采烈。
我不知所措地看著。突然就聽到了那個吼聲——“媽拉逼!”好像是從地心里傳出的聲響。老謝被唬到了,忙不迭扔下手。問,剛才是哪個在罵?
“媽拉逼!”
這次,大家可全聽得真真切切。四個人觸電一樣撒了手。它順勢一蹬從他們身邊跑了過去——那個十字,只完成了一半。在它的背脊上,留下一個奇怪的符號:⊥——“上”字少了那一橫。
我在后面攆,迎頭撞見提著空酒瓶去打酒的父親——一聲大吼,“狗日的,你沒去上學啊?!”我拔腿就跑,大腦一片空白,跑得魂都飛到天上去了,一顆心撲通地跳,就像是要從嗓子眼里迸出來了。
我帶著它躲進家背后的小院子里。
這里每家每戶都用籬笆、木頭,或是鐵絲和磚頭徹成一個一個獨立的院子,平常沒人會去。我們家也有院子,可以連接到廚房,平常是不開的。里面堆滿雜物,祖父還在院子里種養了一些花,都是些沒名堂的花種,梔子、雞冠花,墻沿上則放了幾盆仙人掌。院子里還有一群小母雞,一只體積龐大的老公雞,走起路來步履蹣跚。還有一個舒舒服服的大水缸,我在里頭躺著,它蜷了身子,窩在水缸邊。
我問它——我發現對著它說話比想象的還要自如——“你是狗嗎?”
它沉默。
我又問,“你是從哪里來的?你怎么會說人話?”
它還是沉默。
我朝四周望了望,繼續問,“現在旁邊沒有人,你可以告訴我實話!”
可是,它依舊沉默不語。挪了一個方向,背對我,懶洋洋地把短短的尾巴蜷起來窩在地上。
我失望極了,我累了,剛才一陣瘋跑讓我虛脫。
躺在水缸里,我突然聽到從前面傳來悲傷的嗩吶聲——那是隔壁的蔡家婆死了,早上我擠進去看了,她睡在堂屋中央——一張白色的墊布上面,人干枯得不成樣子。比她活著時還要瘦,但比她活著時直挺了許多。我盯著她看了許久,我不知道人死跟活著究竟是什么樣的差別,人死了,會到什么地方呢?
我帶著一種惘然的情緒,問它最后一個問題,“蔡家婆死了,你說我還能再見到她嗎?”它轉頭,眼睛無辜地看著我,頭點了一下,又搖晃了一下。
那么,到底是能還是不能見到呢?要知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死人。死亡,既讓我恐懼,更讓我好奇。以前我最怕的是鬼,但現在蔡阿婆死了,我最想遇見的,竟然也是鬼。
天黑了,我凝望頭頂上密密麻麻的星星,不知道它們為什么有的亮,有的又暗,有的大,有的又小。它們是誰的,是誰把它們放在天上的?我又想起蔡阿婆了,在心里默念:“婆婆,你終于死了,你能不能回來告訴我,你在什么地方?”我突然感覺一陣恐慌,要是她死了再不能活過來,那么,接下來的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一億年……直到萬億年,她都不會醒來,也就是說,以后無論發生什么事情,她一樣也不曉得了。盡管我的數學那么差勁,但這個龐大而漫長的數字依然讓我心悸,死去的人靠什么死去這么久呢?……我在無盡的狂想中睡著了,我并沒夢見蔡阿婆。在一陣劇烈的疼痛中,我醒了,我看見父親兇狠地站在面前,用那只在鍋爐邊翻砂的右手,使勁揪著我的左耳。我的耳朵好像消失了一樣。
我和我的狗被隔離起來了。
那晚,父親噴吐著濃重的酒味,把我吊在床上用軍用皮帶狠抽了一頓,一邊抽一邊咆哮,其實誰也不曉得他在說什么。直到祖母把房門撞開,踮著小腳照著他臉上就是一巴掌,“狗日,就曉得喝!把伢兒往死里打!抽筋的砍腦殼的!老子涮你,看你疼不疼?!”父親臉都不揉一下,回到堂屋繼續喝。
至于它——被拴在窗戶上。它現在成了勝利二路的新聞焦點。每天,都有很多人來參觀它,隔著院子的柵欄,對著它指指點點,品頭論足,爭得面紅耳赤。他們是來討罵的——帶來吃剩的骨頭,扔向它。然后,渴望親耳聽到從它嘴里迸出的那句罵聲。
但它很難被觸怒。它甚至不拿正眼瞧瞧這些望穿秋水的觀眾。偶爾,當從它嘴里發出一些嗚嗚咽咽的聲音,哪怕是含混不清的聲音,也足以讓圍觀人群興奮起來。
陳醫生篤定地認為——他是一位曾經的赤腳醫生,幾年前才回城——狗能說話并不奇怪,他曾在鄉下見過會吹笛子的水牛,還有會說人話的猴子。他判定,這狗能說話,原因出自它的喉管,肯定是那里的畸形,導致發出這種類似人的怪聲。他提議,由他主刀,將它開膛破肚,重點是,檢查它的發音系統,是不是因為畸形或堵塞而產生的某種發音變異。
當然沒人會同意他這么干。并且,他的觀點被駁斥得一文不值。糧校的劉副校長——雖然他住在這條街上,但這是頭次見到他來串門——一開腔就滿嘴文化味,每句話末都帶著一個“嘛”字。猴子嘛,說話不奇怪嘛。達爾文說了,人本身就是猴子進化的。水牛會哼哼,這有什么奇特的嘛。但是狗——你什么時候見過狗說人話嘛?就算是喉嚨里長了痔瘡嘛,也不至于說得這樣清晰啊,是不是嘛?
也有人插嘴,說這只狗是狗精,只有狗精才能說人話。
劉副校長輕蔑地說,這根本不是狗。他說它是一種叫訛獸的野生動物,最擅長模仿人類說話,而且一套一套的,專門哄人。山海經上就有對它的記載,說它的肉鮮美無比。
“那為什么它只會一句?”這也是大家共同的疑惑。
“有進化,當然也有退化。”劉副校長的解釋,似是而非,但也合情合理。
不過當他離開,新的爭執又開始了。
老謝說,這不是狗,是太歲。有人引申道,怕不是單純的太歲哦,太歲哪里是這種形狀吶!怕是——狗跟太歲的雜種喔?這種言論,一般都會博得會心的哄笑。
爭議看來一直在持續。但毫無疑問,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畜生。大家普遍這么認為。
這只不知來自哪里也無人收養的土狗,突然變得走俏起來了。
有人托人來買它的,還有直接跑來討價還價的。沒人跟我商量,但看母親的樣子,好像動心了。
不過,祖母堅決地拒絕了這一切誘惑。為此母親丟掉了自己在棉紡廠的悠閑的崗位,被調去三班倒。因為她的廠長要買下這只狗的愿望也落空了。
一個后半夜,警醒的祖母發覺了動靜,趕緊將祖父推醒,讓他到后院瞧瞧。祖父一進到院子,就被人從后面一棒子打暈在地。兩個模糊的人影翻墻垣溜了。據祖母分析,賊人的目的肯定是這條狗——她到達院子的時候,除了暈倒在地的祖父,狗也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嘴邊叼著吃剩的肉塊——下了藥的。要晚點發現,狗就要被人給弄跑了。
這給全家蒙上了一層陰影。當晚,他們開會商議。半夜去把毛仙人也請來了。我不知道他們商量什么。
我扒著后廂房的窗欞,但怎么也看不到它。我只看到一團黑乎乎的夜晚,很薄。后來我聽到一種聲音,也很薄。像是哭,又像在笑。我覺得是它。
第二天,我坐在門檻上曬桃花太陽,突然聽到從后面院子里傳來一聲慘吠。是它,是它在叫。
透過窗子,我能看見祖父牽著鐵鏈子,父親執著一根大鐵棒——大板車車轱轆中間的那根軸承,十二三斤——狠狠地敲在它身上,它一邊哀叫,一邊躲跳,鐵棒像雨點落在它的背脊、頭顱、屁股、尾巴、腹部或者任何一個可以砸到的地方,我此前從未聽過那種聲音,沉悶、脆響。
我大聲哀求,但這沒用。
它匍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氣,它那只瞎眼里膿汁都流干了,大量鮮血從那里涌出來,將那些殘積的東西都沖掉了。它的背脊塌陷下去了,一層光禿禿的毛皮耷拉在凹陷處。它身上也再看不到任何人的口水和腳印,全是大塊大塊的紅色的污漬。
他們合力棒打了一下午。父親問,“怕是行了吧?”祖父說,“你就是把它敲死了,只要放在地上,它就能活過來。命硬得很。”“那怎辦?”父親問。“你把它吊起來,只要不讓它接地氣,它就活不成。”于是,父親用鐵鏈子重新把它套起來,找了根長木棍子擱在院墻的兩端,把它倒過來,吊在半空。
半夜,我又聽到那種嚶嚶的哭聲。我睡不著,偷偷爬起來,躲在窗子背后。那晚的月亮很圓,藍幽幽的月光鋪在地上,也鋪在它黯淡的身軀上。它倒懸在院子里,格外凄慘。它在哭。我看見它的淚水淌在地上,有一攤那么多。
天亮時,我回到床上。一只尖嘴的蚊子,嗡嗡飛旋在床帳里,像在找自己遺落的什么東西。
它被吊了三天兩夜,這才死了。
父親早早燒了一大鍋開水——他要剝皮。這也是勝利二路的傳統。幾乎每戶男人都有這種好手藝,剝水蛇皮,剝刺猬皮,剝肚子鼓脹的水老鼠的灰皮。只要有機會一定要當眾表演。
門口早早就擠著圍觀的人群,但剖開后的結果顯然令他們失望了。更準確地說,是釋然了。去掉皮后,沒有在這狗的內部發現什么值得驚奇的東西,不管是內臟和骨骼、乃至任何一樣東西,看上去跟普通的狗沒什么區別。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被剝去皮的狗。
它在我眼里不像是死了,更像是剛剛出生。嫩紅色的肉、四處游走的筋和血管清晰可見,在那種粉嫩的紅色之上包著一層極薄的乳白色的膜。它是那么陌生,仿佛這根本就不是我熟悉的它。我依然相信它并沒有死,但無論如何,它不可能再重新穿上那身被扎漏了的皮囊了。
那些濺在上面的血污,慢慢變成一種深黑色的物質。
父親剝掉它的皮后,將內臟取出來,遞給祖母,她很細心地在內臟中挑出心臟和舌頭,用一張紗布包好。鄰居們起哄,“總得給我們一點湯吧?”父親敷衍著,“行,行,好,沒問題。”起夜霧時,他將剁好的肉塊,用報紙包好,選了幾戶常走動的街坊,每家分了一些。
這晚,全家人——兩個舅爺、幾個同姓的叔伯都來了——過節一樣,圍著吃爐子。爐子燒得旺旺的,綠色的火苗直往邊上亂竄,鍋里燒燙呼呼的,放了辣椒的紅湯煮得沸沸的,里面——它被切成一塊一塊,在湯鍋里上下翻滾。
他們在喝酒,連祖母和母親也倒了一杯。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喜氣洋洋的。媽媽從鍋里撈了一塊肉,遞到我的碗里。我擰著身子,躲過她的筷子。
這個姿態引起了父親的注意。他站起身來,我立刻——畏懼地坐直、端正自己的坐姿。但驚訝的是,他并沒對我的不敬動怒,反而溫柔地撫摩——當他的手掌放到我頭頂時,我全身都繃緊了——我的腦袋瓜,隨后,他轉身用筷子夾了一塊肉,放在我碗里,輕聲說,吃吧。
我不會拒絕,也不敢拒絕。
我將那塊肉使勁攪拌在飯粒里,屏息,吞了進去。
這晚我夢到它了。
我們一起到縣河邊溜達,我一直追著它問,“你是誰?”它笑嘻嘻地,“我是我啊。”
我責備它,“怎么一直不跟我說話兒呢?”它笑嘻嘻地,“我一直在跟你說話兒啊。”
“是嗎,我還不曉得你叫什么。”
“我沒有名字。”它補充說,“但——你可以用你的名字,叫我。”
嘿,我覺著很有意思。“那你從哪里來的?”
它問,“你知道我從哪里來嗎?”
“我從世界里來。”
“‘世界’在哪里?”它剛剛提到的這個詞,我還是第一回聽說。
“怎么說呢,它很大——”它很嚴肅地用手畫了個圈給我比劃著,“它大到沒有邊際,你永遠都走不出去;但其實也很小,比你的指甲還小,比頭發還細,如果不用心,你很難看見它,唔——”它接著說,“它就藏在你的心里。”
“在我心里?”我覺著古怪。
“也可以說,我們都在它的身體里,”它很神秘地說,“世界是平行的。”
“平行的?”我很詫異。
“也就是說,”它緩慢地說,“在另一個看不見的地方,還有一個你。”
“什么?”我悚然叫道,“一模一樣的我?”
“你等著,我們馬上就要在一起了。”然后,它一個猛子,向我的肋下扎進來——先是它的頭,接著是軀干……我的皮囊被某種力量撕開,脹得難受。
“疼!”我說。
“噓!”它微笑著,這是我對它最后的記憶。然后,這張笑臉也進到我的身體。
一陣劇痛使我蘇醒過來。我驚訝地發現,幾乎全家人都簇擁在房里。還有毛仙人,他執著一把手術刀,熟練地切割著我的胸腔;父親則以一種我從未見過的虔誠的姿態,捧著一個白紗布包——喔,我認出來了,那是它的心——小心翼翼放進我的身體。然后,我看見一縷針線在我身上縫縫補補。我好奇地盯著他們,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么,為什么要這么做。但我沒有害怕,甚至沒有一絲疼痛。
很快,我又睡著了。
責任編輯 石華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