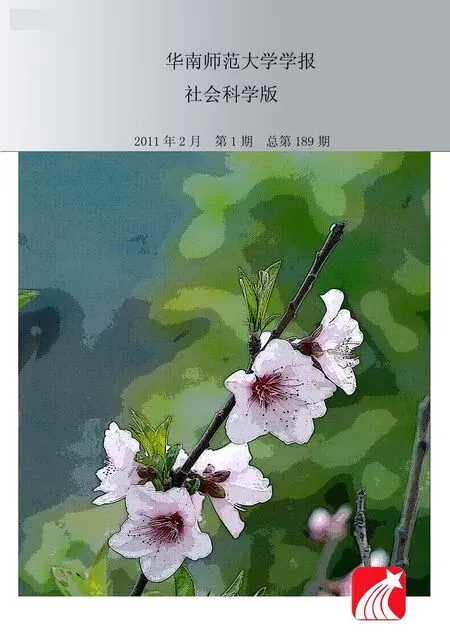北宋熙豐名臣致仕文學研究
吳 肖 丹
(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 廣東 廣州 510006)
宋代“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注]趙翼撰、王樹民校正:《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二五《宋制祿之厚》,第530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致仕官待遇優厚,生活閑適。士大夫處于“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架構下,又“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注]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第27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他們的致仕具有別于前朝的特殊意義,是士大夫由實踐政治理想轉入回歸個人空間的特殊方式。自太宗以來,取士重視年齡,用人注重“老成”,“崇老”的文化對于致仕官而言也是一種有利氛圍。在熙寧、元豐的特殊政治條件下,這些特點更是得到充分體現。北宋文學的繁榮,熙豐與元祐都是重要的階段。[注]蕭瑞峰、劉成國:《“詩盛元祐”說考辨》指出從創作群體、作品數量和藝術質量等方面考察,“詩盛元祐”說難以成立。見《文學遺產》2006年第2期。“議論爭煌煌”的朝論固然是宋初經世致用思潮的延續,而熙豐致仕官回歸文人身份,追求理趣、歸于平淡以及崇尚老美的創作,則無疑對這一時期乃至下一階段文學成熟有深刻的影響[注]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指出追求雄豪奇峭而歸于平淡雋永為北宋變革時期文學思想,以追求理趣和老境美為北宋成熟時期文學思想,而兩個階段交匯于熙豐時期。見該書第80-83、112-121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一、北宋致仕制度述略
官員退休古稱“致仕”、“致政”或“休致”、“休退”。《春秋公羊傳·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致仕,還祿位于君。”《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仕。”致仕制度始于秦漢,逐步完善于隋唐。宋代推行祐文政策,“朝廷以恩遇老臣,無所不厚”[注]蘇轍:《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欒城集》卷三九,第7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致仕制度“完成了從禮到法的轉變”[注]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第414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其主要制度如下。
(一)承襲官員年滿七十致仕的慣例
神宗朝“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禮見于經,而于今成為法”[注]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五五《食貨五》,第1396頁,中華書局1975年版。。官員經所在州府上表、札,普通官員經吏部審查合格、中高級官員直接由皇帝或中書審定后得到告、赦,便可致仕。
(二)致仕官俸祿待遇優厚,規定也更明確

(三)升轉官資、蔭補、恩例等待遇寬裕
宋代官員致仕時升轉本官一級寄祿官資或官階成為定制,還享受帶職致仕和冠帶致仕。“古則皆還其官爵于君,今則不然,故謂之守官致仕,惟不任職也。”[注]趙升:《朝野類要》卷五,第56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這保證了致仕官的社會地位。蔭補、恩例主要照顧上層官員,相當優厚。
此外,宋代一般以道觀設宮使、提舉、監岳廟等祠祿官,用有官階、官名而無實際職權的榮譽官位安置致仕官,還有讓致仕大臣參聽朝政、修書授業甚至復仕的特例。
可見,宋代致仕制度為士大夫退出官場后的地位和經濟提供了穩固的保障。朝廷優賢養老,雖不強硬阻止官員戀棧,但士風也以知止勇退、始終全德為重。如開國元勛王彥超帶頭致仕、真宗時孫冕題詩掛冠皆傳為美談。從制度及當時致仕官的處境看,致仕生活不是黯淡的末路,而是享受純粹自由的文人空間的坦途。優渥的經濟基礎、進退自如的心態,使北宋致仕官的文學創作有別于前代,對于北宋文學思想的構成也有特殊意義。
二、熙豐致仕官的文化背景及創作關系
對于宋代士大夫而言,致仕不僅僅是退休、還祿位于君那么簡單。在致仕一事上包含了這一時代深刻的“士”的精神。它與士大夫的政治立場、個人修養和人生志趣密切相關。政見不合,致仕是對政見的堅持;勇于知止,致仕是人格完善的一部分;身纏俗務,致仕是回歸自我、尋求自由的方式;傾慕老成,致仕官是令人尊敬的群體。要之,致仕生活是人生一種圓融境界的展現。
去掉官僚的身份,回歸純粹的文人學者的生活,致仕是宋代士大夫實踐他們進退觀的特殊方式。文官制度使文人成為了政治主體,從慶歷新政開始,隨著道統的復興,文人的自覺參政意識高漲。到熙豐時期,通變救弊、志在當世的思潮深刻影響了士大夫的主體精神。圍繞因循與變法、理財與重義、君子與小人,士大夫展開了激烈的爭辯。在此期間,士大夫進退灑脫,為公而不為私,行為磊落。一旦政見與統治者所施行的政策相左,往往不會附和行事,盡力而為仍無法實現自己認為有益的主張,則會選擇身退:請求外放、調任閑職或致仕。前兩者不干主政,也可視為半致仕狀態。這種現象在熙豐時期紛擾的黨爭中不勝枚舉。如:歐陽修于亳州任上五次上奏請致仕;熙寧三年,不愿附和變法,六上札子請出知淮潁間小郡,改知蔡州,又三次連章告老;熙寧四年,致仕歸居潁州西湖。其出知蔡州時,實已處于致仕狀態,自號六一居士。又如王安石嘉祐五年向仁宗上萬言書,知“大事不可為”,在母喪后辭官不出;熙寧七年形勢轉變罷相,一度復出后見事不可為便徹底辭官而去。在熙豐變法中,致仕前在政為敵、致仕后在文為友的現象頗多,也體現了士大夫容美可觀的進退觀。像元豐七年,蘇軾訪王安石于金陵,相與唱和,傾慕對方的文才。當然致仕對一些官員來說并非徹底退休,但是士大夫能恰當把握文人優游自娛和心系君國的尺度。如富弼致仕后專注置酒賦詩,但凡“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注]脫脫等:《宋史》卷三一三《富弼傳》,第10255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在通達的進退觀的影響下,熙豐士大夫在政治紛爭中能保有較為豁達的心態。他們的致仕文學,用蕭散的筆墨升華出高遠的人生況味。
在北宋儒學復興的思潮背景下,主動致仕成為一種群體自覺,體現出超越政治的倫理美學,也是宋代士大夫在人格修養方面對致仕意義的開掘。白居易晚年閑居,以滿足的心態寫下了大量閑適詩,這對于宋人是一種啟發;但從他的《不致仕》看,主動致仕尚未蔚為風氣,而致仕的意義也尚未上升到勇于知止、全德圓滿的高度。在宋代儒學復興的背景下,致仕關乎道德修養這層意義才被士大夫發掘出來。從歐陽修的《謝致仕表》、蘇軾的《賀歐陽少師致仕表》可以看出,“早退以全晚節”(歐陽修《休致》)已在熙寧年間成為北宋士大夫的共識。將人生作為一個修養累積的過程,將修身貫穿整個參政及致仕生活中,致仕階段人生閱歷、學識的積淀尤為值得關注;而熙豐間士大夫的致仕文學也在白居易的閑適主題基礎上,開掘出頤養性情、修身樂道的理趣。
對集政治家、學者、文人身份于一身的北宋名臣而言,參政全身心投入,致仕則是恢復文人身份、回歸自我。兩者只是人生的不同狀態,毫不矛盾。在許多鞠躬盡瘁、輾轉仕途的文人身上,都有一份復歸山林、釋放本真的隱逸情懷。陶潛式返璞歸真的生活,加上參禪超脫世外的心境,是他們致仕生活的理想,像司馬光在洛陽作詩《呈邵雍》:“紫花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陶潛的意義被充分開掘出來,固然是熙豐時期黨爭紛紜下審美思潮演變的結果,也與士大夫對自身理想中的致仕狀態的尋求不無關系。許多致仕官在現實中實踐接近陶潛的生活方式,在心靈上去掉官場的限制,拋棄政見紛爭,全身心投入休閑和文學創作,追求更純粹的文學藝術。他們在閑適容與的狀態中,創作上更能接近陶潛詩中那種自由自然的精神,而風格也趨于平淡。
北宋崇老的文化氛圍濃郁。在政治上,自太宗起,取士便偏愛年長者,唐代那種“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子”的現象在宋代已經罕見。朝廷授命,也倚重資歷深厚的老成者。熙寧二年,范純仁參劾王安石的一條罪狀就是“鄙老成為因循之人”。致仕官的地位及待遇也是政治制度優遇老者的體現。在時代文化精神上,“老”代表一種人生境界上的高度自我完善,為注重修身的宋人所提倡。在藝術追求上的老境、老美,像蘇軾贊張先“子野詩筆老健”,是超越了技巧的自然筆墨,在表現上是絢爛至極歸于平淡的完滿境界,體現了宋型文化對人生、藝術經驗積累、轉化、成熟過程的重視。正如錢鐘書《談藝錄》所說“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詩,晚節思慮深遠,乃染宋調”。致仕生活處于人生的最后階段,最宜于表現表現藝術的老境。才思情感雖然不可避免受自然力限制,但經過長時間創作鍛煉,藝術經驗卻達到人生的巔峰,宜于作藝術總結,像王安石歸隱后詩歌從深折透辟走向深婉不迫,正是藝術精進的典型。北宋崇“老”的文化氛圍也與致仕官的地位心態相關。在優渥的待遇下,致仕官是一個為人尊重艷羨的群體,他們對社會有不小的影響力。像文彥博等召開“洛陽耆英會”,賦詩繪像,“好事者莫不慕之”[注]脫脫等:《宋史》卷三一三《文彥博傳》,第10261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又如陳堯佐詩曰:“白發光陰得最多”(《年八十致仕》)。致仕官的怡然自得心態,也豐富了“老”文化的積極內涵。
三、熙豐名臣致仕文學與成熟時期的文學思想
文學創作在熙豐致仕名臣的生活占有重要位置。文學是他們連結同道的橋梁、性命所系的功業和慰藉心靈的寄托。進退的通達、修身的謹嚴、旨趣的天然、審美的老成,使他們的致仕文學不僅局限于白居易式的閑適自在,而是以儒學復興以來的氣格、悟道修身的真淳和他們特有的人生積累,展現出恰如其身份的平淡之美、理趣之美和老境之美。與他們參政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風格相映成趣。論北宋文學,常以“元祐”為成熟時期。實際上,熙豐間作家轉向人生問題的內省,對絢爛至極歸于平淡的追求,在致仕官這一特殊群體的創作中已導先聲。這是文學思潮連貫發展的現實,也與致仕官所處的人生階段特點不無關系。下文將以數個案例試加剖析。
(一)洛陽怡老詩會的理趣
致仕官正式的結社唱和,自白居易組織“九老會”、慶歷七年杜衍五老會后,在熙豐間出現了一股熱潮,并且在組織和主題上較前代有所發展。這些詩社主要由聚集在洛陽的舊黨發起組織。熙寧二年新法推行后,退居洛陽的致仕官富弼、趙丙、到西京御史臺編修《資治通鑒》的司馬光、以太尉之職留守西京的文彥博和理學家邵雍、程顥、程頤等人與其他北方故家官僚頻繁唱和,形成獨特的致仕詩人群。葛兆光《中國思想史》指出這些詩社形成的文學團體構成了足以與政治中心相抗衡的文化重心。這些怡老詩社實際上是反對變法的士大夫實踐“詩可以群”傳統、連結同道的方式。雖然他們的創作有意疏離政治,旨在怡情求真,但是他們的活動及詩歌主題卻浸染了北方故家士大夫最為重視的道德色彩。其活動主要如下:
元豐三年,文彥博發起的洛陽五老會,據《五老會詩》注成員有范鎮、張宗益、張問、史炤。
元豐五年,文彥博發起耆英詩會,于資圣院建耆英堂,由鄭奐畫十二人像于妙覺僧舍。據司馬光《洛陽耆英會序》參加的致仕官有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趙丙、王慎言,還有文彥博、劉幾、馮行已、楚建中、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于富弼宅第治酒賦詩,“尚齒不尚官”。
元豐六年,文彥博又邀程珦、司馬旦、席汝言辦洛陽同甲會。同年,司馬光發起真率會,“以年德為貴”和“以道相高”,立下“為具務簡素,朝夕食不過五味”等強調簡樸的會規[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二二,第15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在簞食瓢飲中領略率真精神。真率會活動頻繁,參加者主要有司馬旦、席汝言、王尚參、楚建中、王慎言等[注]司馬光《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步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詩題交代了參與者。,組織隨意。
除詩會外,洛中致仕士大夫還有多次唱和,其中一次盛大唱和就是和邵雍的《打乖吟》詩。
這一系列洛中耆宿詩會為宴游唱和創新了組織形式,以年長、道高為貴,突出了洛陽世家文人對倫理道德的重視。他們的唱和詩歌也是緊扣真、道等主旨,格調端正平和,契合名宿大儒氣質;而致仕生活的閑適疏放,使這些唱和詩歌在致道中增添了生趣。像司馬光的詩“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經春無事連翻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盡從他笑滿頭花”、“追隨任塵甑,歌笑忘霜髯”[注]司馬光《和潞公真率會詩》、《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步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其二、《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詩二十四韻書懷獻留守開府太尉兼呈真率諸公》。,這樣的詩句在他的集子中是難得的輕松自然之作。而致仕官們也為自己的身份、唱和感到榮耀。像文彥博《五老會詩》:“如今白發游河叟,半是清朝解綬人。”《耆年會詩》云:“垂肩素發皆時彥,揮麈清談盡席珍。”這些唱和,最重要的意義還在于突出返璞歸真、天然平淡的旨趣。像文彥博作《聞近有真率會呈提舉端明司馬》指出“率意從心各任真”、“務簡去華方盡適,古來彭澤是其人”;王尚恭《耆英會詩》指出“服許便衣更野逸,坐從齒列似天倫”;張問《耆英會詩》贊賞“清閑幾席同禪院,山野巾裘似隱淪”,都是強調悟得真淳樸淡旨趣之樂。他們賞識邵雍“高趣逍遙混世塵”(呂希哲《和打乖吟》),正是對能在日常悟道、并于平淡的生活狀態中獲得真趣的人生的肯定。這也是致仕官們所追求的境界。熙豐致仕名臣以詩社群聚的方式結合同道,從志趣相投的唱和中獲得精神的超脫和愉悅;而注重道德修養和對真淳樸淡旨趣的追求。這對于文學思想的發展無疑有承前啟后的意義。他們的唱和引起了當時詩壇的普遍關注以及后代文人的追慕,宋人筆記對此記載尤詳。[注]僅宋人記載就見于葉釐《愛日齋叢抄》、洪邁《容齋四筆》、胡仔《漁隱叢話后集》、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葛立方《韻語陽秋》等
(二)歐陽修潁中修文的平淡
對以文學為畢生事業的致仕官而言,全身心投入前期創作的整理、修改、總結以及記錄人生閱歷是他們致仕后的重要生活內容。他們的這些活動影響到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文獻面貌。淺見洋二指出:“在一個作品從草稿狀態走向定稿的過程中,文集的編纂也成為其中的一環。”[注]朱剛譯淺見洋二著:《“焚棄”與“改定”——論宋代別集的編纂或定本的制定》,載《中國韻文學刊》2007年第3期。改定作品、編纂文集的自覺飽含了作者對自身文學地位的重視和對作品流傳的期待。熙豐間歐陽修通過乞請致仕、爭取時間修改整理文集、撰寫筆記就是一個典型。
相對于留在繁華的兩京,歐陽修選擇了寧靜的陋邦安養晚年。他致仕前幾年已處于過渡致仕狀態。皇祐元年他自請改知潁州,萌發致仕終老于西湖的念頭;治平四年赴亳州上任又取道穎州,為歸老作準備。在亳州任上,沉醉佛學、老莊的他心態已與致仕無異,于九月作《歸田錄》序并開始撰寫《歸田錄》。“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馀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以筆記小說這種輕松的文體總結政治生涯。熙寧二年,《集古錄目》凡跋三百九十六篇、《歐陽氏譜圖》撰成,則是對一生學術收藏的總結。熙寧三年,他更號“六一居士”,向往提前致仕。熙寧四年,六十四歲的歐陽修歸隱潁州西湖之濱,與兒子們一道修訂舊稿,編纂成《居士集》五十卷并撰寫了《六一詩話》,對一生的文學創作及藝術理論作了完滿的總結。
歐陽修致仕前的準備和致仕后的活動,都緊緊圍繞文學這一事業,帶有明顯的總結色彩。即便是創作,也是擇取了筆記這一簡單靈活的文體,契合他致仕歸隱的生活和心理狀態。相對于他蘊含“六一風神”的散文,這些筆記更加平易簡潔,淡無痕跡,有情感消褪的因素,也折射出居士生涯的枯寂平和。這種境界,無疑對追求平淡的文學思潮有所啟示。《歸田錄》序成于蔡州任上,編撰定稿在歸穎后,擇材“掩惡揚善”,少了批判的年少氣盛,而是以寬厚平和的心態頌揚士大夫的道德倫理美,像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曹彬“仁心愛物”,多用白描手法,不事雕琢,筆墨簡遠。致仕后寫成的《六一詩話》把讀詩感受、寫詩體會、詩歌名句與掌故輯錄成冊,“集以資閑談也”,開拓了文學批評的新體制。而正是這種非嚴格的文學批評,體現了歐陽修對平淡自然的一貫追求。作為文學評論,他的分析具有客觀性又有感性的體悟,組織結構有很大的隨意性,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作為隨筆散文,有深中肯挈又形容絕妙之語,但又平易簡潔。不作高深的理論,連早期的曲折俯仰也消解。這樣的筆墨,抒寫致仕官閑適的心境,也適合為一生的藝術經驗做總結。
歐陽修致仕后所享的光陰只有一年,但從他致仕前的準備,可見出北宋士大夫對致仕生活以及自身文學成就總結的重視程度。從早年對平易暢達文風的不懈追求,到晚年擇取筆記作為總結,愈見平淡精神的延續。
(三)王安石鐘山詩歌的老境
相對于歐陽修致仕后的短暫光陰,王安石致仕后隱居鐘山十年,潛沉探索,鍛煉出了老成精妙的“王荊公體”。王安石欣賞張籍的詩歌“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題張司業詩》)。他的詩從詠史翻案到寫景遣興,從諸體兼備到精煉絕句,將前期深折透辟的詩風轉化成深婉不迫,也是一個將詩歌藝術和學養智力的發揮提升到達至“渾漫與”狀態的過程,其致仕后“精進”的藝術*古人多有論及,如《漫叟詩話》云:“荊公定林后詩,精深華妙。”《石林詩話》云:“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造詞用字,間不容發。”,正是老成境界的體現。
王安石晚年詩,尤其是山水詩,雖近于唐音面目,卻是以宋人思維將唐韻了無痕跡地化為己用,包裹宋調的精思,追求藝術的化境,呈現出深厚的人生、藝術積淀的老美。王安石在宋調老成境界方向上的追求,上承梅堯臣,下啟黃庭堅,造語平淡的詩歌不讓梅、黃。自熙寧九年提早開始致仕生涯后,面對宦海的沉浮、愛子的去世、門人的疏離,參禪學佛、登臨山水、吟詠詩句是王安石獲得超脫的多種途徑。他拜相時存念“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比生”;致仕后心態是執著與自適并存,矛盾與超脫交替,使他寧靜澹泊的詩歌有著更豐厚的內涵。像《北陂杏花》“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陳衍《宋詩精華錄》以為“恰是自己身份”;其他如《杖藜》、《獨山梅花》等,吳之振指出“遣情世外,其悲壯即寓于閑淡之中”(《宋詩鈔·臨川詩鈔序》)。以其抱負,致仕后的王安石不能徹底忘懷世事;以其胸懷,他的自遣具有深度,他隱曲的心志使面目平澹的詩句有老成的氣度。像他的翻案詩,前期詠史生新警策,晚期如《梅花》一詩化南朝蘇子卿《梅花落》,了無痕跡,無論是學養技法上還是心態境界上都堪稱老到。
王安石寫得精致流轉的絕句,則不僅僅是字面意義上的絢爛至極歸于平淡的老成,而是“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化工。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描繪王安石致仕后的生活:“蓄一驢,每食罷,必一日至鐘山,縱步山間,倦則定林而臥,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為常。”流連佛寺、注疏《楞嚴經》是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恬淡超脫的心境使他那些色彩明麗、情景交融的詩句能狀態傳神,又有“遠而不盡、近而不浮”的韻味,如“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南浦》),“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書湖陰先生壁》之一),“濃綠扶疏云對起,醉紅撩亂雪爭開”(《池上看金沙花》),對風物明凈可喜的傳寫老到,心境的老成高遠也蘊含其中。沉潛歸隱的修養、專心詩藝的鍛煉使他的詩將早期的斧鑿痕跡一并抹去,筆力傳神老邁,如對仗“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云”(《題齊安壁》),用字“青山無數逐人來”(《若耶溪歸興》),狀物“換得千顰為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雪干》),篇章“江北秋陰一半開,晚云含雨卻低回。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江上》),皆清新天然又非精深功力不到。
致仕后沉潛歸隱,正是宋人老成文化心理在生活方式上的表現;以豐厚的閱歷學養為基礎,將復雜的心志加以提純,更造藝術的老境,則是“王荊公體”給予宋詩的重要啟示。
綜上所述,北宋進一步完善的致仕制度給士大夫晚年提供了優裕的生活保障。致仕觀念的變化、崇老的文化氛圍,使他們的創作呈現獨特的面貌。熙豐時期致仕名臣追求理趣、歸于平淡以及崇尚老美的創作,無疑是考察北宋文學思想發展不可忽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