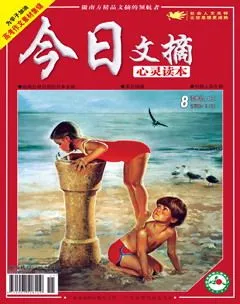老太爺的故事
老家打來電話的時候,正和4歲的兒子嬉鬧。停止游戲,告訴他:“你太爺爺去世了……”小小人兒未必懂得什么是“去世”或是“死了”,不過他倒是若有所思地安靜了一會兒。作為孫媳婦的我,該尊稱一聲“爺爺”的老人,其實,說來,我真的不算熟識。13年里,我只見過老人幾面而已。
第一次見到老公的爺爺,是我的婚禮上。熱鬧而嘈雜的酒宴上,老太爺被從姑姑家接來,坐在主桌上首,接受大家敬酒,聽大同小異的喜慶話兒,和認識的不認識的眾多親戚分別合影,然后,散席,再被送回姑姑家去。那時,這位老太爺已經年過八十,他需要別人在耳邊屢次大聲提醒,才能偶爾認出我老公是他的孫子。席間只要有人到跟前,他就舉起酒杯,笑,抿一口酒,放下酒杯,發呆。無論來人說什么,他都微笑、點頭、嗯嗯有聲、繼續發呆——我那時覺得,他就像一尊家傳的佛像,逢年過節重大時刻被大家捧出來,眾人熱熱鬧鬧供奉一番,然后放回庫房收藏起來。
做了新媳婦,自有姑姑婆婆閑聊拉呱,從七八張嘴里慢慢得知老太爺的好些八卦。他們還有個一致的地方,就是對這位親生父親淡漠的感情。所有提及老太爺的談話,都離不開他年輕時的荒唐,他揮霍,在外玩女人、回家打老婆,徹底窮了以后倒是老實了,可是對家庭始終沒有責任感。
大約一年后,他被送到老人福利院長住。再后來,我生了兒子,他在名義上成為一個四世同堂的老人——這時他仍然住在福利院,兩兒兩女都在本地,不定時地去看看他。
兒子1歲半的時候,老公的兄弟結婚,我們回老家。老太爺又像一尊佛像一樣出現在喜宴上,不過這次他徹底昏聵,所有的親戚都不認得,也沒有人來向他敬酒了,他只在合影的時候被擺在正中間而已。他倒是從頭到尾保持微笑,只是那種笑是你一看就知道他的腦袋里其實啥也不知道的表情。還有,這一次,“佛像”是酒宴開始前一個小時匆匆從福利院里被搬到酒店,散席后馬上送回福利院。這場婚禮后的幾天里,我們去福利院看他。他單獨住在福利院主樓旁一間單獨的小房子里,據說是他自己固執地要住在這間孤零零、看起來好像傳達室的房子里的。
大約10平方米的房間里,一股濃重的“老人味”。床前一只塑料桶里一層顏色可疑的液體,桌子上的牙杯里沒有牙刷,倒是插著奇數的筷子,一看,還發霉了!我想洗洗那些黑色、滑膩的毛巾和抹布,可是才下水搓幾搓,就像草紙一樣,破,進而碎掉。只好扔了,和老公重新去買新的牙刷毛巾抹布襪子枕頭。5月的天氣,他穿著幾件厚毛衣,坐在窗子前面,面前一臺13英寸黑白電視里噪音一片、鬼影重重,完全看不出在演什么節目,而他就那么一直盯著看。老公和兄弟一塊動手把他連藤椅一起搬到屋前空地上曬曬太陽,他的眼神才隨著我滿地亂蹦的兒子活泛起來,還笑了——這之前,我不厚道地以為他已經徹底癡呆了呢。
那天,我看到,他的床頭放著一片形狀奇怪,還有污跡,明顯是撿來的泡沫塑料,那上面,貼著我兒子幾個月大時的照片。照片里肉乎乎的小娃娃干凈漂亮,黑漆漆的大眼睛,甜甜地笑。再后來,他的其他孫子和外孫陸續結婚,他是一個看起來頗龐大的家族、四世同堂的老太爺,一個人住在福利院里的老太爺。
這些年,回老公的老家,我們都去看看他,可是每次時間都不長,不過是給他換些新的日常用品,把他搬出來曬曬太陽,讓我們的兒子去親親抱抱他,和他照個相,這些好像也是我們僅能做得了。關于他的安置,因為龐大家庭的復雜關系,上頭還有長輩,我們并不能決定什么。這個春節回老公的老家,是我最后一次見到老太爺。
春節期間,在親戚們家輪流吃吃喝喝的間隙,找了個下午,去看他。去之前就聽說,他其實已在彌留,幾個兒女每月輪流出1700元錢請護工看著他。幾個月前他就只能躺著了,近10天前他就大部分時間是昏睡著的了,幾天前他半夜醒來大嚷大叫著說胡話,說的都是已經去世多年的親人:他的父母,他去世幾十年的妹妹……
他閉著眼睛陷在一堆被褥里面——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差點以為老太爺已經“過去”了。他早就認不出任何人了,喉嚨里嗯嗯呀呀地說了幾句“話”,也沒一個人聽得懂。他的床前,兒子媳婦孫子孫媳曾孫子們圍了一圈,他的女兒女婿們都在這座城市,他還有好些孫子外孫……他快要90歲了。
這個冬天,老家的氣溫零下幾度到零上幾度,下了幾場雪。老太爺躺在福利院那間屋子里,陷在那堆被褥里面熬過了這個冬天。4月了,氣溫回升,太陽露臉的日子漸漸多了。他在所有人的預期中,走了,享年89歲。
相冊里有一張他們家四代男人的合影,從老太爺到他的兒子們、他的孫子們、他的曾孫子們,遺傳的巨大威力一覽無余。現在,老爺子去世了,我想我不會向我兒子詳述一脈相承的五官后面那部分分裂破碎的家族記憶。
(范譽明薦自《三聯生活周刊》)
責編:小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