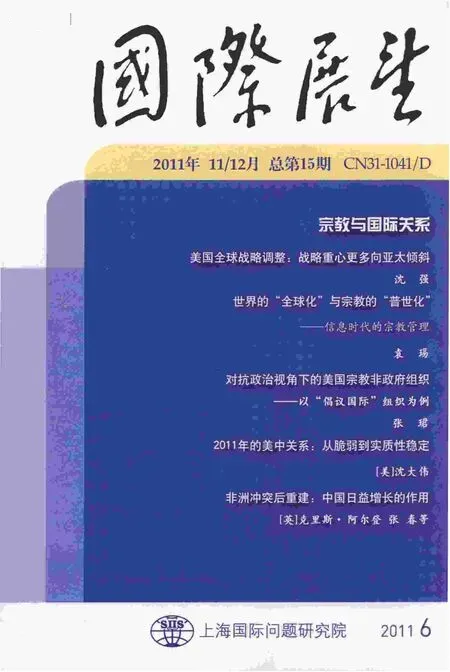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挑戰與展望
王 沖
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挑戰與展望
王 沖
奧巴馬政府上臺后,通過政策宣示和實際操作逐漸形成了一套綜合而務實的“阿富巴”戰略。然而,“阿富巴”戰略的推行不會一帆風順。一方面,它會受到來自國家行為體和地區國際體系層次的制衡。另一方面,它還面臨著來自非國家行為體和社會層次的反擊。從前者來看,“阿富巴”特殊的地緣戰略位置決定著美國會面臨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權力對抗,尤其體現在阿富汗運輸通道的爭奪上。從后者來看,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等極端勢力將給“阿富巴”戰略的推行帶來持久的威脅,這與“阿富巴”邊境地區尤其是巴基斯坦西北普什圖部落區的社會形態有著密切聯系。由于面臨復雜的周邊環境和對手的極力反擊,“阿富巴”戰略的實施效果并不顯著。退出戰略的執行并不意味著美國真正放棄既定的戰略目標,也攸關“阿富巴”戰略的最終成敗。
奧巴馬 “阿富巴” 塔利班 普什圖人
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為了順應國際反恐形勢的變化和基于對外戰略轉變的需要適時推出了針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問題的一套綜合戰略——“阿富巴”戰略(the “Afpak” strategy)。隨著阿、巴兩國的形勢變化,“阿富巴”戰略的基本內涵呈現出動態性和一致性,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進中已經進入退出戰略階段。本文主要研究“阿富巴”戰略自推出以來所面臨的挑戰,并嘗試對這一戰略的實施效果進行評估和展望。
一、既有研究文獻評述
關于“阿富巴”戰略面臨的挑戰,國內方面的研究相對不足。高新濤的論文《奧巴馬“阿富巴”新戰略及其面臨的挑戰》對于新戰略的實施所面臨的挑戰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文章主要探討了阿巴邊境部落區、周邊大國、基層政權等因素對新戰略實施的制約作用。①高新濤:“奧巴馬‘阿富巴’新戰略及其面臨的挑戰”,《和平與發展》,2009年第 5期,第51—53頁。王世達在《大選后的阿富汗局勢走向》的論文中指出,由于“塔利班反彈強勁,加之背靠巴阿境內普什圖部落區以及外來匯款和毒品經濟滋養,尚能控制相當廣泛的農村地區”,②王世達:“大選后的阿富汗局勢走向”,《和平與發展》,2009年第5期,第28頁。因此美國的阿富汗戰爭將陷入僵局。趙華勝在《評美國新阿富汗戰略》中分析了奧巴馬政府新戰略的目標和途徑,指出新戰略也有諸多不確定因素和弱點,如阿富汗政府的能力和作為、與塔利班對話的可行性、改善經濟的困難等。③參見趙華勝:“評美國新阿富汗戰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第1-9頁。
總體來說,國外在“阿富巴”戰略困境方面的研究要比國內更加深入和充實。艾薩克·開法爾認為,美國對“阿富巴”的政策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他著重分析了來自巴基斯坦方面的挑戰,指出“根本問題在于巴基斯坦的國家形態”。④Isaac Kfir, “A Review of AfPak and the Ongoing Challenge of Pakistan,” PSRU Brief Number 51, Dec. 10, 2009, p. 4.邁克爾·斯韋因的《中國和“阿富巴”問題》分析了“阿富巴”問題上中國的利益、動機、特定政策、現實和潛在的影響以及未來的定位和行為選擇,認為“根深蒂固的戰略利益、長期的歷史情結和強烈的不確定性將主導中國對‘阿富巴’問題的處理”。⑤Michael D. Swaine, “China and the ‘AfPak’ Issu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1,Winter 2009, p. 12.馬修·赫爾伯特也認為在美國的阿富汗戰略實施中,地區化的動力將是決定性的但也是非常復雜的,①Matthew Hulbert, “Last Throw of the Dice? U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CSS Analyses in Security Policy,No. 51, Mar. 2009, p.這就涉及俄羅斯、伊朗、中國和印度等在該地區的博弈。阿也沙·汗在《概念化“阿富巴”:前景及險境》中指出奧巴馬政府應努力避免“阿富巴”邊境地區的由普什圖族群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結合所造成的難以控制的暴亂。“阿富巴”戰略是一項“進行中的工作”,需要奧巴馬政府不斷地予以審視和修正。②Ayesha R. Khan, “Conceptualizing AfPak: the Prospects and Perils,”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Research/Asia/0110pp_khan.pdf.③ Debidatta Aurobinda Mahapatra , “The AfPak Strateg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3, 2009, p. 1003.印度孟買大學的馬哈帕特拉的《“阿富巴”戰略及其實施》一文從印度的視角分析新戰略,認為由于“阿富巴”問題本身的多重復雜性和地區政治的各參與方利益的沖突性,新戰略目標的實現并非易事。③由加拿大北—南研究所(The North-South Institute)和德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共同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阿富巴”戰略的地區化途徑具有重要的意義,體現出對地區各方動力的不斷重視。“如果不關注這些地區動力,國際社會和國家行為體就很難改善阿富汗的安全和發展,也難以解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的恐怖分子安全港的問題。”④Krista Nerland, “A New Approach to Afghanistan/Pakistan?” Round Table and Public Panel Report, Jun. 3, 2009, p. 3; John Prados, “The AfPak Paradox,” Apr. 1, 2009,http://www.fpif.org/articles/the_afpak_paradox.約翰·普拉多斯指出美國在“阿富巴”的悖論在于“美國大量的軍事義務和進出阿富汗的運輸能力的限制都將使得任何撤退困難重重”。阿賈伊·帕拉斯拉姆認為,“阿富巴”問題本質上是反政府武裝斗爭的問題,基于印度的視角,談判和和平是不可能的。⑤Ajay Parasram, “Call in the Neighbours: Indian Views on Regionalizing Afghanistan Strategies,” Asia Pacific Bulletin, May 14, 2009.
上述文獻對于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面臨的挑戰或者阻礙的問題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這為本文所開展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啟發作用。在實際推行中,“阿富巴”戰略面臨著諸多挑戰,厘清這些復雜的挑戰因素的關系需要尋找一個合適的視角和框架。本文將參考借鑒上述文獻分析,從國際關系不同行為體的挑戰這一視角進行分析,并將努力實現地區國際體系層次和社會層次兩個分析層次的結合。
二、來自國家行為體與地區國際體系層次的制衡
(一)關于國家行為體的理論
一般而言,國際行為主體可以劃分為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主權國家雖不是國際舞臺上唯一的行為主體,但卻是國際政治中最主要的行為主體,這是國際關系學科研究最基本的對象和邏輯起點。本文主要借助現實主義關于國家行為體和國際體系的理論來分析美國“阿富巴”戰略所遇到的挑戰。
現實主義關于國家行為體的基本論點包括:理性國家論、單一國家論、國家中心論和權力政治論。現實主義認為,主權國家是一個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為體。國家根據所確定的利益行事,追求利益最大化。國家作為一個統一體,具有整體的利益需求,而不考慮其內部社會結構、利益團體等因素。現實主義堅持國家中心論,認為國家是國際社會中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行為主體。現實主義主張權力政治論,突出權力因素的重要性,強調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中,斗爭與沖突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是不可避免的,“國際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①閻學通、閻梁:《國際關系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09頁。現實主義國際體系結構包括兩個層面:體系內的單元層次和體系本身的結構層次。體系的單元是指國家行為體,主要是大國;體系的結構是由體系內自助的單元相互作用形成的,它取決于無政府狀態下實力在各個國家分配的結果。體系的結構決定了體系的性質,體系的結構層次決定了系統的單元層次的行為。地區國際體系也可以稱之為區域性國際體系,是全球國際體系在地區層面上的反映。同全球國際體系一樣,地區國際體系結構也受制于地區內主要大國間的實力分配,而無政府狀態的排列原則對于世界大部分地區國際體系結構的決定作用都是恒定的。地區國際體系結構的無政府狀態的本質決定“國家被迫采取自保或自我加強的外交政策,致力于追求自身安全最大化”,①許嘉等著:《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時事出版社,2008年,第357頁。因此地區內各國尤其是主要大國間的關系往往是充滿權力角逐和沖突的。
(二)“阿富巴”戰略與地區國際體系中的大國權力博弈
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的一個基本內涵在于對地區合作的期盼和規劃上。事實上,這是一個很明智的戰略選擇,因為“阿富巴”問題已經給周邊國家帶來了現實或潛在的威脅,所以地區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阿富汗周邊主要國家圍繞阿富汗的安全與重建問題的溝通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但是根據現實主義關于國家行為體的基本觀點,“阿富巴”戰略仍然面臨著大國權力之爭的深刻挑戰,這種挑戰來自于在該地區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利益的俄羅斯、中國、印度、伊朗及中亞國家。從根本上說,“阿富巴”戰略設想的地區合作的實現與否最終還是取決于俄羅斯和中國的態度及戰略選擇,因為美國與俄、中兩國權力關系的對稱性相對更高。其他挑戰因素如美國、巴基斯坦、印度的三邊關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關系,美國和伊朗的關系等居于次要地位,難以對“阿富巴”戰略的推行造成根本挑戰。“阿富巴”所在的中、南亞地區的國際體系并不是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國際體系,而是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其變化發展的邏輯受制于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和影響,這一點在“9·11”事件后表現得更加突出。因此,這里主要分析在地區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下,美、俄、中三大國在該地區的權力博弈及其對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的推行帶來的不利影響。
冷戰結束后,美國憑借其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綜合優勢,加緊對中、南亞地區的滲透,美、俄角逐日趨激烈。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為美國進入中、南亞地區提供了良好的契機,阿富汗反恐戰爭使得美國在中亞地區獲得了軍事基地,這也是美國軍事力量首次駐扎中亞地區。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的開始階段沒有弱化軍事手段,反而一再增兵阿富汗,雖然這是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安全形勢急劇惡化決定的,但是其深層的地緣戰略意圖不言自明。雖然2009年12月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首次提到開始撤兵的時間,但奧巴馬的撤兵只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戰略性的。美國在阿富汗有著長期和綜合的利益關切,保留一定的長期軍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從地緣政治上看,阿富汗是美國進入中亞地區的戰略支點和前哨,美國的戰略考量就是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遏制中國的崛起勢頭、包抄伊朗的戰略后方、爭奪中亞能源主導權,“在該地區重新構筑一個有利于自己的地緣政治版圖”。①文天堯:《中東黑血:中東的戰爭與和平》,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246頁。因此,作為在中、南亞地區最重要的利益攸關方,俄羅斯、中國對美國一度大舉增兵阿富汗不能不抱有極大的擔心和懷疑。
美國與俄、中兩國在中、南亞地區的權力博弈緊緊圍繞著地理意義上的運輸通道而展開,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的實施就面臨著來自俄羅斯、中國對美國在阿富汗運輸通道的牽制上,這是大國權力博弈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美國和駐阿聯軍運送兵員和各種物資的通道主要有南方的巴基斯坦和北方的中亞地區兩條運輸線。從巴基斯坦經由開伯爾山口到阿富汗的陸上運輸線甚至能為在阿富汗的北約和美國軍隊提供 80%的物資,②“Obama’s War,”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opinions/outlook/interactives/af pak/afpak.pdf?sid=ST2009021500356.然而這條線頻頻遭到塔利班等武裝組織的襲擾。在北方運輸線問題上,美、俄圍繞吉爾吉斯斯坦的馬納斯空軍基地一直明爭暗斗,而該基地也是美軍在中亞地區剩下的唯一軍事基地。考慮到南方運輸線的安全隱患,奧巴馬“阿富巴”戰略中對阿富汗的軍事和民事物資援助尤其離不開馬納斯空軍基地的繼續使用。對于馬納斯基地的重要性,時任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彼得雷烏斯曾表示:“該基地是確保阿富汗乃至整個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美國沒有任何改變該基地地位的計劃。”①王德祿:“美國希望借力中亞諸國解決阿富汗問題”,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5/8707616.html。但是中亞地區作為俄羅斯的戰略后方和傳統勢力范圍,俄羅斯始終將美國的軍事存在視作對其的威脅。2009年,俄羅斯通過20億美元低息貸款和1.5億美元援助的承諾獲得吉爾吉斯斯坦關閉馬納斯空軍基地的回應,但俄羅斯承諾給吉爾吉斯斯坦的 20億貸款一直沒有到位。隨后,美國通過將馬納斯空軍基地租金提高至每年6000萬美元的方法促使吉爾吉斯斯坦“背叛”了俄羅斯,雙方得以達成協議保留了基地,并把名稱改為美國馬納斯國際過境轉運中心。2010年4月,吉爾吉斯斯坦爆發政變,受到俄羅斯支持的反對派上臺后一度宣稱要關閉馬納斯基地。此外,俄羅斯也打算擴建距馬納斯基地不遠的坎特基地,并有意在吉國南部的費爾干納谷地建立新基地。與此相對應的是,2011年4月28日,五角大樓宣布將在塔吉克斯坦境內建立一座全新的軍事基地,用以為反恐軍事以及人道主義援助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奧巴馬宣布“三步走”撤兵計劃后的7月3日,美國馬納斯轉運中心負責人詹姆斯·雅各布森宣稱,中心駐扎的美軍將逐漸減少,但永遠不會關閉。這表明美國仍會繼續保留在馬納斯基地的軍事存在以維持對周邊國家的威懾力,美俄之爭也難以休止。以馬納斯為代表的軍用基地之爭實質上是美俄圍繞亞歐大陸心臟地帶的權力博弈的縮影,這場權力博弈直接制約著奧巴馬“阿富巴”戰略的順利實施。
如果比較俄羅斯和中國同美國在中、南亞地區的權力博弈不難發現,俄美博弈主要是為了爭奪對這一地區的主導權,削弱對方以維護自身利益和追求權力的最大化。而中美博弈相較于俄美博弈的烈度要輕許多,這與中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的廣度和深度不足有關系。中國應對“阿富巴”問題的主要目的還在于維護中國西部邊疆安全,國家安全乃是中國最緊要的考慮。基于維護西部邊疆安全和防范美國對中國遏制的目的,中國對于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的支持只會停留在道義上的支持和有限的非軍事性援助上。中國“不希望‘阿富巴’的形勢成為美國在中國的‘后院’維持長期和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存在的根據”。①Michael D. Swaine, “China and the ‘AfPak’ Issue,” p. 4.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美國和北約為打開通往阿富汗的新運輸線曾多次要求中國開放聯結中國和阿富汗邊界的狹長的瓦罕走廊,這使得中美圍繞是否開放瓦罕走廊的爭論浮上臺面。奧巴馬首次到訪中國的時候也提出了開放瓦罕走廊的問題,但是中國并沒有給予積極回應。因此,美國和北約期盼的東方運輸線的開辟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在補給通道問題上,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也將因此面臨推行不暢的困境。針對中國在中、南亞地區不斷上升的自信,美國有文章提出美國在“阿富巴”應有一個切實的B計劃,即“排擠中國、引入印度和平息土耳其”。②Tony Corn, “The Real Plan B in AfPak,” Small Wars Journal, Feb. 5, 2011, p. 1.
俄、中對中亞地區事務的支配主要是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實現的。2011年6月的上合組織阿斯塔納峰會將阿富汗問題列為重要的議題,并發表宣言強調“上合組織支持將阿富汗建設成為獨立、中立、和平、繁榮的國家”,③《上海合作組織十周年阿斯塔納宣言》,http://www.sectsco.org/CN/show.asp?id=450。而獨立和中立的阿富汗對俄、中來說至關重要。從長遠來看,俄羅斯和中國在中、南亞地區得天獨厚的地緣戰略優勢將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行動帶來深刻影響,這種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美國在中亞的利益是“反恐、能源安全和民主化”,而這些利益遠遠超出了其“實現目標的能力”,④帕格拉·卡納著,趙廣成、林民旺譯:《第二世界:大國時代的全球新秩序》,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23頁。也受制于其他大國權力的侵蝕。隨著大國權力博弈態勢的演變,美國針對該地區的戰略規劃和推行都會面臨難以避免的挑戰和障礙。
總之,從國家行為體方面來看,“阿富巴”戰略要受制于大國權力的平衡,大國權力博弈主要就是在中、南亞地區美、俄、中三大國圍繞權力、安全和利益而展開的沖突與合作。沖突與合作是國家間關系的基本內容,奧巴馬政府尋求在“阿富巴”問題上的地區合作,在實際操作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然而,合作只是一個方面,沖突難以避免,權力政治因素對于國家間關系的良性發展依然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尤其是對于大國關系。這一點在中、南亞地區體現的分外明顯,在這個地區,美、俄、中三大地緣政治棋局的操控者之間的權力博弈會持續進行,美國在這個地區政治、軍事和經濟影響力的不斷上升必然會造成中俄兩國的不安和抵制。以上海合作組織為框架,中俄展開的各層面合作其實也是為了應對作為區域外強權的美國力量進入所帶來的挑戰。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的地緣政治野心具有極大的隱蔽性,但并不能逃避大國權力爭奪的怪圈,它的推行將會受到權力因素和地緣因素的雙重挑戰。“阿富巴”戰略受到大國權力制衡,這是地區國際體系結構的必然產物,也是全球國際體系結構下三大國爭奪領導地位和擴大影響力的反映。
三、來自非國家行為體與社會層次的回應
(一)關于非國家行為體的認識
國際關系研究傳統范式以國家為中心,但這種研究范式正在發生轉變。所謂“范式的轉變,就是強調從由國家構成的范式向由多種行為體構成的范式轉變”。①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2頁。隨著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不斷推進,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治正逐漸走向多種行為體共同參與的“世界”政治。關于非國家行為體的認識,學術界有很多爭論。本文認為凡是能夠獨立參與國際事務并發揮影響和作用的非國家行為體都屬于國際關系行為體的范疇。在世界政治事務中,非國家行為體大量涌現及其地位和作用的上升極大地沖擊著民族國家的主權屬性和現有的國際秩序。詹姆斯·羅斯諾提出“分合論”(fragmegration),①倪世雄等主編:《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11頁。描述全球化時代的一體化過程和分散化過程,國際關系深嵌于由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所構成的世界中。卡倫·明斯特認為國家面臨著來自“全球化進程、以宗教和意識形態為基礎的跨國運動以及種族—民族運動的多種挑戰”,②卡倫·明斯特著,潘忠歧譯:《國際關系精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8頁。后兩者都侵蝕著國家認同并尋求超越國家之上的個人忠誠和歸屬感。對于像跨國恐怖主義這樣的非國家行為體的危害,奈作過比較,“國家間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一般來說,比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非國家行為體戰爭中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更容易為人所容忍”。③約瑟夫·奈注,張小明譯:《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6頁。從國際關系現實來看,奈的這種比較或許并不為過。
(二)“阿富巴”戰略面臨極端主義和部落社會的挑戰
從非國家行為體方面來看,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的推行還面臨著更復雜的挑戰,這個挑戰來自于以普什圖部落社會為生存環境的各種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部族主義勢力。
“阿富巴”邊境的部落區尤其是巴基斯坦一側的部落區是塔利班、“基地”組織以及各種極端主義的“淵藪”。塔利班政權垮臺后,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殘余勢力化整為零退避到阿富汗東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部落區中。由于普什圖部落區與塔利班的天然聯系以及塔利班采取了既拉又壓的手段,塔利班在巴基斯坦西北邊境逐漸穩住陣腳并重新恢復發展起來。塔利班與當地部落的結合使其影響力擴大并由此衍生出各種形形色色的部落形態的塔利班武裝,其中尤以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Tehrik-e-Taliban Pakistan)為著明,外界將這一過程稱之為“塔利班化”(Talibanization),①“塔利班化”導致“阿富巴”邊境地區幾乎形成了一個隱形的“塔利班斯坦”。因此,“阿富巴”戰略面臨的來自于這些非國家或跨國家行為體的挑戰恰恰就是這一戰略所面臨的部落問題的挑戰。以塔利班為代表的極端主義能夠在“阿富巴”邊境扎根是與普什圖部落特殊的社會形態緊密相關的。
普什圖人種族成分比較混雜,長期以來保持著氏族部落的社會結構,被認為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部落群體,②史蒂芬·坦納著,張遠航譯:《父子統帥:布什們的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的南部和東部地區。長期以來,這片區域幾乎都是處于無政府狀態中,正如羅伯特·卡普蘭所描繪的那樣,“政治地圖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取而代之的是武裝民兵,他們不僅控制著本國領土,還滲透到鄰國,很少顧及或根本不顧及地圖上已確立的合法邊界”。③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著:《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163頁。以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區為活動基地的塔利班等恐怖主義頻頻越界到阿富汗境內展開恐怖襲擊,而且在巴基斯坦境內甚至整個中、南亞地區制造大量恐怖活動。
巴基斯坦西北普什圖部落區主要包括“聯邦直轄部落區”以及西北邊境省④2010年3月31日,巴基斯坦憲法修改委員會簽署法案,將“西北邊境省”正式更名為“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和俾路支省的普什圖部落。而在該地區活動的各種恐怖極端勢力雖然有不少來自中東、中亞和高加索等地區的外國伊斯蘭極端分子,但是塔利班分子主要還是普什圖人,甚至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裝直接是由當地普什圖部落武裝構成的。由于同一族屬的認同感,塔利班更容易獲得一部分部落民眾的支持從而得以扎根于部落區。從自然因素來看,這一地區地形復雜,多高山深谷,氣候環境惡劣,交通非常不便,現代化高科技戰爭手段在這里難以發揮有效作用。而且部落區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三國交界處,偏于巴基斯坦一隅,屬于復雜的三角地帶。又由于該地區和阿富汗一側的部落區接壤,因此易于成為塔利班等極端分子跨境行動的天然庇護所。從社會形態上看,巴基斯坦的“聯邦直轄部落區”儼然是一個“國中之國”,沒有現代政治體制比如議會、行政和司法機構,中央政府權力幾乎未滲入到該地區,“巴基斯坦國民議會通過的法律也不適用于部落區”。①Parker H. Wright, “Pakistan’s Tribal Lands: Central Front in the War Against the Global Islamist Insurgency”, A Research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Apr. 2009, p. 4.從民族特性來看,部落區的普什圖人驍勇善戰,民風強悍,男人被譽為“天生的戰士”。普什圖人不畏強權,歷史上屢屢挫敗外來強敵的入侵。部落區的普什圖人信奉傳統的部落習慣法——“普什圖瓦里”(Pushtunwali),其核心內容包括“榮譽”、“復仇”和“好客”,而“捍衛榮譽的主要方法是仇殺”。②弗雷德里克·巴特著,黃建生譯:《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過程:一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范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0頁。作為不成文的部落行為守則、傳統和習慣,數世紀來它的強制性并沒有發生變化,普什圖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一直深受其影響。此外,在普什圖部落區還廣泛分布著眾多的阿富汗難民營,這也是部落區復雜的社會生態的重要反映。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資料,在巴基斯坦有大約170萬登記在冊的難民,幾乎都是來自阿富汗的難民。③UNHCR, “UNHCR Global Appeal 2010-2011,” Dec. 1, 2009, p. 19.而巴基斯坦大部分難民營都分布于與阿富汗交界的西北普什圖部落區,這與阿富汗難民的普什圖人身份有根本關系。大量阿富汗難民滯留在巴阿邊境地區尤其是巴西北部落區,這“不但有可能使難民營成為恐怖分子的藏身之所,也可能成為恐怖分子招募新成員的‘大后方’”。④朱永彪、閆培記:“阿富汗難民:歷史、現狀及影響”,《世界歷史》,2009年第4期,第93頁。遍布于部落區的宗教學校和清真寺對政治伊斯蘭主義思潮在部落地區的傳播更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使得傳統部落權力結構受到很大沖擊,毛拉的政治影響力急劇上升,而政治代理人和部落長老的權力受到一定的挑戰。這進一步推動了部落區的政治伊斯蘭化,構成極端勢力能夠扎根部落區的宗教和意識形態基礎。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推斷,僅僅依靠軍事打擊難以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等極端勢力徹底鏟除,原因在于極端勢力與部落社會關系的密不可分。普什圖民族保留了他們的部落機制并非因為無知,根源在于這種機制是“對他們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一種穩定而成功的適應方式”。①弗雷德里克·巴特:《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過程:一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范例》,第193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界的普什圖部落的復雜社會形態決定著以塔利班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力量仍將與美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繼續展開非對稱性戰爭,奧巴馬政府“阿富巴”戰略面臨著活動能力極強、社會基礎比較厚實的非國家行為體力量的持續的嚴峻挑戰。
總之,從非國家行為體方面來看,以極端勢力為代表的跨國家行為體和次國家行為體會給“阿富巴”戰略的推行造成持續不斷的挑戰,雖然這一類非國家行為體與美國相比在實力上具有巨大的懸殊,但其破壞性不可小覷。“阿富巴”戰略的主要目標就是要破壞、瓦解乃至消滅阿巴兩國的“基地”組織及其盟友,由于“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等極端勢力與普什圖部落區的緊密結合,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無疑將更加艱巨。在“阿富巴”邊境部落區活動的非國家行為體所具有的分散化、聯合性、草根性以及部落特質決定了該地區是美國反恐的重心,“阿富巴”戰略的“機會專區”(Opportunity Zones)設想在部落區的推行難以取得成效。
四、評估和展望
比較“阿富巴”戰略面臨的雙重挑戰,大國權力博弈是中、南亞地區特定的國際體系結構導致的結果,也是塑造這一地區國際體系結構的根本動力,非國家行為體力量的凸顯在一定程度上了改變了這一地區國家間關系互動的內容,給地區國際體系帶來重大沖擊,使地區國際體系結構的演變進程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阿富巴”戰略所面臨的挑戰是中、南亞地區國際體系結構變遷的現實表現和必然結果。
自“阿富巴”戰略首次推出后,奧巴馬政府就根據情勢變化通過政策宣示和實際操作兩個層面對這一戰略進行不斷的調整,形成了希拉里所概括的由三個部分組成的戰略:“對‘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反叛分子發動的軍事攻勢;增強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民事運動以削弱反叛活動的影響;以及加強外交努力以結束阿富汗沖突并為該地區規劃一個新的、更加安全的未來”。①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國務卿克林頓闡述美國的阿富汗戰略”,2011年2月18日,引自http://www.america.gov/st/peacesec-chinese/2011/February/20110218184208x0.38870 75.html。2009年12月的奧巴馬西點軍校演講對“阿富巴”戰略進行重大調整,包括2010年夏季之前增派3萬余名美軍士兵進入阿富汗的增兵計劃,同時首次正式提出了明確的撤兵時間,為未來移交責任和安然脫身定下基調。“阿富巴”戰略實施至今,美國及其盟友已先后擊斃多名“基地”組織、塔利班武裝以及其他極端勢力的領導人,盤踞在阿、巴兩國境內的各種極端勢力的活動能力受到極大削弱,其中最為突出的成果莫過于2011年5月1日擊斃“9·11”恐怖襲擊的元兇本·拉登。然而長期以來疲于躲避追殺的拉登更多的是作為“基地”組織和極端勢力的精神領袖而存在,實際的指揮權和操控權已然微弱,因此拉登之死的象征意義要大于實際意義,并不足以使已經本地化的“基地”組織網絡走向瓦解,而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極端勢力也不會一蹶不振。
2011年6月22日,奧巴馬發表《阿富汗在前進》的講話,提出“三步走”撤兵計劃:從2011年7月開始至年底前撤出一萬人;2012年夏季結束前總共撤離3萬3千人;到2014年年底前完成移交進程。撤兵計劃這一退出戰略意味著“阿富巴”戰略的實施進入新的階段,也攸關這一戰略的目標實現,它并不意味著阿、巴兩國在美國外交戰略棋局中的分量下降,而是奧巴馬政府基于國內外形勢變化尤其是美國經濟復蘇困難、國內民眾對折兵傷財的戰爭多有不滿以及總統大選將至等諸多因素考量的。撤兵計劃也得到多數美國民眾的支持。根據2011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支持盡快撤兵的人數從一年前的 40%上升到 56%,而主張維持駐軍直至形勢好轉的人數則從53%下降到39%,①The Pew Research Center, “Record Number Favors Removing U.S. Troops from Afghanistan,” Jun. 22, 2011, p. 1.這也反映出美國民眾對阿富汗戰場形勢好轉的認知在提高,而拉登被擊斃對美國民眾的心理認知無疑起到了催化作用。但是下面一系列相對客觀的統計數據卻從多個側面證明“阿富巴”戰略的推行效果并不令人樂觀。根據由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和美國和平基金會所編制的“失敗國家指數”及排行榜來看(見表1),阿、巴兩國近四年來高居排行榜的前列并無明顯變化。

表1 失敗國家排行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表2則反映出,2010年駐阿美軍死亡人數較前兩年均有較大幅度增加,而2011年上半年的死亡人數幾乎是上一年死亡總和的一半,美軍所面對的阿富汗安全形勢依然嚴峻。此外,根據澳大利亞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發布的2011年“全球和平指數排行榜”,在所有參與評估的153個國家中,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排名分別低至146位和150位,均為“最不和平國家”。①55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1 Methodology , Results & Findings,” Global Peace Index, p. 9上述數據顯示出,“阿富巴”戰略的推行對阿、巴兩國產生的成效并不顯著。在此形勢下,奧巴馬宣布如期執行撤兵計劃無疑是一個冒險的賭注。

表2 駐阿美軍死亡人數 (單位:人)
其實,對于撤兵計劃應該“聽其言,觀其行”。正如伊拉克撤兵計劃一樣,2011年底前美軍可能不會全部撤出伊拉克,而且美國對伊拉克的施壓使得伊各政治勢力達成共識同意美國可保留2萬駐軍訓練部隊,所以阿富汗撤兵計劃也很有可能會如出一轍。奧巴馬也指出,美國將以負責任的方式逐步撤出軍隊,以使阿富汗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國家,并給予美軍繼續在那里行動的能力,以便徹底擊潰“基地”組織網絡,②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奧巴馬總統說美國正成功地達成在阿富汗的目標”,2011年6月30日,引自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1/06/20110630145 615x0.7856671.html#axzz1RZG8XaLj。這就暗含了美國不會全部撤軍的可能性。而與撤兵計劃同時進行的是,美國還在推動阿富汗與其簽訂一系列戰略協議,其中包括美軍在阿富汗建立多個長期軍事基地。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阿富巴”戰略退出階段的開展,直接的軍事打擊和武力清剿將逐漸減少,民事手段和間接的軍事與安全援助將會成為主導手段,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阿富汗戰略的根本問題不在于戰場上的勝敗,美軍可以輕易擊敗對手,但很難取得最終勝利”,“新戰略成功的關鍵還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①肖河、余萬里:“奧巴馬政府的阿富汗新戰略”,王緝思主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0》,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第171頁。只要暴力極端主義在“阿富巴”邊境不被徹底剿滅,美國對阿、巴兩國的支持和援助就會以各種方式和名義繼續進行。由于阿富汗塔利班堅持外國軍隊全部撤出,美軍及其盟友一旦不全部撤出就難以令塔利班真正放棄武力而走向政治和解。在“除暴”的戰略目的之外,“阿富巴”戰略還隱藏著美國意欲主導中、南亞地區事務、與俄、中兩大國爭奪地區影響力和控制力的盤算。遏制俄、中崛起以及阻控二者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機制主導和分配中亞事務是美國政府長期不變的戰略目標。“阿富巴”戰略是奧巴馬政府當前以及未來數十年內美國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環,它緊緊聯結起美國的亞太戰略和中東戰略。肇始于反恐戰爭的阿富汗戰爭已持續十年之久,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阿富汗已從美國期待的戰略楔子變為急欲擺脫的戰略負資產,但即便是戰略負資產也能給美國帶來一定的戰略效益。因此,“阿富巴”戰略不會因為撤兵進程以及未來美國政局的可能變化而發生實質性變更,所不同的只會是這一戰略實施的手段和方式,唯一不變的是要建立和維持美國在中、南亞地區的戰略優勢地位。
The “Afpak” Strategy of Obama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WANG Chong (47)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關系專業博士研究生
Sinc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it has gradually formed a comprehensive and pragmatic “Afpak” strategy by means of policy statement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fpak” strategy will not be smooth. For one thing, it faces the challenges from some countries and the region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lso for another, it faces the counterattack from non-state actors and social le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er, the special geo-strategic location of “Afpak” decides that the U. S.will face the power confrontation from Russia and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competition on the Afghan transport corrido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latter, the Taliban and Al Qaeda and other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will bring long-lasting threa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fpak” strategy,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social patterns of Afpak’s border region, especially Pashtun tribal area in northwest part of Pakistan.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 surrounding environments and the opponents’ strong counterattack, it is rather difficult to achieve good results for the “Afpak” strategy.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it strategy does not mean that the U. S. really gives up its strategic objective established, and it also concerns ultimat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Afpak”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