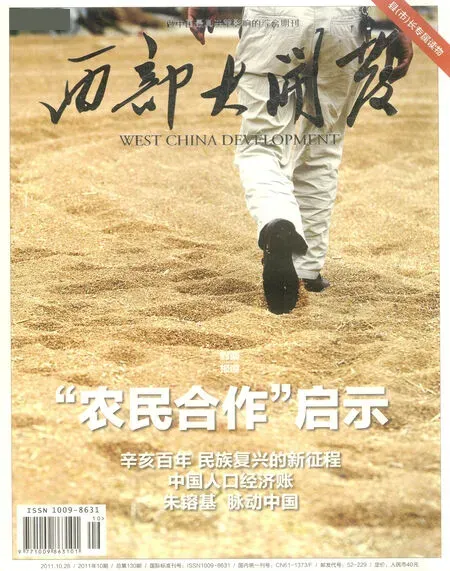重農 小心傷農
當一種思想,
一份對策,
一個道理
被認定為不可置疑的正當時,
在實踐中,
在操作中,
對可能遭遇的問題,
可能發生的變異,
可能造成的對農民的侵害,
尤應保持清醒的頭腦,
保持特別的警覺。
長期以來,我們重視“三農”問題,啟動了廣泛的思路,構思了無數的對策,論證了太多的道理。可是,風雨滄桑幾十年后,明顯地遇到了一個邁不過去的坎:這一歷史性難題究竟緩解了多少?
近些年來,從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對策和道理看,產業化、城市化、知識化是我們努力的重點。然而,現實中的“三農”問題卻更加的突出了。
首先講產業化。產業化可以將分散的小規模農戶有效地組織起來,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順利對接,實現產銷一體化經營,增加農民收入。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常常走偏路子:有的強行在交通要道兩側連片規劃極具觀賞性作物種植;有的不問市場行情是否看好,強行要求農民鏟除青苗,大面積種植經濟作物;有的地方號召縣鄉干部下村領辦農業開發基地,引進工商企業、專業大戶直接進入農業生產領域,反租倒包,一年每畝區區幾百元甚至幾十元,就把土地上擁有承包權的農民輕易打發了。農民不滿,抵制?上訪?無可奈何。到頭來,吞下苦果的自然是農民。
再說城市化。城市化的進程正在全力加速,有些地方政府認為只有轉移農民,減少農民,才能發展農民,富裕農民。然而,好多農民從中品嘗到的都是苦澀與辛酸。如今城市的大門雖逐漸向農民開啟,但是,進城農民至今被排除在城市的體制之外、發展之外、社會保障之外。農民工為了城市的發展貢獻了廉價的勞動,卻沒有享受到平等的權利、平等的身份及其子女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利,有的甚至連他們拼命勞作付出的血汗錢都難討回。還有征地,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城市化強征農地,又無力為失去農地的農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艱難生活在城市的邊緣。
知識化的社會如期而至。教育,是公民應當享受的基本權利,是社會實現公平的重要保障,也是農民朋友改變命運的有限機會。隨著教育話題的不斷升溫,“改革”、“接軌”的呼聲日益高漲,“信息社會”、“知識社會”的預期分外殷切。這一切,也給“三農”問題的解決拓展開了更為深廣的思路。可是,在現實中,我們感受到的卻是更多的憂慮。在“產業化”、“市場化”的進程中,在“教育”被赫然列入“暴利行業”的演變中,農民子女上學的門檻卻一高再高。越來越普遍的普通學校與重點學校的分離,加快了教育投入、優質師資從村莊向鄉鎮、向縣城甚至向省城流動和聚集。而且,普通學校一旦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升格為“重點學校”,巧立名目的上學費用立馬飆升,還會趁勢擴大招生,廣開斂財之路。如何防止因為改革的偏差導致更大的社會不公,導致鄉村義務教育的基礎動搖?這是一個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不可否認,推進產業化、城市化、知識化,可加快“三農”問題的解決。可是,為什么我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往往是跳蚤呢?
其實,問題的癥結很清楚。如果我們堅定“以人為本”、“以農民為本”的發展理念,堅實地“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公正的讓農民“享有充分的發展機會、擁有平等的社會地位”,“三農”問題的解決就會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這里,我們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既有利益結構的調整與再分配是分外艱難的。長期的城鄉分治,向城市傾斜依然在頑強地發揮著作用,城市在城市化過程中,依然堅守著最后的利益。市場經濟賦予資本發展的強勢,帶給資本耀眼的光環。在投資農業的交易中,在房地產經營的擴張中,在教育等公用事業的市場化改革中,我們充分領略了資本的精明和智慧,也一再見識了資本的貪婪和對弱者(農民)的擠壓。
更應警惕一些政府部門不斷滋長的趨利、自肥、賺快錢的現象。單以“城市化”而言,一些地方的領導也有他們的利益驅動:大搞土地財政,為政績增光添彩,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傷民工程,有的通過權力與資本的勾結為自己牟取暴利。
與民爭利,再好的改革也會踩空,再好的政策也會變形。
“重農”小心傷農。當一種思想,一份對策,一個道理被認定為不可置疑的正當時,在實踐中,在操作中,對可能遭遇的問題,可能發生的變異,可能造成的對農民的侵害,尤應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特別的警覺。
本期封面報道《“農民合作”啟示》,旨在積極探索“農民合作”的途徑、得失,同時也為探討解決“三農”問題獻出一種思路,相信閱后會給讀者帶來諸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