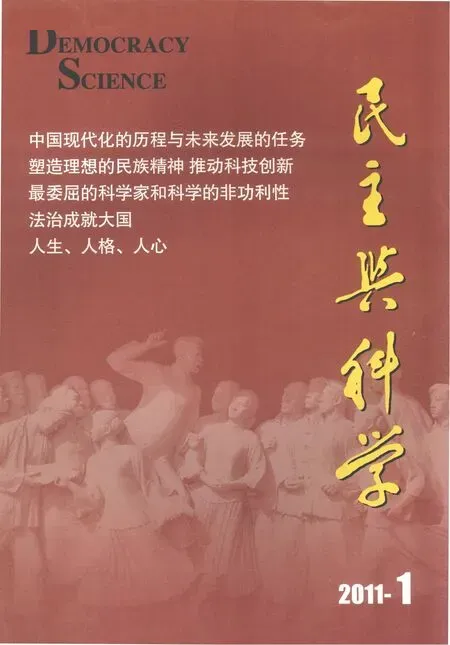塑造理想的民族精神推動科技創新
■田克儉
塑造理想的民族精神推動科技創新
■田克儉
在2010年度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再次空缺,這已是自2000 年以來11 年中該獎項第7 次無人問鼎。令人遺憾之余,我們想到另一個連續61年的空缺———新中國61年了,然而中國人卻從未問鼎過諾貝爾科學獎項。中國在體育競技中成績非凡,奧運會金牌世界第一。而在世界科學的這一最高賽事上,61 年卻沒能實現零的突破。
中國是一個人力資源大國,所以也自然是智力資源的超級大國,因此中國有條件在科學研究上走到世界的前列。有雄厚的智力資源卻少有杰出科學成就和杰出科學家,這種情況既讓人慚愧又讓人困惑。另一個相關的現象是,中國在技術自主創新方面的表現也一直差強人意。
在科學史研究中,人們把“科學技術發達的文明古國——中國,為什么沒能最先進入現代文明”稱之為“李約瑟之謎”。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提出了三個問題:為什么中國能在中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在科技方面領先于歐洲?為什么中國古代和中世紀科學沒有演變成近代科學?為什么近代科學產生于西歐而不是中國?這三個問題的核心實質是,為什么近代中國會在科技方面落后于歐洲?
李約瑟難題所討論的狀況是過去兩千多年中國諸多社會因素的產物,在探討過去的病因。是過去的因導致了今天的果。
但是,如果孕育這個難題的因素依然左右和影響著中國人,興許再過兩千年又會出現張約瑟、王約瑟難題。今天的因就將成為明天的果。如果真是這樣,責任就要追究到我們這代人頭上。不能察覺這一點并辨明其中病因是我們的愚蠢;察覺了、明白了卻聽之任之無所作為則是一種犯罪。我們應該避免孕育李約瑟難題的因素再繼續困擾中國,不讓李約瑟難題千百年后重演。
有人將中國缺乏杰出科學家和杰出科研成果的原因歸于資金、技術、設備、體制等方面。但這并無法解釋為什么海內外中國學者(尤其是大陸學者)的群體式微——在海外發展的學者是根本不受這些因素影響的。由此是否可以做這樣的猜想:李約瑟難題和我們今天的諾貝爾困局都出于同樣的原因,病根都在人的精神層面上。
群體式微,那一定是大家出了什么同樣的問題。什么東西能使一個民族成千上萬的成員形成某種差不多一致的狀況呢?這種東西只能是一種可以同時在千千萬萬民族成員中間潛移默化地相互感應、相互傳染、相互影響的東西,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卻又像遺傳基因一樣能一代一代傳下去的東西——民族精神。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創新主體——科技工作者——的主觀精神方面。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解釋為什么中國學者(無論在國內還是到國外的)全都少有領先世界的上佳表現。其中人們的行為傾向性最值得注意。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較缺乏科學創新的內在動機。內在動機指人們對某些活動感興趣,從活動中得到了滿足,因而活動本身成為人們從事該活動的推動力。相對應,外在動機則是指人們參加某種活動的動力不是基于對此活動本身的興趣,而是由外在的利益驅動或壓力所致。許多卓越科學家都注意到科研內在動機的重要性。而我們多數學者的學問動機僅是黃金屋、千鐘粟、顏如玉。研究表明,外在動機過強還會削弱內在動機。
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精神的、智力的活動,是一種精神的事物。科學精神是貫穿并深藏于科技創新之中的內驅力和靈魂,是人們在科學活動中所具有的意識和態度,是科學工作者所應有的信念、責任感和使命感。而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既有的一些不利行為傾向一直延續到今天,如:過于關注現實得失,奉行功利主義,人生信念比俗化,太重既得利益,玩世不恭等。這些行為傾向反映了一種精神上的缺失,也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最大障礙。
“科學技術是人類智慧的精華,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征”。“崇尚科學技術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為了在科技創新上奮進,我們中國人應該追求一種更理想的民族精神。從科技創新角度探討理想的民族精神,則理想的民族精神應該是一種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以下作用的精神:能夠為它的人民提供一種有責任感的人生哲學,能夠為它的人民提供一種莊嚴的人生態度,能夠為它的人民提供一種神圣的人生理想,能夠為它的人民提供一種樂于探求的科學動機。很遺憾,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中以上東西常有欠缺。
塑造理想的民族精神,一要挖掘傳統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內涵。祭祀文化、家族文化、人生禮儀活動、民間信仰文化、傳統節慶文化等,這些傳統文化形式中或多或少都蘊含著凝聚人心、整合民族精神的作用。
塑造理想的民族精神,二要借鑒其他民族文化中積極的內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塑造一種理想的民族精神是比攻玉艱巨千百倍的任務,其他民族一切積極有效的方法都不妨為我所用。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