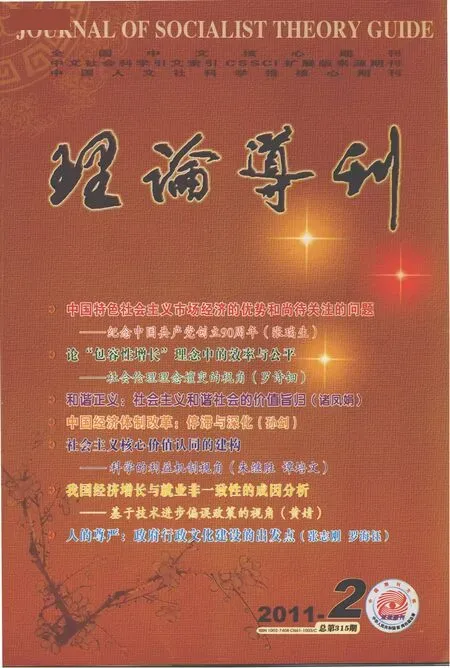村上春樹文學的主題表現及其時代意蘊
張鵬
(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西安710069)
村上春樹文學的主題表現及其時代意蘊
張鵬
(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西安710069)
通過對村上春樹不同時期的多部作品分析發現,村上文學始終背負時代賦予的使命,深刻反映了當下消費時代的愛與憎、善與惡。村上竭盡全力地投身創作,其文學創作的三大主題——“喪失情結”、尋求靈魂救贖和探索產生“暴力”的根源,無一不表現出他對時代的獨特把握和深切感受。也正因為村上春樹文學緊密地體現了時代脈搏,豐富地展現了時代特質,才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贊譽。
村上春樹;文學創作;主題;時代意蘊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說:“不是作家選擇時代,而是時代選擇作家。這就是時代賦予作家的歷史使命。也就是說,作家接受時代賦予他的重任,傾其一生通過作品的主題,參與時代、表現時代。”[1]190盡管不同的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現的主題是作家自身對混沌的現實世界的獨特感知的產物,但是他們在主題表現上肯定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從不同的視角藝術地再現自己所處的時代。從時代與作家的這層關系來看,村上春樹在其作品的主題表現上,也遵循了這條法則。縱觀村上迄今為止發表的作品,他在不同時期作品中的創作主題,都賦予了其獨特的時代意蘊。綜括而言,可分為三大類:通過意識世界與無意識世界的對立構圖,表現了被動地接受現實,貪圖享受生活、具有“喪失情結”的一代;直面混沌的無以寄托的現實世界,主人公試圖通過宗教信仰尋找靈魂自救,進而對日本的現實體制提出尖銳的質疑;對“9·11”暴力事件的反思及其表現。本文將圍繞以上三點,對村上春樹文學的主題表現及其時代意蘊展開剖析。
一、意識世界與無意識世界的構圖
通過意識世界與無意識世界的對立構圖,表現具有“喪失情結”的一代,是村上文學初期作品表現的重要主題。其作品主要包括五部:《且聽風吟》(1979年)、《1973年的彈子球》(1980年)、《尋羊冒險記》(1982年)、《挪威的森林》(1987)、和《舞!舞!舞!》(1988年)。其中,《且聽風吟》是村上的處女作,獲得當年“群像獎”。這部作品和所有作家的處女作一樣,對我們解讀該作家的文學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且聽風吟》描寫的是1970年的夏天,發生在主人公“我”、“鼠”和一個沒有小手指的女孩之間的故事。她是“我”的女友,但倆人的交往沒有結果。“鼠”是“我”經常在酒吧喝酒、聊天的摯友,但倆人之間并未達到真正可以交流的地步。一種感傷的基調,充溢于作品始終。作品中寫道:“有一天,一個彷徨于宇宙的青年潛伏在一個井里。他疲倦于宇宙的浩大,希望悄然地死去。隨著不斷地下沉,他漸漸地覺得在井里有種心情舒暢的感覺,一種奇妙的力量洋溢于他的全身。”“風對他竊竊私語:你可以完全不在乎我,就像對待風那樣。如果你想給我一個稱呼,也可以叫我火星人。絕不會帶來后遺癥什么的,對我而言語言本來就沒有什么意義。”“但是,你仍然在說話。”“是我?說話的是你,我僅僅是給你的心傳達一種信息而已。”對此,日本著名評論家拓植光彥指出:作品中的“‘風’與‘井’”是以二元對立的構圖出現。其中,“風”明顯地借用了弗洛伊德的“id”(=無意識)的語意,暗指精神分析意義上的自我。在井里“隨著不斷地下沉……”一句,表現了青年在無意識世界里感悟到的一種舒適;同時,青年從井里出來后提到的“風”,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榮格心理學中的、由集體無意識發出的聲音。因此,所謂“且聽風吟”,其真正的時代意蘊就是傾聽由現代人的集體無意識發出的心聲。[2]那么,這種集體無意識的聲音究竟是什么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第一次以“人”的聲音向日本國民和全世界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從6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而村上春樹出生于1948年,這就意味這他的成長過程基本上和二戰后日本經濟的復蘇、高速增長期同步。隨著經濟的飛速增長,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豐富,但是,與此同時人們也深感在精神上失去了許多。關于這一情景,在小說的開頭部分,“鼠”在登場前后拋出的兩句臺詞對我們解讀“風吟”的寓意頗有啟發:“只要心情舒暢,管它呢!”;“什么有錢人,統統是王八蛋!”關于這兩句臺詞,日本評論家加藤典洋認為:前者是對世界的肯定,預示著80年代以后的時代氣息;后者是對世界的否定,暗示了70年代以前的時代氣息。即潛在于這部作品的深層寓意是,人們在70年代的擔憂心理,敗北于80年代以后的時代氣息面前,因此,《且聽風吟》的主題向讀者傳達了一種“從否定到肯定的時代氣息。”[3]38加藤典洋的這一觀點無疑是卓見,從作品誕生的年代1979年來看,當時的日本正處于經濟繁榮,國民生活蒸蒸日上的全盛時期,許多人在享受富裕的現實生活的同時,快節奏的現代生活,又使人們深感若有所失,有一種“喪失情結”纏繞著自己的心緒,這就是現實賦予村上文學初期主題的時代意蘊。從《且聽風吟》到《舞、舞、舞》這五部作品,作品的表現主題一以貫之,都在且聽由“風”傳出的時代氣息。
二、直面混沌,尋找靈魂救贖
側耳且聽由“風”傳出的時代氣息進行創作,這僅僅是村上文學初期作品的創作主題。大江健三郎指出:“村上春樹文學的特質是對于社會、或者是個人身邊的生活環境,一律采取被動的接受姿態,即他對于來自世俗的環境影響毫不抵抗,順其自然。經常是在傾聽流行音樂的背景下,編著自己內心的夢幻世界。”[4]229這一見解對我們解讀村上文學頗有啟發,但他僅僅擊準了村上春樹的前期作品的創作方法和主題。從《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1985年)、《奇鳥行狀錄》(1995年)到《地下世界》(1997年)等開始,村上文學的旨趣已經發生變革,開始創作介入現實社會的主題。其中以《地下世界》和其續篇《在約定的場所》的表現尤為突出。這是因為1995年1月,首先在日本神戶地區發生了大地震(后來被稱為阪神大地震)。此次地震造成30萬人無家可歸,6400多人死亡。同年3月,又在東京地鐵發生駭人聽聞的奧姆真理教事件。對此,村上在《地下世界》的后記中寫道:“1995年1月和3月發生的阪神大地震和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是日本戰后劃歷史的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兩大悲劇,即使說日本人的意識狀態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為過的重大事件。(它們)有可能作為一對災難,作為在講述我們的精神史方面無可忽視的大型里程碑而存續下去。”[5]764可見,這兩大事件對村上本人的沖擊之大。不過,對村上而言,他似乎更關注由奧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這也許是從真正意義上促使村上進一步改變對于社會的不介入態度,轉入思考和創作現實事件的意義和時代意蘊的最大契機。這里,筆者以《地下世界》為主闡明這個問題。
《地下世界》是以1995年3月20日發生在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事件為素材,且以敘事者“我”現場采訪的形式,通過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證言”完成的一部寫實作品。具體地說,“我”共采訪了62名這一事件的受害者或目擊者,且以證人從“現在”開始敘述自己的遭遇的形式——“現在”不斷侵入“過去”的敘事手法,將由奧姆真理教集團策劃的那場駭人聽聞的“無差別”大量殺傷人命事件再現于讀者面前。
在很長一段時間,日本的新聞媒體把這場事件的受害者歸于市民社會的“此方”,屬于“正義”;麻原奧姆真理教集團的成員歸于邪教的“彼方”,屬于“邪惡”。由此將雙方以“正義”與“邪惡”的對立圖式,通過電視、新聞媒體展現在日本國民面前。但是,我認為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如果我們認真反思一下,現實世界中為何會釀出奧姆真理教?并加以反省就會發現,奧姆真理教的出現有其潛在的社會背景。就日本而言,進入90年代后,泡沫經濟的崩潰造成許多人失業,進而導致心理恐慌。比如,日本評論家吉田司就指出:不是因為人們覺醒了市民的“正義”,才使“邪惡”教主麻原如此受到關注,而是完全相反。即在高度管理下的“和平與秩序”的市民社會下,人們早已厭倦程式化的日常風景,期待著發生〈破壞世界〉和〈世界破滅〉的那一刻。因為,只有〈破壞世界〉和〈世界破滅〉的瞬間,才能給予人們由非日常的〈解放感〉和〈狂歡〉感帶來的幻覺。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就扮演著這樣的“破壞王”。因此,〈破壞〉扮演著市民在電視上觀看的悲劇;〈破滅〉成了民眾參與〈狂歡〉活動的祭日。阪神大地震使上百萬的民眾參與了救助活動,也是源于同一道理。[6]這就是村上小說《地下世界》的敘事主題。也是村上文學在90年代以后,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文學主題。
在現代社會里,一個新型宗教的出現,肯定有產生這一宗教的社會背景。因為,宗教產生的根源是人們直面現實世界,有各種各樣的解不開的疙瘩。這時,人們就期盼著有一個“上帝”的存在,可以解救自己的苦惱,進而走出現實困境。其實,90年代在西方國家也出現過類似的宗教。村上文學正是借描寫發生在日本的奧姆真理教事件,展開了對現實社會人們生存狀貌的剖析。換句話說,是這個時代賦予了村上文學,直面混沌的現實世界,尋找靈魂自救的創作主題。
三、“9·11”暴力事件的反思及其表現
從《奇鳥行狀錄》等作品開始,村上文學就已表現出對邪惡、暴力及其導致這些產物萌生的體制堅決斗爭的態勢。目擊了2001年在美國發生的“9·11”暴力事件后,村上春樹對現實世界更為關注。在一次采訪中他明確表達了對世界格局的危機感:假如不發生“9·11”事件,世界的發展應該與當下的情勢完全不同……然而,“9·11”暴力事件的發生,結果使世界變成了這個樣子。我們就生活在其中,沒辦法不這樣活著。換句話說,眼下這個實實在在的世界比虛擬世界、假想世界還要缺乏現實性。可以說,我們是活在一個錯誤的世界里,但這對我們的精神有極大意義。[7]
對此,日本評論家川村湊率直地指出:“9·11事件使美國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鮮等國的暴力惡夢,從這一刻開始帶著明確的‘惡意’,作為‘惡魔的存在’,映入美國人的眼簾。他們正是基于這樣的正義心、報復心和恐怖心理,發動了對暴力的‘圣戰’。我認為對這一暴力事件,村上春樹做出了明確的反應,在2009年9月12日出版的《海邊的卡夫卡》中,就有對‘9·11事件’之后的美國的反思。”[8]47這一見解一語道破了作品的創作動機與“9·11”事件的密切關系,對我們解讀作品啟發甚多。那么,《海邊的卡夫卡》中究竟是如何再現這一充滿暴力的現實世界的呢?
《海邊的卡夫卡》的世界可分為兩層。第一層是1944年11月7日,在日本山梨縣的某一山上學生們正在采蘑菇時,突然發生了集體昏睡現象。在這次事件中,后來所有的學生都恢復了健康,而唯有一個名叫吶卡它的學生從此失去了所有記憶,但他卻獲得了能和貓對話的特異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有一天夜晚,長大成人的吶卡它被一只黑色的狗帶到一個叫做喬尼枉卡的家里。此人專門殺貓,其目的有二:一是為了吃掉貓的心臟;二是要用貓的靈魂制造一種特殊的笛子。這時,喬尼枉卡正準備殺掉吶卡它要找的那只貓。吶卡它求他別殺這只貓,喬尼枉卡回答說:除非你殺了我,否則就休想阻止我。無奈之下,吶卡它真的殺了他。在這個故事層面上,可以喚起我們對兩個暴力事件的反思:一是1944年這個特殊的年份,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采蘑菇中發生的集體昏睡事件,讓讀者很容易聯想到美國給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呈蘑菇狀的原子彈。同時,在這一事件后,吶卡它從此失去記憶,也具有深刻的寓意。小森陽一就指出:《海邊的卡夫卡》中發生的“集體昏睡事件,暗示著日本國民想忘卻二戰中留下的慘痛記憶。”[9]86可見,這里既有對戰爭暴力的反省,也有對日本國民性的批判。如果說戰爭暴力似乎遠離我們現實,那么,象喬尼枉卡殘殺自然界的牲靈的暴力事件;人與人之間互相殘殺的暴力事件,卻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事實。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時代。
二是描寫美國當局對“9·11”暴力事件做出的強硬對策。小說中寫到:一個叫做西露克哈特的少年,對攻擊他的名叫烏鴉的少年,帶有充滿嘲笑的口氣回擊道:別得意,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你無論有多大威力,都無法傷害我,因為你沒有資格和我斗。你只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幻影而已,或者只能引起廉價的反響罷了。你無論使什么花招,對我都無濟于事,難道你連這點都不明白!這段對話很像是“9·11”事件爆發后,絕對強者“美國大總統·布什”對以拉登為首的暴力集團發表的聲明,也好像是美國強硬派對暴力集團者們發出的憐憫之聲。總之,像烏鴉的少年這樣的少年們,懷著必死的信念,絕望地投身攻擊超級大國——美國,其結果只能是飛蛾投火。言下之意就是,像你們這種自取滅亡的攻擊方式,受傷的、滅亡的只能是你們自己。但是,直面強大的美國,對美國懷有報復心理的、像烏鴉少年一伙的人們,除了用這種方式攻擊美國,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呢?這就是現實世界,同時也是村上春樹通過作品對現實中到處潛在著這種暴力危機的反思。因此,正如川村湊所指出的那樣:“《海邊的卡夫卡》中新的主題,不再是表現‘喪失’,而是旨在表現‘缺失’。所謂‘缺失’,就是現實中人們對愛與憎、善與惡,缺乏真正的判斷體系。”[8]51也就是說,直至《挪威的森林》為止,村上文學一直在表現充滿感傷情調的“喪失”的一代,而到了《海邊的卡夫卡》之后,其敘事主題轉為旨在表現:戰爭、暴力,以及導致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社會根源。這一主題無疑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繼《海邊的卡夫卡》之后,村上春樹在《1Q84》(2009年)中,進一步挖掘了關于“暴力”的主題。林少華就指出:“《1Q84》是一部關于善與惡的故事。惡是村上‘始終都在思考’的和描寫的一個主題。”因此,“直面‘混沌’的現實,描寫‘混沌’的《1Q84》應運而生。從這種意義上,《1Q84》可以說是歷史題材的擬寫,即以現在的坐標把握奧姆真理教事件,賦予這一過去不久的歷史事件以新的內涵,質疑現有的惡善標準,探討歷史與現實、未來的關系,表明自己對日本以至世界現狀及人類走向的擔憂和思考,其中未嘗不含有對世界在‘9·11’后趨向全球化、同質化、宗教化之可能性的警惕。”[10]119這就是村上小說《1Q84》的創作主題,也是時代賦予作家村上春樹的歷史使命。
四、結語
縱觀村上文學作品直面不同時代表現的敘事主題,以及賦予該時代的意蘊,我們從中不難看出,村上始終在介入對日本乃至全世界的現實社會問題的思考。在他的初期創作中表現的具有“喪失”一代情結的敘事主題,表現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雖然給人們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但同時讓人們深感精神生活倍感貧乏。對此,如果我們反思一下本國經濟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國民生活的巨變,不也存在如此種種現象嗎?因此,村上在他初期作品中探討的日本經濟高度發展下帶來的社會問題,同時也是我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下普遍存在的現實問題。因此,“村上現象”就成了“消費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個普遍性現象”[11]21。進入90年代后,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1990年,東西德國合二為一;1991年蘇聯分崩離析,二元對立的冷戰時代從此宣告結束,西方世界沉浸在資本主義勝利的喜悅之中。但是,好景不長,1995年日本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地鐵沙林毒氣事件;2001年爆發震驚世界的“9·11”事件。從此,暴力事件此起彼伏,局部戰爭和種族、宗教沖突接連不斷。直面現實世界,村上文學再現“暴力”與反“暴力”的主題孕育而生。可以說,村上文學始終背負時代賦予的使命,全面擔起對這個時代的愛與憎、善與惡的觀照和透視使命,竭盡全力地投身創作,表現了他對時代的獨特把握和感受。也正是因為村上春樹文學緊密地把握了時代脈搏,豐富地展現了時代特質,才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贊譽。
[1]大江健三郎.“我”從日本寄出的信[M].巖波書店,1996.
[2]拓植光彥.從作品結構到作家論——村上春樹[J].國文學解釋和教材研究,1990,(6).
[3]加藤典洋.夏天的19日物語——解讀“且聽風吟”[J].國文學解釋和教材研究,1995,(6).
[4]大江健三郎.最后的小說[M].講談社出版,1994.
[5]村上春樹.地下世界(文庫本)[Z].2006.
[6]吉田司.奧姆是我友[J].文學界,1997,(6).
[7]村上春樹訪談:「成長」を目指して、成しつづけて、載于“Monkey Business”2009 Spring Vo1.5[N].(訪談于2008年12月16日進行,采訪者:吉川日出男.
[8]川村湊:「アメリカ」から遠く離れて――「9·11」以降と『海辺のカフカ』、載于『村上春樹をどう読むか』[M].作品社出版,2006.
[9]小森陽一.歷史認識和小說[M].講談社出版,2004.
[10]林少華.1Q84:當代“羅生門”及其意義[J].外國文學評論,2010,(2).
[11]王志松.消費社會轉型中的“村上現象”[J].讀書, 2006,(11).
I206
A
1002-7408(2011)02-0105-03
陜西省教育廳2010科研項目“語義認知方向下的漢日被動句式比較研究”(2010JK312)。
張鵬(1978-),女,陜西寶雞人,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日語語言學和日本文學。
[責任編輯: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