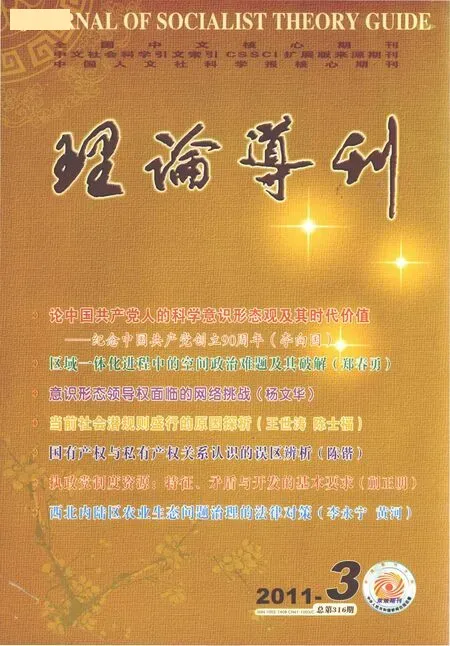社會資本對社會各階層政治距離的影響
白瑾,趙紅軍
(1.西安社科院政治學所,西安710054;2.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后勤集團,西安710071)
社會資本對社會各階層政治距離的影響
白瑾1,趙紅軍2
(1.西安社科院政治學所,西安710054;2.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后勤集團,西安710071)
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總體呈現出不平衡、不協調的特點已引起一系列的結構性社會問題。社會結構的深層次矛盾表現在政治結構上就是政治距離。政治距離影響了社會各階層對政治生活的關心度、對政府的信任度和各階層獲取政治資源能力。從社會資本視角切入,社會資本對各階層政治距離的影響因素表現為:信息交流與獲取決定了各階層間的流動性,高階層的影響決定了各階層間的政治距離,階層社會信用決定了階層之間的政治距離,階層間的政治距離強化了身份和認同感。
社會資本;政治距離;社會階層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總體呈現出不平衡、不協調的特點已是學界共識。據一些權威課題組研究,中國的社會結構大約滯后經濟結構15年。這種結構差是當今諸多經濟與社會矛盾和問題的結構性原因。[1]社會結構淺層次矛盾主要表現為社會對抗行為的激烈程度不斷增加,由自我傷害型逐漸向報復社會型轉變,由個體事件逐漸向群體事件發展。那么,這種結構差表現在政治結構上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呢?政治距離是政治人的關系狀態描述,意指每個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之間必然存在一種互相聯系的關系結構,這一結構內含著空間的要素,即政治距離。政治距離可以從物理學和哲學心理學層面來認識,物理層面的距離是指可見的空間關系,而心理層面的距離則是指互相的認同、信任關系。[2]當前,人們在拆遷工作中往往反映出對政府部門的不信任,對基層領導干部評價低,對建構社會關系網的熱衷,實質上是干群之間、人與人的信任危機,逐漸向政治危機滲透。由于個體差異和制度制約,個人獲取各種有利于再發展的政治資源的能力存在差異,腐敗可能引發的政治心理認同、信任危機,是否將各階層的政治距離逐步拉大,社會資本如何影響各階層對政治資源的獲取,政治距離與社會資本的價值取向等等,都是亟待研究的課題。
二、社會各階層與政治的距離現狀
政治距離分為空間距離和心理距離。空間距離表現在社會結構上,就是社會階層之間的距離。心理距離表現為對別的階層的認同與信任,特別是對社會地位比自己高許多的階層。距離本身不具有價值取向,但是與社會階層聯系在一起就有了價值取向,尤其是與獲取政治資源的能力聯系在一起時。從一些統計數據來看,距離政治信息發源地最近的階層,并不一定關心本地區的政治生活;一些執行政府決策的階層,也不一定就對某些政府工作信任度不高;而那些需要政府提高公共服務的階層,反倒較難從政府部門獲取相關信息。
1.政治距離影響各階層對政治生活的關心度。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已經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結構,分化為“十大階層”,這是社會的進步。與此同時,對政治生活的關心度也由全民參與向階層分化轉變。雖然“新社會階層”已進入國家政治生活,但中國新富關心中國經濟發展,對國內政治卻不甚關注。即使是已具備一定經濟實力的私營業主,對政治榮譽的關心度也遠遠低于對經濟發展的關心度。2007年,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北京市私營企業主狀況調查”結果顯示,京城四成私營業主認為自己政治地位低,可是,77%的受調查者認為“和社會上其他階層成員和睦相處”是一項迫切的任務,遠高于“與黨政領導經常保持聯系”和“爭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相反,筆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低收入階層更關注政治生活。馬克思說過,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現實生活中,低收入群體的切身利益常常得不到保護,或者受損的利益(如下崗和失業)不能得到必要的補償,一些人雖然也會對公開的“政治承諾”產生懷疑,進而產生政治不滿,可是絕大部分人把自己這種狀況歸因于自身素質差。他們或是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目的而了解政策,或是為提高自身素質,大多對新聞聯播和大到中央領導,小到鎮長的政府人員的變動進行各種解讀。
2.政治距離影響各階層對政府的信任度。政治信任是共同體內部成員對權力團體和其他相關個體的確信,并愿意接受某種統治秩序和共存關系的價值態度。信任程度高的,則心理距離就小;信任程度低的,則心理距離大。一般來說,高信任度的社會表現出高度的和諧性和穩定性,社會具有高度的活力;而低信任度的社會表現出內部分裂和爭斗,乃至政治的動蕩不安。普通群眾對政府工作的效率來自于生活感受。如果群眾在政府部門辦事順利,他們就會真心實意地稱頌;如果不順利,就可能會對政府產生不信任。信任度的高低也與他們距離政府官員的距離有關。這就是美國專家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提出的“距離悖論”:“人們相信或者崇敬離他們近的政府官員,而認為離他們遠的政府官員則是懶惰、不稱職和不誠實的。”
3.政治距離影響各階層獲取資源的能力。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的結盟使得經濟精英距離權力中心更近,獲取資源的綜合能力更強。例如,房地產界為了保護自身利益,雇傭一批文人向政府闡明房價不高的原因,企圖影響國家房價調控政策;而相對弱勢的購房人,由于不掌握話語主動權,只得被動承受房價的無理性剝奪。農村社區選舉的不公正性也能說明政治距離對獲取資源能力的影響。在一些農村,任當地村委會領導職位的人,不乏農村以前的閑人、混混,借助農村居委會換屆選舉平臺,他們通過賄票方式攫取了村委會最高領導權。掌握了村級領導權的所謂“精英”,通過腐蝕拉攏上級領導干部,使其客觀上成為自己攫取非法利益的“保護傘”。市場機制下這種"政治距離影響經濟能力,經濟能力決定政治距離,政治距離提高經濟能力"的怪圈,只能是愈演愈烈,階層政治距離進一步拉大。
三、社會資本對各階層政治距離的影響因素
林南將資本定義為“期望在市場中獲得回報的投資”,社會資本定義為“期望在市場中得到回報的社會關系投資”。[3]資本的概念溯源于馬克思,但是社會資本指出了資本是在社會關系中獲得,并引出了資本獲得的結構約束與機會問題。為什么嵌入在社會網中的資源可以幫助一些人達到行動的目標呢?林南認為主要是信息、影響、社會信用和強化四要素影響著社會資本。由此可知,不同階層掌握社會資本的多少又進一步影響他們獲取政治資源的能力,決定了他們的政治地位。穩定的社會結構應該是一個社會流動率較高的社會,即就是各階層間距離保持不斷變動的社會。階層之間的適當距離,可以促進社會流動,保持社會活力。適當的政治距離,可以促進政治民主化,防止腐敗產生或蔓延。如果階層距離不具有流動性,甚至由精英聯盟制定特定政策阻止社會流動,輕則引發社會矛盾,重則可能引發政治危機。那么,人們從哪些途徑更容易獲取有用信息,獲取這些信息是否需要付出代價呢?社會資本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分析框架。
1.信息交流與獲取決定了各階層間的流動性。在市場不完備和社會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社會關系能夠為個人提供其他渠道得不到的關于機會和選擇的有用信息。一方面同質階層間的信息交流不僅加深成員間的友誼,還可以在小范圍內形成亞文化圈。一般情況下,同處于金字塔結構較高位置的階層成員,更傾向建立這種亞文化圈,例如一些經濟精英愿意與政府官員建立“深厚”的個人友誼,縱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亞文化圈內通過成員間互通有無的信息交流,進一步加強了階層內部的人際交往,以及彼此提供向上流動的必需信息。另一方面這種信息在異質性的上下階層之間的流動,客觀上幫助了低階層的人向高階層流動,更有利于打破固化了的階層結構。由于社會流動大多傾向于向上流動,通過社會關系獲得的信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低階層對重要信息的選擇更傾向于從比自己高的異質階層獲得。如果是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互通信息,則容易形成精英聯盟;如果信息在政治精英與普通百姓之間交流,則容易促進階層的流動性。
2.高階層的影響決定了各階層間的政治距離。高階層因為處于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的較高位置,占有的社會資源更多,獲取各種信息更便利,所以他們的社會威望更高,一方面他們的文化、價值觀、行為和語言等范式對其他階層的社會成員具有較大影響,另一方面,社會其他階層的成員也主動把他們的文化、價值觀、行為和語言等范式“誤識”為社會“客觀”范式,自覺接受高階層的影響。這種主動交流與被動交流的反復交替,逐漸分化了較低階層,愿意接受較高階層影響的人,階層距離逐漸縮小,反之則會階層距離拉大。反映在政治距離上,政治精英如果能既維護自己既得利益,同時愿意讓渡一部分利益給較低階層,以維護社會基本平衡,那么他們的文化與價值觀容易獲得各階層的認可,階層之間的政治距離則會縮小。如果政治精英借助特殊社會地位不斷與民爭利,壟斷某些社會資源,那么,社會各階層的政治距離必然會拉大,距離達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社會結構的斷裂,中外各國的革命史已然證明了這一點。
3.階層社會信用決定了階層之間的政治距離。在社會資本理論里,個人的社會信用是被組織或代理人確定的個人社會關系,個人信用的高低反映了其通過社會關系與網絡,即個人的社會資本,獲取資源的能力高低。我們都知道,個人獲取資源的能力越強,其社會信用越高,對別人的影響也越大。如果其掌握的是稀缺的政治資源,他或她與亞文化圈內的人的政治距離會更近,與圈外的人距離更遠。如果稀缺的政治資源被一個階層所獨有,并拒絕與其他階層人分享,就會導致階層政治距離拉大。許多干群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就是一個例證。當群眾無法通過合法渠道取得必要信息時,掌握資源的政府部門或官員如果不能及時公開信息,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再如果其個人或部門信用一向被群眾解讀為濫用,這些人或部門與群眾的政治距離就會急速拉大,最終醞釀為群體性事件。相反,如果這種政治資源變為全民共享,各階層之間的政治距離就不會明顯。如在各種災難面前,如果各級政府及領導能及時救民于水火,他們的政府威信或領導威信將空前高漲,政府或領導個人所能獲取資源的能力就更高。
4.階層間的政治距離強化了身份和認同感。缺乏流動性的社會結構容易固化,掌握社會資本的能力可以強化身份和認同感,各階層間不同的政治距離將會進一步強化階層身份和認同感。例如“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問題。“農民工”原是學術界為研究方便,對改革開放后中國境內出現的鄉城遷移者的統稱,也有人稱他們為“流動人口”、“外來人口”等。學者陳映芳在一些城市社會調查中也發現:“農民工"雖然有較普遍的不平感,但面對城市政府,基本上不表達(利益訴求)、不申訴(權益受損狀況),被稱為特殊的"沉默的群體”。[4]這種主動與城市環境保持距離的態度,使他們把生活目標(價值獲得方式)以及在城市的生活原則、生活方式,設定為基本與農村、農民相同,普遍認同自己是“外地農民”、城市“局外人”的社會身份。這種身份認同,客觀上進一步拉大他們與其他階層的政治距離。他們或許住在城市社區,卻不參與社區活動,因此身份通常得不到同社區人的認同,即使是城市底層人或下崗工人都以城市人自居,主動拉開與他們的距離。
四、破解社會資本負效應的幾點對策
一是加強社會信息公開化,建立制度規范社會資本的機制。社會資本的“價值中立”決定了它的兩個價值效應——正效應和負效應。社會資本的正效應可以降低信息交換的成本,加快信息的流動,打破階層文化區隔,促進階層政治距離的縮小。但是社會資本的負效應容易形成階層內部的亞文化圈,信息在亞文化圈內流動,容易形成權力的暗箱操作,關鍵信息的壟斷。正確對待社會資本,就要規范各種用人機制和定期公布社會信息等制度,盡量做到制度管人,克服亞文化圈影響政府決策的可能性。
二是縮小階層差距,增進社會互信。獲取社會資本能力的差異性,導致了高階層人對低階層人的政治、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不同影響。文化的區隔性特點,容易使社會階層固化,進而拉大階層距離。其中明顯的政治距離將會強化階層身份和認同感,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縮小階層差距就是縮小階層收入差別,縮小社會競爭機會差別,縮小階層文化的差異性。增進社會互信就要盡量不去損害底層人的利益或及時足額補償底層人的受損利益,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擴大公共服務范圍,盡量讓不同階層的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三是建立多元化的社會價值觀。不同階層的人都希望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原因之一是社會資本可以幫助其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和更高的社會地位,擁有更多的政治發言權。這種單一的價值觀,必然使稀缺的社會資本尋求資本尋租的路徑,其中腐敗就是最常見的社會資本尋租行為。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貪官面對法官提出的贓款,振振有詞地辯解說:“這是正常的人際交往,是他們為答謝我的幫助給我的。”建立多元化的價值觀,就要改變社會對“成功”的單一評價體系,建立“行行出狀元”的評價機制,鼓勵社會成員通過不同領域、不同途徑追求人生價值最大化。尤其反對“學而優則仕”的腐朽價值觀,破除“議而不治,治而不議”的文人怪癖。
[1]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建設[N].學習時報,2010-08-30.
[2]劉圣中.政治的距離[J].人文雜志,2008.
[3][美]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和行動的理論[M].張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3,8.
[4]陳映芳.“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同[J].社會學研究,2005,(3).
D663
A
1002-7408(2011)03-0047-03
白瑾(1971-),女,陜西定邊人,西安社科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社會階層;趙紅軍(1964-),男,西安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后勤集團工程師,研究方向:社會政策。
[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