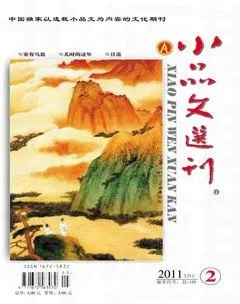那根
2010年12月31日,這一年的最后一個凌晨,6點。
風頭如刀,悍雪橫掃。
一輛救護車呼嘯著沖進茫茫雪霧之中。
救護車護送的,是一個肝臟,它剛剛離開陪伴了59年的一個軀體,現在它要繼續前行,去履行一個莊嚴的使命,延續另一個垂危的生命。
救護車正在駛離的后方,是北京宣武醫院。這里,數名醫生正神色凝重、細心而完整地縫合一個已經沒有肝臟的胸腔,這顆胸腔中的那顆心于2個半小時前停止了跳動。
救護車正在駛往的前方,是天津武警醫院。那里,一盞水銀燈下,一位等待肝臟移植的病人,已經躺在水銀燈下,醫生正在做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能呼吸時,就要有尊嚴地活著;臨走時,我要毫不吝惜地將自己的生命像接力那樣傳遞給別人。只要我身上還有一件對別人有用的器官,當最后離開現實世界時,就一定無保留、無條件捐贈他人。”
他怕冷,他蓋著自家的那條羽絨被走了,卻留下了他的脊椎、他的大腦作為醫學研究;留下了肝臟給瀕臨絕境的患者帶去生機。
寒夜的徹骨,剎那間,被一個依然溫潤、依然鮮活的肝臟溫暖。
徹骨的寒夜,一瞬間,被一個叫“史鐵生”的名字照亮。
“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這9個字放在史鐵生身上,是那樣令人心酸地契合。17歲中學未畢業就插隊去了陜西一個極偏僻的小山村,一次在山溝里放牛突遇大雨,遍身被淋透后開始發高燒,后來雙腿不能走路,運回北京后被診斷為“多發性硬化癥”致使雙腿永久高位癱瘓。20歲便開始了他輪椅上的人生。
病癥的后遺癥導致眼睛復視,脊髓功能的損害導致小便反流使腎功能受到嚴重損害,泌尿系統感染導致敗血癥。惟一值得慶幸的是經過及時治療,眼睛得到恢復。
史鐵生與各種痛苦的病痛周旋三十多年。十多年前腎病加重,轉為尿毒癥,必須頻繁地做腎透析才能維持生命,只有中間不做透析的兩天的上午可以做一點事。即使這樣,他也沒有停止寫作。他曾不無“幽默”地說:我的職業是生病,業余是寫作。
在最生龍活虎最狂妄的20歲青春年華里,突然沒了雙腿成了一個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幾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廢人”,這幾乎挑戰了一個人的最高理智極限。他的脾氣變得陰郁無比且暴怒無常,他常常會突然狂暴地捶擊自己,喊著:“我活著還有什么勁!”母親撲過去抓住他的手,“咱娘兒倆在一塊兒,好好活,好好活……,”事實上,這個時候母親的肝病已相當嚴重,常疼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覺,可她將兒子瞞得緊緊的。
那年北海的菊花開了,母親用央求的口氣說和他一起去看看菊花,他居然很難得地答應了。母親高興地一會兒坐下,一會兒站起來,然后就出去做準備去了。他怎么會想到,母親這一出去就再也沒回家。突然大口吐血的母親被送進醫院,昏迷前她留戀的不是自己僅僅49歲的人生,而是掛心自己的孩子:“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未成年的女兒……”
母親猝然離去之后,仿佛一記悶棍將史鐵生敲醒——在他被命運擊昏了頭的時候,他一直以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個人,其實孩子的不幸在母親那里總是要加倍的,他是母親惟一的兒子,母親情愿截癱的是自己而不是20歲的兒子,可這事無法代替。
看到孩子沉陷于無助的深淵,她要找到一個讓孩子活下去的路,可是她找來找去也找不到,這種無助注定她是活得最辛苦的母親——積郁于肝,才讓她四十來歲便被肝病奪去生命。他懂得了母親臨走前未說完的那半句話:他與妹妹倆人在一塊兒,要好好兒活……
他有一次與一個作家朋友聊天,問朋友他寫作的最初動機是什么?作家朋友說:“為了我的母親。為了讓她驕傲!”也許有人會說這位朋友的寫作動機太低俗了吧,似乎與神圣的寫作沾不上邊兒,但朋友坦率地說,我那時就是想寫出好文章來在報刊上發表,然后讓母親看著我的名字和文章印成鉛字兒,讓別人羨慕我的母親。
這種坦率深深深打動了史鐵生。然而,當史鐵生的頭一篇作品發表的時候,當他的頭一篇作品獲獎的時候,他多么希望他的母親還活著,看到兒子用紙筆在報刊上碰撞開了一條小路,至少她不用再為兒子擔心,欣慰他找到自己生存下去的道路和希望。
當他被生活的荊棘戳刺得滿心疼痛時,他沒有沉淪,而是勇敢地抬頭,他看到母親的眼神是荊棘上開出的美麗花朵,在陪伴他一路前行。他有一次在廣州剛去醫院透析完,就去領獎。透析之后是很痛苦的,然而他就那么靜靜地、微笑著面對每個人。
他一路彈著命運的琴弦,高歌。
許多人可能初看他的文字,會覺得平淡而選擇放棄。我也是。少時看他的《命若琴弦》,覺得文字平淡,竟未看完就丟下了。年少之人都喜歡繁花似錦的文字,待歲月輪回,一個又一個深夜,我一次次重拾《命若琴弦》,才讀懂,那荒涼山坳中無休止行走的老瞎子,就是史鐵生,就是他自己。
“永遠扯緊歡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無字的白紙……”
就像他自己,無所謂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也無所謂誰是誰,就那么永遠而執拗地扯緊著命運這根弦,不去看那,空茫而又無情的人生。
作者自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