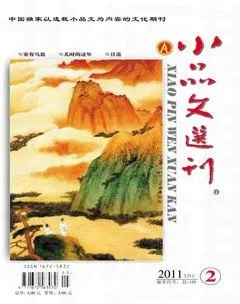牽掛
至今我仍清晰地記得,在縣高中寄宿之后,我就被母親由一根電話線牽掛。本想著學成之后,能留在鄉下的父母身邊,給他們一些幫助,但并不如愿。
大學畢業之后,我來到離家千里的省城,5年彈指過,回家的次數卻屈指可數。每次聽到母親在電話里說“有空就回來吧”,是懇求,似命令,話音不像是落在耳際,而是落在心底,泛起層層愧疚的漣漪。如今又到歲尾,我不禁想起了去年在家時,和母親一起忙碌的幸福時光。
去年,我從省城到家的時候,已經是臘月二十六了。吃過午飯,母親說:“你都一年沒吃麻花了,你小時候最愛吃它了,給你炸馓子。你給我做下手,快一些!”
看著母親和面、搓條、盤條、翻炸、濾油,像一套復雜的程序一步一步地完成。母親嫻熟的動作有條不紊,尤其是纏好的面條放進油鍋時,那樣的神情那樣的動作,如同小學生做作業般地小心翼翼——擔心熱油會濺出來燙傷正在燒火的我。
待到晚上8點多的時候,母親看著一簸箕和兩蛇皮袋麻花,揚揚頭捶捶腰,笑了。而同樣在廚房待了一下午的我,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終于“解放”了。“拿著吃吧,孩子,嘗嘗怎么樣,可口不可口?”母親見我難堪的樣子,笑著吩咐,如同招待客人,這是她有意無意堅守了一輩子的習慣。
第二天,母親又在廚房炸雞、炸魚、炸丸子、炸油糕——沒有什么活兒,母親翻著花樣做吃的,從早到晚。第三天,她開始蒸要吃到正月十五的饅頭……
“媽,你就不覺得累嗎?平時莊稼又是種又是收就夠忙活的了,好不容易到過年了,整天還忙成這樣子,就不知道坐那兒歇歇?再說,做那么多也吃不了啊!”看著母親匆忙的背影,我有些嗔怪她。
“媽也累啊,但累得心里踏實啊!看著你們高興地吃著玩著,當媽的我心里也高興!”母親不以為然,笑著說,“你是不知道啊,平時,你們都不在家,看著這么大的院子就我跟你爸,心里空著呢!你爸他血壓高,不能吃油膩的東西,那個時候,媽就是想忙著做這做那,也找不著人吃啊!”
在回省城時,母親執意要送我,她背著裝滿食物的包,還裝著很輕松的樣子,一路叮囑我:“在外要懂禮讓,不要惹是生非,記著沒事的時候常往家里打個電話啊……”我不住地答應著,走在身旁的母親,步履緩慢,皺紋溝壑的臉也被勞作打磨得更顯蒼老。
我每每疲憊地躺下或難以入眠時,都會想起母親,她在忙碌著什么,為什么從未對孩子有絲毫的要求,也不奢求什么回報?自從孩子出生后,我才明白:從孩子呱呱墜地的時候,一個母親就開始了第二次生命。以后,不管是咫尺還是天涯,不管是貧窮還是富有,不管是被呵護還是被忽略,孩子都是母親心中最放不下的牽掛。
選自《京郊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