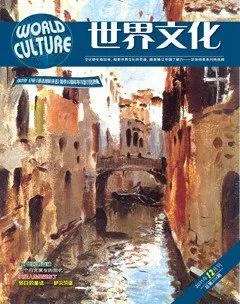一個白宮醫生的回憶
初到白宮,負責總統安全的特勤人員告訴我要時刻防備總統遭襲受傷。聽后我還感到很生氣,為什么會有人傷害我的“病人”?但遭遇多次險情之后,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
克林頓總統在任的8年里經歷了各種威脅。醫生隨時準備著:一旦總統遭到襲擊,要立刻進行搶救。因此,我也處于各種危險之中。特勤處稱總統附近的區域為“死傷區”,和總統在一起就是面臨死傷,這使你感到一種莫名的壓抑,體會到和刺客最有價值的獵物在一起的刺激感。8年來,在“死傷區”工作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還好,我沒有受到傷害。但并不是每一個在“死傷區”的人都這么幸運,例如1981年時任里根總統新聞秘書的詹姆斯布雷迪就成為刺客約翰-辛克里的犧牲品,子彈擊中他的頭部,造成下半身癱瘓,只能終生在輪椅上度過。提到詹姆斯布雷迪,我想起了向他借車的事情。
那是1997年3月,當時克林頓總統因摔傷在貝塞斯達海軍醫院就醫。出院前一天,值班的特勤官員對我說:“夫人,有個麻煩事,我們的車子無法搭載坐在輪椅里的總統。”“難道特勤處的車庫里就沒有羅斯福時代留下來的車?”我挖苦道。特勤聽到這句話驚訝得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我一向是個禮貌溫雅的人,說話謙和并帶點幽默感。但自總統住院后,我連續看護了三天三夜,連洗浴都顧不上,真是精疲力竭、近乎崩潰。這時特勤又提出這樣的問題,我也顧不上禮貌,更不用提平時表現出來的幽默了,便隨口說出這樣一句揶揄的話。我意識到自己失態了,于是又用平靜的語氣說:“真對不起,我不應該這樣說,你剛才的意思是我們沒有能放得下輪椅的轎車嗎?”“是的,夫人。”特勤用一副公事公辦的語氣答道,“我們能把他背到轎車里嗎?”“恐怕不行,”我否定了他的建議,如果美國總統靠特勤人員背著上下車真是有傷國體和尊嚴了。“他應該坐在輪椅上離開貝塞斯達,到達白宮南廊后再停下來坐在輪椅里接受記者采訪。”
聽到這里,站在旁邊的海軍副官說:“我們能不能從用過輪椅的人那兒借個小貨車?這兒不是有一個在越戰中失去雙腿用輪椅的議員嗎?”特勤—下子打起精神:“好主意!”他想了一會兒又說,“最好去找詹姆斯布雷迪,他肯定有能搭載輪椅的特備車。”
在克林頓總統出院的前天下午,特勤部門聯系到了詹姆斯布雷迪,他慷慨地把車借給了我們。我坐在從布雷迪處借來的寬敞的車子里,旁邊是在輪椅里的克林頓總統,這時我想起了“死傷區”。克林頓總統是許多刺客的目標,布雷迪的車又沒有任何裝甲,所以這次旅程最易遭受襲擊,這也是我頭一回如此接近潛在的暗殺惡魔,幸運的是我們安全到達了目的地。
醫生所受的訓練大多是與傷病做斗爭,而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但作為軍醫,我們的義務就是在危險的環境中履行義務。白宮醫生知道所服務對象的生命和安全高于自己的一切。醫療小組流傳著一個黑色幽默:如果“空軍一號”墜落,新聞的頭版就會報道某某總統和“其他人員”遇難。我們這些醫生就是不知名的“其他人員”,將很快被人遺忘。想到此總會讓我們和家人感到一絲不快,但這樣也好,會讓我們認清自己的使命,不至于產生自大的心理。
另外一次危險的經歷是隨克林頓總統出訪。我們先從土耳其起飛,途經希臘的雅典過夜。在雅典的那一晚,我們待在酒店沒敢出去,因為街道上到處是抗議者和燃燒的汽車、垃圾桶。
第二天“空軍一號”從雅典起飛到意大利。途中,空乘主管走進醫務間,坐在我旁邊的護士問他:“您需要什么?”護士認為主管可能需要阿司匹林或要問一些醫療方面的問題。看起來有點心煩意亂的主管盯著地板上的醫療箱說:“什么也不需要,我想檢查—下這些箱子。”我問:“為什么?”主管沒有回答。在檢查完我們的醫務間后他用略帶輕松的語調說:“我是為了找出不應該在這兒的東西。”“你是說發出‘滴答’響聲的東西?”護士問。“呃,類似于那樣的東西。”主管含糊不清地說著,快步走出了醫務間。
后來我從特勤處得知,當“空軍一號”正在跑道上滑行時,無線電通知說飛機上有炸彈,15分鐘后爆炸。飛行員采取了兩個明智的舉動:一是召集特勤到駕駛員座艙來聽關于炸彈威脅的錄音,二是把定時器定在15分鐘。15分鐘后沒有炸彈爆炸,于是飛機繼續滑行起飛。
接著我們到了馬其頓,在飛機降落的軍事基地周圍有很多標志提醒人們注意在此區域有地雷。我的高級助手克雷格·阿什比已在飛機降落的軍事基地等著我們,然后我們和總統一起換乘直升機“夜鷹1號”到科索沃,在那兒克林頓總統將進行一個雙邊會談。由于去科索沃的安全級別很高,我的副手理查德塔伯乘坐后備直升機“夜鷹2號”隨行。盡管任務艱巨,我還是非常自信,因為我把白宮醫療組最高級和最有經驗的成員都帶來了。
造訪科索沃的時間很短,我們很快返回到馬其頓的停機坪。這次任務使用了很多交通工具——直升機、裝甲車、航母、“空軍一號”等。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受人擺布的機器人,機械地背著醫療箱按照指令隨“主人”上下車,時刻看護好“主人”,以備萬一他受到傷害時我能做出快速反應。
感謝上帝,科索沃之行沒有什么意外情況。能夠和我的醫療小組安全回到在馬其頓等候的“空軍一號”就是對我最大的獎賞,當巨獸似的飛機爬上高空,大家算是松了一口氣。我的醫療小組成員此刻已放松下來在座椅上休息了,高級助手克雷格-阿什比總是一副不茍言笑的樣子,但現在我察覺到他的嘴角露出一絲笑意。高級護士史塔克斯樂于接受危險的任務,并把執行這些任務看作是探險之旅,但這一次長時間高度緊張的“探險”使他精疲力竭,他已閉上眼睛熟睡起來。另一個是我的副手塔伯中校,他的金發凌亂地從頭后部直豎起來,真有點孩子氣。看著這三位成員,我突然意識到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把最富經驗的人員都帶來了,一旦飛機失事,總統和我們這些“其他人員”遇難,那誰來管理白宮醫療小組,誰來照顧新總統呢?
我讓聯絡官拿來保密電話,撥通了在白宮醫療辦公室值班的官員芭芭拉艾迪。接電話的艾迪聲音清脆,顯得很高興。我用緩慢清晰的聲音說:“芭芭拉艾迪指揮官,請記錄如下白宮醫療小組接任人員名單……”我告訴她一旦飛機失事,誰有能力管理白宮醫療小組,誰可以繼任高級助手,誰能承擔高級護士的工作等。艾迪從我的語氣中聽出了事情的嚴肅性,她認真記下我說的每一個名字,我能想象出她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在黃色的便箋簿記錄我說話的樣子。
“記下來了嗎?”我問。
“記下了,夫人。”她用顫抖的聲音回答,“還有其它事情嗎?”
“如果我說的成為事實,記得在阿林頓國家公墓給我留個地方。”實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我繼續說,“我請求葬禮在辦公室舉行,要有完整的儀式、護柩的人和音樂。”
“是的,夫人。”艾迪回答。
“如果我的遺體還能夠套上衣服的話,記住要用我的藍色制服。”
“是的,夫人。”她哽咽道。
打完電話,我嘴角露出一絲自嘲的笑。我知道擔任“第一病人”的醫護工作,在執行任務時不得不考慮這樣的事情。當上白宮“御醫”在別人看來很風光——辦公室和總統的辦公室在一起、時常乘坐“空軍一號”跟隨總統出訪世界各地等等。但是作為白宮醫生,我還是一名軍人,在白宮行醫如同在戰場作戰。這份工作讓我整日在外奔波,體會不到家的溫馨,我也渴望過上正常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