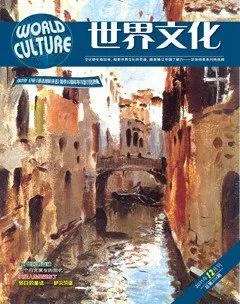從《語法修辭講話》的寫作談呂叔湘先生的社會責任感
報告人:張伯江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句法語義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郭繼懋教授(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呂先生離開我們已經18年了,這些年來我也經常想起他,尤其是在今天紀念《語法修辭講話》60周年這樣一個重要日子里,我們更加地懷念他生前的業績。這么多年過去了,語言研究在呂先生、朱先生開拓的方向上走了這么遠的路,我本人也是參與者,對學術方面的體驗也逐漸深化。在這個過程中,我也經常想起來,經常反思,想想呂先生他們這一代學者究竟留給我們的是什么樣的學術遺產,尤其是2004年紀念呂先生的百年誕辰的時候,媒體采訪到我,問我對呂先生感觸最深的是什么?我說感觸最深的就是他的社會責任感,這一點直到他離世我都不是體會很多,直到2004年我編輯呂先生的傳記,才發現對他的學術境界有了一些新的體會。我很愿意在這兒跟大家分享在這些方面對呂先生的了解和我自己的體會。
呂先生一生很多重要的轉折點都很好地詮釋了這一點,《語法修辭講話》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解放初期,毛澤東主席親自倡議要糾正公文文書中的語言文字缺點,責成中宣部的胡喬木同志弄出一些具體的措施,胡喬木找到了權威的語言研究機構,希望他們寫一部講語法規范的書,沒想到給回了。葉圣陶葉老當時是教育部的副部長,他就主動地向喬木同志推薦了呂先生,他說有一位呂叔湘可以做這件事情,而且我保證他可以做好。葉老就請呂先生和喬木同志見了面,把中央意圖說了,呂先生想了想說可以答應。喬木同志問有沒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呂先生說我只提三點:第一個,我希望你們能給我提供一些素材,比如說報紙雜志、政府公文、大中學生的作文,那時候材料并不易得,不像現在網上一搜就全有;第二呢,當時呂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他說我在清華大學想找一位助手幫著我做;第三,要求在兩三個月內完成,時間這么緊,我們兩個人的課時適當地減一點。喬木同志說這都沒問題。有的學者,當時可能是出于明哲保身吧,很明白這件事情將會給自己帶來什么樣的麻煩,就拒絕了這項任務。我覺得這是呂先生的社會責任感驅使著他,他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語法修辭講話》對國家的文化建設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他和朱先生就把這件事承擔下來了。后來的事實證明了這本書的深遠影響。呂先生給我講這事的時候講得很輕松,我聽著卻是非常的感動。我覺得一個學者,把自己悶在書齋里面,固然可以做很高深的學問,但是你怎么看待你這個學問在社會中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愿不愿意同時用你的學問來影響一般民眾,我覺得這是有境界的差異的。
這件事,主要是葉老的推薦,為什么葉老敢這樣推薦呢?這得自于兩位老先生的淵源。他們兩個人是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認識的。我想要講一講我所得知的他們最早的相識,到葉老怎么成為影響呂先生一生的人。呂先生自己也說,如果沒有葉老,他對學術境界的認識可能都不會有這樣的轉變。呂先生1938年提前結束了在英國的留學回國,先在云南大學,1940年到成都華西大學工作。華西大學出了很多響當當的人物。呂叔湘當時40多歲,也是其中的一個頂尖的人物,他在華西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里邊主要做歷史語法的專題研究。現在我們從呂先生的論文集里邊一翻開就是那幾篇文章,呂先生近代漢語研究最重要的幾篇,都是在華西完成的。這里就發生了一個故事,1941年年初,一個春天的早晨,葉圣陶敲開了他們家的門。葉圣陶當時是四川省文化廳的廳長,主持四川省的語文教學,為了提高中學語文教師全面的素養,他想推出三部書,一部精讀指導,一部泛讀指導,一部文法指導。其中這部文法書,葉老邀請呂先生寫。呂先生用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把《中國文法要略》寫出來了,現在已經成為中國語言學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當時這部書是葉老為了中學語文教育,為了提高中學語文教師的素養而倡議編寫的。呂先生通過這個事情的實踐慢慢理解了葉老的思想,在葉老去世以后,呂先生寫的懷念的文章里邊說,如果沒有那天他來找我,我可能學術思想上不會有這種轉變,從那時才知道學術的普及工作,不僅不是第二流的工作,跟學術研究一樣的重要。呂先生寫這部書,在中國文化研究所還挨批了,當時研究所負責人的觀念就是大學者不能寫通俗的東西,必須寫專而又專、深而又深的東西。呂先生在葉老先生的影響下,發生了這一生認識上的重大轉折,從那以后,他就一直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作為學術界的領袖,以自己的學養和眼光引領著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從來沒有忽略初等教育的投入,比如在開明書店編了一些國文讀本等等。
我再說一件上個世紀70年代的事情。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文革”結束了,這些老先生從干校回來紛紛聚首,都有誰不在了,大家在一起唏噓一番,很多老先生都心灰意冷。在1976年底呂先生得到一份很好的宣紙,請葉老題字,1977年初葉老就寫好了,是兩首詩:“華西初訪猶如昨,既接清芬四十年;邃密深沉殊弗逮,愧存虛愿欲齊賢。”這是說他們四十年的交誼;“并臻信達兼今雅,譯事群欽夙擅場。頗冀移栽名說部,俾因椽筆得深嘗。”葉老的意思是,你翻譯小說的出色成就我是知道的,真正是信達雅,葉老說你不如用你的精力來多翻譯文學名著。可是這一回呂先生沒有聽葉老的。因為呂先生心里有放不下的心結,他從年輕時起就為祖國文化事業的振興而努力,可以說一生都在為這個目標而奮斗,短短的十年“文革”又遭到了全面的破壞,他為此痛心疾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1977年“文革”結束后那十來年里,他不僅參加了語言學界眾多的學術會議,也參加了大量的語文教學方面的會議,中小學語文教學體系的擬定等,到處奔走,“注音識字,提前讀寫”就是他和王力先生大力支持才推廣開的。他一直在這兩條線上奔走,一方面關注全民的教育,語文普及;另一方面完成他在語言學界的使命。我覺得從他和葉老幾十年的交往的側面就可以看--出來,他的境界是什么樣,所以紀念呂先生百年誕辰的時候江藍生先生稱他為“人民的語言學家”。
《語法修辭講話》凝聚了兩位老先生當時對漢語語法的理解,呂先生也常常囑咐我們,只有把語法規律研究透了,才能拿出來指導實際語言應用。所以我們覺得一方面不能忽視對學術普及方面的重視;另一方面,作為專業研究人員,我們更需要把我們的研究工作做好。我本來為這次會議準備。了。一篇論文,可能沒有時間細說了,簡單向大家報告一下。
呂先生在《近代漢語指代詞》里討論“這、那”的時候曾經提出“轉稱稱代”和“直接稱代”兩個概念,沿著這個思路,我們發現,漢語的“這+量+名”格式也存在呂先生在討論稱代問題時所指出的兩種語義的區別。我的文章認為,這個現象反映的是漢語沒有定冠詞所帶來的結果。漢語沒有定冠詞,定冠詞的功能常常是靠指示詞實現的。與英語定冠詞用法相應的語法成分中,量詞是個關鍵。漢語的指示詞不可能離開量詞而發展為定冠詞,“指+量”是個相互依存的整體。這也是受呂先生在語法研究上重視英漢對比、提倡方言語法觀察的影響得到的一點發現,我想也是有助于漢語教學的實際應用的。我們在研究所里邊長年累月地都在做這樣的工作,越做就越體會到呂先生當初告誡我們的,理論問題解決得越好,你去給人家做普及的時候,你的說服力也就越強。所以我今天來用這個題目參加會議也是表示對前輩學者的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