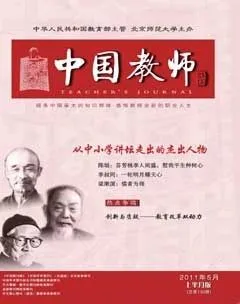陳垣:芬芳桃李人間
編者按:
2010年教師節,溫總理在講話中說:“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當中小學教師不會有大出息,我認為不是這樣,教中小學也能出大師……在這個平凡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業。”遵循總理講話精神,《中國教師》將以“從中小學講壇走出的杰出人物”為主線,展現這些歷史人物的中小學教師生涯對其本人終身成就的影響,與所有教師共勉。本期推出歷史學家陳垣、藝術家李叔同和儒學大師梁漱溟。
2002年9月8日,有兩座銅像在北京師范大學落成,一座是孔子銅像,另一座則是北師大老校長陳垣先生的全身像。陳垣,這個在史學界讓人如雷貫耳的名字,如今可能會讓人們感覺有些陌生。作為一個史學大家,他并不像胡適、王國維那樣,有著廣為流傳的坊間段子,但在學術界,他的學問是沒有人不嘆服的,陳寅恪就曾說過,他平生最佩服的是王國維和陳垣,陳垣學問踏實,德才兼優。
陳垣,字援庵,又字圓庵,1880年生于廣東新會棠下鎮石頭鄉(棠下現已劃歸江門市蓬江區)。和那個時期的眾多大家不同,陳垣是靠著《書目答問》和《四庫全書總目》啟蒙的,無師承,自學成才,也沒有留學列國的背景。他在宗教史、中國歷史文獻學、元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飲譽海內外,被學術界譽為“一代宗師”。更令人稱道的是他在教育界的傳奇經歷,陳垣從事教育工作長達70年,通觀古今中外,有如此長期教育生涯的教育家是不多見的。他教過蒙館、小學、中學、大學,在國立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都擔任過教授,并連任了46年的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其培養的人才之多,用他1962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今日》一文中的“芬芳桃李人間盛”一語來形容再合適不過了。陳垣先生逝世后,回憶、紀念他的文章有200余篇,其中作者大多是他的學生,而許多已經成為當時著名的學者或史學界的領導人。
師意:人生須有意義,死須有價值
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
——陳垣對啟功語
陳垣第一次走上三尺講壇時年僅18歲,自己還是舊式學館的學生,因為文采出眾,在書館里常被“貼堂”,鄰里就請他到一家蒙館教書。彼時的老師,總是在學生背不下書時打手板或打腿,陳垣自己也挨過打,所以對這樣的體罰很反感,他教蒙館后,貼出告示,不打板,不體罰,受到了學生家長的一致歡迎。
1906年,陳垣因在《時事畫報》經常發表反清文章而引起了清政府官員的注意。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回到了家鄉新會,任篁莊小學堂教員。這是一所新式的鄉村小學,他在這里教國文、算學、體操、唱歌、美術等科目。這些課程在當時是很新鮮的,很受學生歡迎。放假時,他便常和學生去遠足,并采集一些植物標本。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學生們很喜歡這樣的新課程,所以他們歡迎我這個從廣州來的新教師。”[1]他是小學堂里思想很新的教師,一般教師都穿沒有領子的長褂,有時腰間還系一條絳帶。陳垣卻穿著黃色操衣(即制服),同學們都說他很精神,師生感情很融洽。沒多久,廣州的風聲稍緩和,他便離開篁莊回廣州,同學們紛紛前來送行。陳垣晚年曾回憶起江邊送別的情景,說:“啟程那天清晨,同學們半夜就來到江邊送行,船已開了很久,他們還站在黎明的晨曦中,揮帽告別。”[2]55年后的1961年,他在這所小學教過的學生歐陽錦棠,從廣州來北京開會,到他家去看望,兩人都已經須發斑白,當他們談起在小學上課、遠足的情景時,仍然會完全沉醉在少年的回憶之中。
1913年的春天,陳垣懷著對民族興旺、國家強盛的美好向往,只身從廣州來到北京,開始了自己短暫的政治生涯。但很快地,在參加了所謂的眾議院的幾次活動后,他逐漸看到了很多過去想象不到的事情:議會成了爭權奪利的場所,成了派系奪權、集團牟利、爾虞我詐、置國事于不顧的官衙。推倒了幾千年的帝制,換來的卻是一批軍閥。他們利用民國之名,巧取豪奪;盜得議會名義,以充當自己的工具。
1920年,華北旱災嚴重,農民逃亡外鄉,北京街頭每天都有從外縣災區涌進的大批難民,扶老攜幼,缺衣少食。陳垣看到這種慘狀,便和朋友們商議,集資辦起一所半工半讀學校,起名為“北京孤兒工讀園”,陳垣擔任園長,并負責教務。該園不收任何費用,還供給食宿,使很多無依無靠的孤兒得到了較好的照顧,深受社會的歡迎和稱贊。30年代著名的電影演員黎莉莉姐妹,因其父母都參加革命,幼年時就在園內就讀。陳垣還為該園題寫了一副對聯——“無私蓄,無私器,同惜公物;或勞心,或勞力,勿做游民”——掛在園門兩旁。從這副對聯中,陳垣關注教育、開辦學校之意,可窺一斑。[3]
1920年9月,他又與朋友創辦了平民中學,即今北京市第41中學前身,這座中學除招收一部分本市小學畢業生外,大部分收容的是河北災區逃難到北京的青年。學校不收學雜費,對清寒學生還有補助,這使得許多小學畢業無力升學的學生,也得到了繼續讀書的機會。陳垣自己任校長,兼教國文、歷史,包括中國文學史等課程。中國文學史這個課,是他在別校從未教授過的。而當時的平民中學,也因其授課出色、紀律嚴明,在北京的中學里鶴立雞群。[4]
1921年,陳垣還擔任了教育部次長(即副部長),但是在舊政府工作的經歷讓他覺得筋疲力盡,常常事與愿違,件件事情都不易推動,理想的實現更是遙不可及。經過觀察和體驗,他認為當時的政治是“骯臟的”,也更加堅定了他“人生須有意義,死須有價值”的人生觀,從此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教書育人、讀書治史的道路。
師心: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東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陳垣《中國史料的整理》
陳垣身上有著很強的戰斗因子,他反抗過清朝、北洋軍閥和日偽政權,除了在報紙雜志上對各種反動勢力進行口誅筆伐之外,陳垣還將自己的拳拳愛國心融入到了教育事業當中。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宣揚“品行第一”。在輔仁大學的返校節上,陳垣給大家講了一個孔子開運動會的故事:《禮記》有一節是講孔子主持射箭比賽的事情,讓誰把門呢?弟子子路。孔子說,有三種人不能參加:一種是敗軍之將,一種是為敵人做事情的,一種是認敵為父的。很多漢奸聽了以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敵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