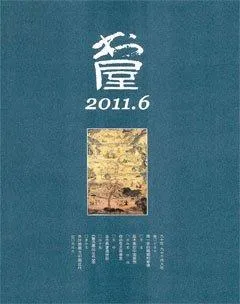鄒漢勛咸豐元年系獄事考
鄒漢勛(叔績)與魏源、何紹基并稱“湘中三杰”,以精研經學、地理、文字音韻著聲于時;又曾協助鄧顯鶴湘皋首刊《船山遺書》,是近代湘學的代表人物,《清史稿·儒林》和《清史列傳》均有傳,咸豐三年末與江忠源在廬州同太平軍作戰時戰死。王闖運作《鄒漢勛傳》敘其死事之后有云:“初,漢勛之為諸生也,過邵陽。邵陽令固驕庸,以事收之入獄。事頗亟,自院司以下皆不能道地。會太守至郡,念所以出之。時五月,俗重五日節,太守開宴,僚吏耆老人士畢至,太守虛上坐,遣人持紅紙書名,稱‘頓首’,詣邵陽獄迎鄒先生。于中無鄒先生,唯有囚,太守即迎囚,囚即鄒先生。於是獄吏大驚。出漢勛。”將此事描述得很富傳奇色彩,而對產生這戲劇性一幕的本末不詳,連這位太守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李元度在《國朝先正事略·鄒叔績先生事略》中云:“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為申理。諸生某爭于縣庭,先生隨眾往觀,令并執而幽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解。”事情的原委大略可知了,也說到力救他的人是鄧湘皋,但對那位為他平反冤獄的太守卻完全沒有提及。
這在朱克敬的《儒林瑣記》中才找到了。他在此書的《儒林附記》中寫了十三位當時還在世的湘籍和寓湘名人,如郭嵩燾、陳寶箴、王閩運等,也包括他自己。卷中第一位便是“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改寶慶府同知,升永順府知府,署永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寶慶人鄒漢勛以事為知縣所系,文琛遣役持柬備肩舁,詣獄迎鄒先生,明日即劾知縣,出漢勛獄”。敘鄒漢勛出獄的細節與王閩運大致相同,重點則是寫黃文琛及其仕履,更沒有言及從中起作用的鄧湘皋。
朱克敬是甘肅皋蘭人,以家貧客游四方,咸豐間曾任湖南龍山典史。雖兩任湖南巡撫惲世臨、劉崐皆重其才,薦入朝而不用;諸友憐其貧困,共同籌集千金相贈,遂流寓長沙。他與黃文琛、郭嵩燾諸人均友善,郭嵩燾在《日記》卷四中稱其“詩筆雄渾,高出諸人之上”。有關鄒漢勛出獄的詳細經過,看來他也是一直留意的,果然,在所著的《雨窗消意錄》甲部卷二中又有了記載:“寶慶鄒叔績漢勛,有學行。咸豐三年,與江忠烈公忠源俱死廬州,身后著述零散。同治初,羅研生中翰輯《湖南文征》,咨于黃海華先生,先生復書日:‘咸豐辛亥歲四月,某往攝寶慶郡事,行次界嶺,得鄧湘皋山長書,以邵陽有冤獄相告,而又不言其所由。湘皋時已赴永州,與姚石甫廉訪為西山之游,未由緘問。及到邵,邵陽令先期往隆回相驗;一問,始知叔績以事系獄。先是,東門外有無名男子縊死富戶某姓山樹上,詣驗,吏仵均云無傷,埋葬了案。叔績訪得乃其族子,死有他故,同其族姓來縣呈控。堂訊大觸令怒,遂以事不干已、詐索扛訟、哄鬧官署等情革辦。是夜叔績自獄中上書自訴。明日,提釋詳雪,復其衣領”’,云云。
當事人一說事情就眉目清楚了。時值咸豐元年(1851)四月下旬,鄧湘皋的好友姚瑩于起用后又由湖北鹽法道升任廣西按察使,到長沙后即派人送信至邵陽約他去永州會面,這時,他們已分別二十六年了。鄧得信后即匆匆上路,但心里又牽掛著鄒漢勛的事,為了不耽擱時間,乃即派專人持信赴界嶺去等候這位即將來上任的署理知府黃文琛。然而以他當時正是府學山長之身,又不便在信中向這位尚未履新的知府私控現任的邵陽縣令,只能讓黃深感此事使鄧連過幾日從永州回來再面談都等不及了,絕對不同于一般,必須立刻查辦。界嶺是接湘鄉界往邵陽的官道站,距邵陽縣城一百二十五華里,府縣同城。黃到任后立即一查,原來是鄒漢勛系獄,當晚就收到了鄒漢勛自獄中的上書。這是一篇寫得極其辭工藻美的駢四儷六文,自然是鄧湘皋在行前就告知鄒準備好了的。于是,第二天鄒漢勛就經“提釋詳雪,復其衣領”。(因鄒漢勛那時是秀才,按例于收禁前須革去功名,昭雪后便立即恢復其秀才身份。)
鄒漢勛系獄的時間應該是四月十一日。鄧顯鶴《南村草堂詩抄》卷二十四有《四月十一日作》詩云:“旌旆悠悠甫出城,風波驀地滿城驚。雙清六嶺無顏色,棠渡濂池怒有聲。載酒東山方問字,馳書西粵正談兵。可憐一老無情緒,咄咄終朝意不平。”只須一對照便可了然:首聯寫縣令的驕橫跋扈;頷聯寫鄒之冤獄在當地引起天譴人怒,句中的雙清亭、六亭山、甘棠渡、愛蓮池俱邵陽名勝;頸聯的上句指鄒日前還剛到鄧湘皋書院所在的東山問學,下旬指時江忠源正率楚勇在廣西作戰,鄒有書馳往談兵;尾聯寫鄧滿懷義憤之情,全詩俱系圍繞鄒漢勛的事而作。鄒漢勛在獲釋后有《和湘皋先生四月十一日作》詩云:“翕然絕跡古梅城,不受風塵半點驚。親愛每教勤有業,盡傷何詎哭無聲。舊經篇已多聞義,群從讎原后執兵。盂博無言橫見逮,深紉詩老為持平。”鄒漢勛以博聞強記著稱,詩文皆極喜砌典,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中說“其中式引用書,九房無有知其出處者”,不過這首詩倒不難索解。他們倆都是新化人,新化固古稱梅山,縣城即號梅城;他長期追隨受教于鄧湘皋,相與編校圖書,執經問難,鄧也對他特別關心;只有尾聯稍覺冷僻一點。孟博乃東漢范滂字,范平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亦遭無辜系獄,事見《后漢書-黨錮傳》。鄒在《獄中上黃海華太守書》中有句云:“嗟嗟靈均好潔,非因諫而致累;孟博揚清,乃無言而見逮。”此文已收入羅汝懷輯《湖南文征》卷一O一。末句的“紉”字典出屈原《離騷》“紉秋蘭以為佩”,比喻自己已將湘皋先生力救之恩深系于懷。
按王闿運所作《鄒漢勛傳》,鄒出獄是在端午節這天;朱克敬《儒林附記》只說“詣獄迎鄒先生”而未言何日;黃文琛則但云“明日,提釋詳雪”,是否備肩舁以及是哪一天都沒有提到。考黃文琛在這天確實舉行過慶典活動,鄧顯鶴《南村草堂詩抄》卷二十四有《端午日黃海華太守文琛率僚屬詣濂溪祠為元公作生日,百年曠典也。詩以紀之,簡彭學博同作》一首古風詠其事,周敦頤卒謚元公。時鄧顯鶴正“我編周子全書成,首載度尚公年譜,大書營道誕降地,天禧元年五月五”,并于“是日以手訂《全書》及新采五色芝敬獻”。因知那天主要是為了紀念周子的誕辰,而這一天又是由鄧顯鶴所考定,鄧是在這之前一日或二日才趕回邵陽的。《南村草堂詩抄》卷二十四有《冷水灘行別紫卿,兼簡姚石甫觀察桂林,何子貞編修道州,時約游九疑未果》詩引言云:“五月朔日離永,紫卿拉舟送我于冷水灘,時石甫先一日赴粵,子貞尚留滯道州。余以故人在系,倉皇告歸。為賦《冷水灘行》,兼寄二君,不自知其言之長也。”朔日是當月初一,鄧于先一日才送別姚瑩,因為心里懸掛著鄒漢勛的事,所以何紹基要邀他游九疑也沒有答應,就匆匆趕回邵陽。按清制,凡府州縣每歲遵照《會典》于正月十五日、十月十一日於儒學行鄉飲酒禮;太守并無于端午宴僚吏耆老之俗,這一黃文琛到任后的首次公眾活動,顯然是鄧顯鶴這位山長向他提議的。于是,乃有“圣主改元日端午,太守率屬肅祠宇。敬為元公作生日,此事今無昔未睹……是日天朗氣淑清,傾城冠蓋趨荒圃。新蒲荷葉相參差,簪艾焚香齊佝僂。我抱遺書隨后拜,手五色芝代角黍”的盛舉。鄒漢勛是郡廩生,當然也應邀參加了。為了張揚給他恢復名譽,黃太守特意遣役持紅柬去迎他亦是有可能的。至于王湘綺在傳中的種種描述,則可能是于鄒殉難后摭拾些民間傳說的夸張,因為是日并不是設宴為鄒壓驚,鄧湘皋在詩中亦無一語涉及。所以羅汝懷在同治初年編輯《湖南文征》時,還特地要修書去詢問黃文琛。羅汝懷一直自稱是鄧湘皋的弟子,又曾與鄒漢勛一道參與編校《船山遺書》,兩人極為相諗,關心他的事跡和遺著是必然的。
黃文琛同時是一位著名詩人。鄧顯鶴在鄒漢勛釋后四個月就去世了,他的絕筆詩之一《點定黃海華太守詩集付刊,綴以二律》中有句云:“當代論詩稱健者,涪翁豈但博詩名。問天遠嗣騷人響,張楚還為大國聲。”對其評價甚高。彭洋中在《思貽堂詩集序》中稱其詩“憂時感事,觸物起興,言近旨遠之妙,莫不天真絕俗”。徐世昌在《晚晴簃詩匯詩話》中亦說其“長篇短什皆有浩浩落落之致,而字字必經洗練而出”。郭嵩燾在《黃海華先生<玩靈集>遺詩序》中則謂“南士能詩者無敢與先生比并……其后官寶慶,官永州,屢攝縣事,典郡,凡為利于吾民者靡弗舉也,為病于吾民者靡弗厘而正也。于是又益稱先生為能吏,不徒為詩者”。當郭嵩燾因好言洋務致謗,幾不容于鄉里時,黃文琛作《寄筠仙侍郎》詩,斥煽事者為“捉風病狂吠雪怪,多口紛爭難與強”;勸慰郭“自來功德藉文字,吾曹當作千秋想。飛輪火舶早歸來,援古證今誘徒黨”,可知他同時又是一位極有思想,富于改革志向的人。
關于鄒漢勛系獄的事,在光緒十一年刊由郭嵩燾、李元度總纂的《湖南通志》鄒傳中亦有記敘:“漢勛之族子有為邵陽某所橫斃者,漢勛憫其冤,質于知縣。知縣受賄不直,反下漢勛獄,思中以法。知府黃文琛平之,事得解,罷知縣。”原來是知縣受了賄,所以盡管鄧湘皋等在之前極力援救,都無法疏通。時正知府出缺,縣令可以一手遮天,便亟思“中之以法”,匆忙結案。這也正是鄧湘皋連黃文琛到任后再面談都等不及了,要派人持信到界嶺去告知他“邵陽有冤獄”,催促他速來查處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