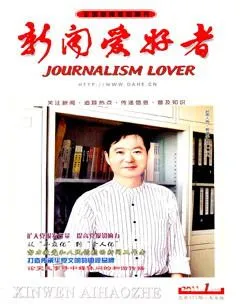“如果有來
他就是新聞界“大師”——范敬宜了。我疾步迎上前去,自報家門:“我是從河北大學(xué)來的,專門在此等候您。”范老就騰出那只拎著一個印有清華大學(xué)標(biāo)志的藍(lán)色手提袋的右手,熱情地與我行常規(guī)之禮。他問我:“你的手怎么這么冷?”我說有點(diǎn)緊張。他說:“不要緊張,我不是官,我是個小老頭。”
聽我們向茶館的服務(wù)員指名道姓地要新上市的頂尖龍井,范老打岔說:“不要這么客氣,我本是一個很普通的老頭。”接著又給我們解釋,說他很少在家里接待客人,老伴83歲了,沒有請保姆,懶得收拾,又偏愛清靜,所以就只好把我們約在這里見面。清香林茶館的經(jīng)理也來作證,說范老經(jīng)常在這里接友會客,這清香林茶館是他的“根據(jù)地”。范老的一番自嘲和茶館經(jīng)理的旁白透露了眼前這位新聞大師對晚年生活寧靜致遠(yuǎn)的追求。
小隱于鄉(xiāng)野,大隱于朝市。79歲的范老從人民日報總編輯崗位上退休后沒有告老還鄉(xiāng)、沒有閑著,反倒更忙了,他以古稀之軀受聘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院長,同時又兼任著社會團(tuán)體數(shù)不清的名譽(yù)會長、顧問等頭銜。能在這里見縫插針地采訪他,對面品茗,聽他談新聞?wù)勅松瑢?shí)在是三生有幸。
“我有很多思想都是群眾給的”
1957年,范敬宜因?yàn)閮善s文被定為右派,被發(fā)配到遼西最偏遠(yuǎn)的農(nóng)村接受改造,而且一下就是20年。“就是在那些年,我才真正了解到中國的國情、民情,特別是中國的農(nóng)村。”深山出俊鳥,鄉(xiāng)野有馬列。在訪談中,范老多次談到他的羈押地遼西,談到遼西的風(fēng)土人情。翻開擺在茶幾上的《范敬宜文集》,第一張照片就是茅屋前的大笑,與幾個農(nóng)民肩并肩地?fù)г谝黄稹?br/> “我有很多思想都是群眾給的。”范老扳著指頭,一字一頓,如數(shù)家珍——《莫把開頭當(dāng)過頭》、《回頭路辯》、《政策要放寬,管理要跟上》、《夜半鐘聲送窮神》、《月光如水照新村》,這些作品,我們知道它除了篇篇都是新聞教科書上的精品之外,當(dāng)時對撥亂反正,推動農(nóng)村體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設(shè),都發(fā)揮過相當(dāng)大的作用。
“我寫不出好文章的時候,就往下走,去到群眾的生活中找素材、找靈感。”范老又回顧起30多年前的往事,那個時候正是改革開放之初,十一屆三中全會盡管已經(jīng)開過兩年了,但農(nóng)村的形勢還屬于早春二月,不但沒有到處鶯歌燕舞,而且還是倒春寒。有的地方甚至出現(xiàn)暴風(fēng)雪,到處能聽到“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fù)辟”、“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倒退到從前”的奇談怪論。“當(dāng)時我想寫一篇駁斥這種觀點(diǎn)的文章,但是我寫來寫去寫得很蒼白。我只是被動地說,我們不是走回頭路。我們是在前進(jìn)。但這樣的話沒有分量,壓不住陣,人們也不服氣呀。”好在范老有20年的農(nóng)村體驗(yàn),他就坐上膠輪大馬車往下走,往他熟悉的生產(chǎn)隊(duì)走,在那里召集干部群眾開座談會、辯論會。在農(nóng)村的牛圈馬棚,在農(nóng)民的田間炕頭,范老獲得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寫作思維猶如井噴。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對毛主席的這句話,范敬宜理解最深,他在執(zhí)掌人民日報期間,曾處理過不少寫在兒子演算本上、包裝尿素的牛皮紙上或者是廢舊書刊封面上的人民來信。范老說:“群眾來信有讀頭、有看頭,別說有真理的成分內(nèi)含其中,單就是語言上,也有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的地方,言簡意賅,直奔主題,不像秀才們寫的文章,三紙無驢,既長又臭。新聞講求個性語言,而現(xiàn)在的寫作成了一個模式。官話、套話,看不出群眾的思想,把不準(zhǔn)群眾的脈搏,這種東西(文章)不用采訪也能照葫蘆畫瓢寫出來的。”
談及現(xiàn)在的新聞寫作文風(fēng),范老認(rèn)為要增加文章的可讀性,就要多一些生動活潑的群眾語言,少一些枯燥乏味的材料語言。范老舉了一個曾發(fā)生在他身邊的例子:“一次有個地方的通訊員看到好新聞就順手用抽完香煙的空盒寫了一篇原汁原味的新聞。寄到人民日報后被編輯相中,我拍板讓這個香煙盒上的新聞上了《人民日報》。”范老看重的是來自群眾中的語言,哪怕語法有錯誤,只要能表情達(dá)意,說明問題,就將群眾原汁原味的話搬上報紙,“這種稿件是記者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甚至想都想不出來的,它能讓人看了以后特別過癮”。范老的意思是希望記者多盯著百姓身邊事,把關(guān)注力投放到基層和老百姓生活中去。
“記者不闖禍,不是好記者”
范敬宜是范仲淹的28世孫,自幼對詩書畫很是敏感。可惜范老在孩童時體弱多病,不能正常上學(xué)堂。陪伴少年范敬宜的就是家中的史書報刊,他甚至在家里自寫自編了一份手抄報《靜園新聞報》,靜園是他家弄堂的名字,版式學(xué)《大公報》、《申報》,報紙的內(nèi)容為鄰里小事,讀者也是左鄰右舍。沒有人幫他發(fā)行,他是自辦發(fā)行,偷偷往人家的門縫里塞。
總想搞點(diǎn)動作出來弄些文字出來讓很多很多人看的少年范敬宜有幾次看到一個當(dāng)記者的鄰居下班后經(jīng)常在弄堂里頭吃一碗餛飩,邊吃邊東張西望,生怕別人和自家兒女發(fā)現(xiàn),于是。他就寫了一篇新聞《王大胖背兒女偷吃餛飩》,然后塞進(jìn)他的家門里。結(jié)果惹出一場風(fēng)波。這個被范敬宜戲稱為王大胖的記者找到范家興師問罪。他警告范敬宜的母親說:“你這個孩子,如不管教,早晚要惹禍的!”
“早晚要惹禍的”,這句話被王大胖所言中。范敬宜在以后的大半生中,屢屢闖禍。在他考取上海約翰大學(xué)并兼任校報編輯那年,他寫了一個影射醫(yī)學(xué)院院長的諷刺小品,不但給自己帶來了麻煩,也給學(xué)校添了亂,險遭開除。參加工作后又因兩篇雜文斷送了前程。行政連降四級并改變身份,舉家被遣送農(nóng)村。《莫把開頭當(dāng)過頭》這篇文章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播發(fā)后。他當(dāng)時還在農(nóng)村采訪,有人找到他,說省委書記要約見他,聽到這個消息后,他的頭嗡的一聲就炸了。心里忐忑不安,以為又闖下了大禍。
范敬宜對“記者不闖禍,不是好記者”這句話的理解是,新聞工作者要有自己的頭腦,要敢于擔(dān)當(dāng)。要有捍衛(wèi)真理的勇氣。記者闖禍要看什么禍,為誰闖禍。1989年6月4日的那場風(fēng)波,《經(jīng)濟(jì)日報》的記者就沒有參與上街游行,因?yàn)楫?dāng)時范敬宜在當(dāng)總編輯,他此時政治上已經(jīng)成熟,對“禍”這個字有了辯證和全面完整的理解。
范老說,記者的筆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除惡,可以伸張正義;用得不好,就可能禍國殃民,有時候,我們常常聽到有人引用李大釗的話“鐵肩擔(dān)道義,妙手著文章”,有些同志自以為是,但他擔(dān)的不是國家和人民的道義,而是他個人的英雄主義甚至是個人的偏見、個人的好惡。同樣我們強(qiáng)調(diào)輿論監(jiān)督,范老把輿論監(jiān)督比喻成刮臉刀,使用得好,使用得熟練,可以使人容光煥發(fā);使用得不當(dāng),可能在臉上劃出血口子,如果這個刮臉刀掌握在你的仇人手里,他保不準(zhǔn)在你的喉管上戳上一刀。其后果不堪設(shè)想。
“生活里,你淺入一下就有寫不完的地方”
范老談及幾十年從事新聞工作的最大感受時,總是用這樣一句話來回答同行:“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范老在北京,盡管享受有專車待遇,但他出行時很少叫車,多是以步當(dāng)車,即便在任時也盡可能地多騎自行車、多坐出租車。他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幾篇“兩會走筆”,就是乘坐出租車去往人民大會堂和政協(xié)禮堂的路上與司機(jī)聊天聊出來、侃大山侃出來的。范老說:“北京的出租車司機(jī)個個都是業(yè)余政治家,他會一路上給你反映各種情況,包括我這個總編都是聞所未聞的。所以我很喜歡打的出行或騎自行車出行。”
“現(xiàn)在有一種傾向叫做記者官員化。記者下去采訪,吃喝拉撒跟著官員活動,經(jīng)常處在受騙的位置,聽到的、看到的都是事先準(zhǔn)備好的。”范老認(rèn)為,至少有五種人不能當(dāng)記者:“不熱愛新聞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風(fēng)險的不可以,慕浮華的不可以,無悟性的不可以。”范老彎腰拾起掉在地上的香煙狠狠地吸了一口說道:“坐在辦公室里的/0zUpeE9UKg5BpsJgb3k8w==記者永遠(yuǎn)不能成為名記者。”結(jié)合自己干新聞的體會,范老很看不上那些懶得往基層跑的記者:“有不少記者抱怨新聞寫窮了、寫盡了,沒有什么可寫的了。其實(shí)生活里,你淺入一下就有寫不完的地方,用不著挖地三尺。”
干新聞和學(xué)新聞的人都知道范靜宜有一篇睡出來的新聞作品,叫做《月光如水照新村》,但很少有人有機(jī)會去了解范老寫這篇新聞的來龍去脈。當(dāng)問及這個話題時,范老娓娓道來:“1982年春天,我到遼寧康平兩家子公社采訪,公社秘書家里有事,就安排我臨時住進(jìn)秘書室,一住就是幾天,我發(fā)現(xiàn)這里晚上特別安靜,一是沒有接昕到一個電話,二是沒有來人要錢要糧和告狀報案的,我就找來秘書詢問以往的情況。秘書說要在以前就別想睡個囫圇覺,總有電話或來人打擾,有時天不亮就有人來堵書記的被窩。”兩者一對比,范敬宜問陪同的宣傳干事:“你發(fā)現(xiàn)什么沒有?”那干事回答:“沒有。”范老說:“我可發(fā)現(xiàn)大新聞了。”幾天后,一篇題為《夜無電話聲早無堵門人兩家子公社干部睡上安穩(wěn)覺》的短新聞刊登在《遼寧日報》上,《人民日報》轉(zhuǎn)載時改為《月光如水照新村》,在以后的傳說中,這篇稿子被同行說成是“睡出來的新聞”。范老說,能在沒有新聞的角落里設(shè)法抓到新聞是一種本領(lǐng),新聞記者就應(yīng)該鍛煉這種本領(lǐng)。
清華大學(xué)聘用范老的初衷或許是相中了他的招牌,沒想到這老頭給個棒槌認(rèn)作真(針),按時按點(diǎn)來坐班、來上課,言傳身教,一絲不茍。范老上任后特別強(qiáng)調(diào)實(shí)踐教育和社會調(diào)查。該學(xué)院有個學(xué)生叫李強(qiáng),在放寒假的時候回陜西老家做社會調(diào)查,回來后他用大量的非常有力的數(shù)據(jù)提出了8個問題。都是當(dāng)前農(nóng)村最重要的話題,比如農(nóng)民的醫(yī)療問題、教育問題、農(nóng)村基層政權(quán)建設(shè)問題。寫出了洋洋灑灑4萬多字的《鄉(xiāng)村八記》。出于對后生的獎掖,范老情不自禁地寫了一篇評價文章,讓全學(xué)院的老師傳看,后來他又覺得僅僅在清華顯然影響太小了,就冒昧地給溫家寶總理寫信推薦,溫總理很快給范老寫了回信,李強(qiáng)的《鄉(xiāng)村八記》因此上了《人民日報》。
范老在當(dāng)右派被勞動改造的時候,最大的奢望是能當(dāng)一個墻報的編輯。幫人家出出黑板報。后來一步一個臺階,當(dāng)上了遼寧日報的副總編輯,再后來當(dāng)上了經(jīng)濟(jì)日報的老總、人民日報的老總。新聞夢已圓,但記者情未了,“如果有來生,我還要當(dāng)記者。”他說的這句話,絕對不是賣噱頭,不是人生觀價值觀的套話,而是情有獨(dú)鐘,是對新聞事業(yè)那種難以割舍的情懷和對逝去的新聞歲月的深情留戀。正如他的那首膾炙人口的《滿江紅》:“平生愿。唯報國,征途遠(yuǎn),肩寧息?到巔峰仍自乾夕惕。當(dāng)日聞雞起舞,今宵扶劍猶望月。念白云深處萬千家,情難抑。”
編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