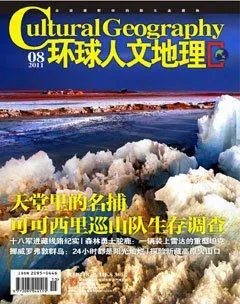父輩的旗幟
當我以《環球人文地理》特派記者的身份剛剛抵達可可西里的時候,就認識了秋培扎西。
夏天的可可西里,白天往往有20℃~30℃,紫外線射得人眼睛發紫,但晚上溫度往往又到了零下,索南達杰保護站內,我們升起了火爐,泡好了熱茶,開始第一次談話。
初次見面時,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這個坐在才旦周局長旁邊的藏族漢子是主力巡山隊員,厲害得很。
講到巡山的細節,情感的沖動使大家忘了可可西里由于氧氣的問題不能做大動作,他開始手舞足蹈地講那些趣事:“有一次,進山后水箱壞了,前后都是無人區,怎么辦?不可能走出去吧。大家就想辦法,用熔化牙膏皮的錫來補,結果翻遍了車廂,發現牙膏皮都是塑料的。娘的。最后好歹發現了一點錫——車上收音機的主板,就把那個拿來燒熔,結果就搞定了……”
更激動的時候,這個漢子還拿起筆,直接在我的筆記本上畫起地圖來。
我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談,窗外夜色越來越黑,板房上的冰霜也越結越厚。老志愿者楊震把茶爐擺上火爐,蒸汽讓我們溫暖。盡管這水有濃烈的味道,但大家依舊覺得很甜。
而當我知道他的身份后,我坐在那里開始有點發慌,似乎保護站外的空氣又變少了。回憶像甜苦的烈酒,使他兩眼發光,滿腔的感情,就像漲水的楚瑪爾河一樣涌動。我們聊了數個小時,卻不想停止。可是醫學常識告訴我,如果不睡覺,明天的高反會讓我頭更痛、被高反引發的牙髓炎也會更加厲害。我不得不硬生生地打斷他:今天就先到這里吧。
他又安慰我說:“其實昆侖山口就是個坎,你一出山就會好了。”
第二天聊天繼續。保護站門口有一面旗幟,旗幟下是一塊石碑,上面刻有為建站付出過的人的名字。他興致盎然帶我找到他的名字,我采訪他一些建站的細節,在敘述中遇到一個瓶頸,“這我說不清了,”他像孩子一樣失望地歪了歪嘴,“可是拉巴(野牦牛隊老隊員)好像知道,你下去格爾木后,可以問問他。”
他擺弄我的相機,說我們去照相吧。然后他站在“天路”——青藏公路中間,張開雙臂,就像在擁抱可可西里。他眼神純真,卻又堅定,執著。
那些當年的影像似乎又在我腦海中顯現:我看見一個眼睛清亮的12歲孩子,在格爾木的陽光下吃著糌粑,旁邊,他的父親與舅舅痛飲烈酒,正商量如何拉起一支拯救藏羚羊的隊伍;我看見一個16歲的孩子第一次在電影上看到親人的身影,是一部紀念自己舅舅被盜獵分子槍殺的悲劇,叫作《杰桑?索南達杰》;我看見一個血氣方剛的高中生考入了青海民族學院法律系,發誓要用法律來捍衛這片土地;我看見一個英氣逼人的青年跪在父親靈前,看著父親隨天葬升入天堂。畢業后,他毅然選擇接過父輩的旗幟,不懼嚴酷的自然環境和死亡的威脅,從容地走近可可西里……
在他的身上,我看見一個粗獷民族所培養出來的兒子,我看見一個典型的可可西里巡山隊隊員,我看到一個打不倒的斗士。更重要的是,我看見一種高大光明的人格。
“你見,或者不見,他就在那里!”提到父輩,他很平和,甚至還用上了電影臺詞。但我知道,父輩在他心中從來沒有漸行漸遠,而是永遠清晰地刻留在了他的心中,以及世紀的史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