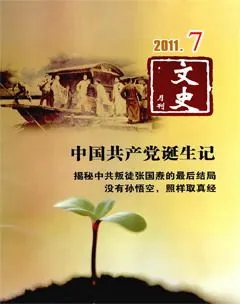古代文人靠什么賺錢
中國歷史上,從隋、唐、宋到元、明、清,持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從文人中考錄出700多名狀元、10萬余名進士和數百萬名舉人,他們提名金榜不久,就會被選派到各級“政府”,走上仕途,雖不是個個暴富,但拿著朝廷的俸祿,也都安居樂業、豐衣足食。
但科考的臨場發揮,無法把文人的才華全都“考”出來,一批在民間極具聲望的才子卻“屢試不第”,如王勃、盧照鄰、孟浩然、柳永、賈島等,這些文人不善農工商貿,他們謀生的手段大多依然是靠寫。但詩詞再美,也無處發表拿稿費,只是自我抒發消遣,他們寫些什么可以賺錢呢?
首先是受雇于“政府”寫公文。古時的府、道、州、縣官員,多是通過科舉選拔上來的,不乏文采,但他們都身居官位,忙于紛繁復雜的事務、聲色犬馬的享受,哪有功夫寫公文!于是每當有急于上傳下達的文件,就雇用民間寫手。如唐代詩人李邕文筆出眾,當地及附鄰州縣官衙紛紛拿錢請他寫奏折,李邕一生代寫公文800余篇。《新唐書》中記載:“李邕代撰官折受籌銀巨萬,據此為豪富者。”
唐代的知名文人賀知章、宋之問、駱賓王、王昌齡等,都是代寫公文的高手,所得報酬均不菲。
再是寫文賦。“賦”是抒發情懷、說明事理的一種文體,一如今天,我們要褒貶或講清某件事物,寫篇“博文”。
西漢時期,陳皇后失寵,為表明衷委,她請了幾個文人給漢武帝寫文賦,但陳皇后看了都不滿意。有人推薦司馬相如,此時司馬相如已因病退職回鄉,陳皇后鳳輦親駕,找到司馬相如。司馬相如聽完陳皇后的傾述,頓生同情,揮就凄楚委婉、動人魂魄的《長門賦》,武帝讀后大為感動,陳皇后遂復得寵,《長門賦》被后人譽為千古絕唱。
陳皇后為感激司馬相如,賞賜他100兩黃金的稿費。當時,一個人全年的生活費,一兩黃金就綽綽有余,司馬相如僅此一篇文賦,便一輩子吃穿不愁了。
《晉書·陳壽傳》載:有位富豪請陳壽為其父寫傳賦。陳壽說:“見與千斛米,為尊撰佳賦。”一篇傳賦開價千斛米,可見當時名人索要稿酬之高。
還有,就是給死者寫碑文賺錢。如唐代的韓愈,寫碑文頗得潤筆之利,他寫《平淮西碑》得到的酬勞是500匹絹,按《中國物價史》的記載換算:唐開元年間,500匹絹相當于7690斗米,而買7690斗米需要199940元,韓愈寫此碑文就拿了近20萬元稿費,而碑文只有1505個字,每字價值約132元。
白居易為元稹作墓志銘,其家屬付酬金70萬,白居易全部捐給了香山寺,為老友元稹積陰德。白居易雖晚年潦倒,但中年時卻很有錢,一捐就是70萬,看來稿費確實沒少賺。
清代的鄭板橋晚年寫有《板橋潤格》,對自己作品的稿酬明碼開價,且作詩說:“畫竹多于買竹錢,竹高一尺銀三千,任爾怨話任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他完全放下了“君子喻義不喻利”的虛榮,明碼標價,愿買愿賣!
古代知名文人也并不是個個靠寫致富,也有清高自傲、不為當權者所用,致力于“純文學”的,但他們大都貧困潦倒。
東晉末期的陶淵明雖才華橫溢,卻不愿為官府的“五斗米折腰”,一生在故里過著“躬田自資,夫耕于前,妻鋤于后”的日子。
號稱“詩圣”的杜甫,雖寫作成就很高,但因為沒有積蓄和經濟來源,過著類似乞討的日子,晚年時連住的茅草屋都“為秋風所破”。
出身名門望族的曹雪芹,幾乎一生投入到《紅樓夢》的創作中,從不去寫文賦碑銘賺錢,晚年窮困到“舉家日食一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