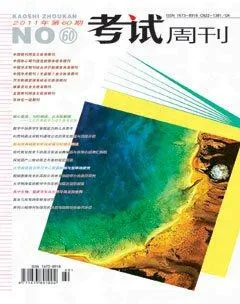多譯本存在的合理性
摘 要: 解構主義者認為意義是不確定的,文本是開放的,任何文本都沒有終極意義,強調譯者的創造性。該文借助解構主義翻譯觀,以“意義的不確定性”為理論依據對《老人與海》的四個中文譯本進行分析,旨在探討力圖展現多譯本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解構主義理論的譯學意義。
關鍵詞: 《老人與海》 中文譯本 合理性 譯學意義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翻譯理論開始涌入國門,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語言學派的翻譯理論。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認識到該派理論的局限性:首先,語言學派過分強調語言的共性,忽略了語言間的差異;其次,該派理論增強了二元對立的思想,并在此基礎上突出其中的一元。
90年代以來,德里達的解構翻譯思想被陸續介紹到中國;該思想消解了作者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絕對權威,否認原文文本存在終極意義,還重新定義了原文和譯文的關系,提出譯文是對原文的改寫和補充,譯文不僅讓原文繼續生存,而且讓原文活得更好。此外,德里達還堅持認為任何文本都是既可譯又不可譯,絕對忠實的翻譯是一項無法償還的債務。這些反傳統的觀念為中國翻譯界吹來了一股清新的學術研究之風,促使人們對傳統翻譯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反思,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去審視原文、作者、譯本和譯者。
美國當代作家海明威的小說The Old and the Sea是美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一朵奇葩,于1952年在美國問世,憑此力作海明威1953年獲得普利策獎、1954年贏得諾貝爾文學獎;1955年,The Old and the Sea的第一個中譯本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譯者為張愛玲女士。次年,大陸最早的《老人與海》問世,連載于《譯林》,譯者為資深編輯、翻譯家海觀。此后,《老人與海》的新譯本相繼在兩岸三地出現,2007年1月,黃源深先生翻譯的《老人與海》與讀者見面。本文借助解構主義翻譯觀,以“意義的不確定性”為理論依據對《老人與海》的四個中譯本(以下簡稱海譯,張譯,吳譯,黃譯)進行分析,力圖展現多譯本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解構主義理論的譯學意義。
二、意義不確定性與多譯本存在的合理性
在改造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差異”一詞的基礎上,德里達提出了“延異”(Différance)這一概念。在他眼中,語義就其實質而言,只是一種不斷變異與延遲到來的游戲。語言符號的意義不過是在文本中暫時得以確定,但隨著不斷產生的空間上的差異和時間上的延衍,意義也在不斷變化,因而任何語言都沒有終極和固定的意義。因此,德里達闡述了自己全新的譯學意義觀:原文文本身并不完善和統一,存在多重意義,任何對原文的理解和翻譯都不能窮盡其可能的意義,即使權威或完美的譯本也不可能因窮盡原文的意義而使原文封閉起來。[3](P76—77)
1995年,國內發表了第一篇研究德里達解構翻譯思想的文章;二十多年來,關于解構翻譯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其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有學者把德里達的思想等同于美國“耶魯學派”的思想;混淆德里達與瓦特·本杰明的翻譯思想;德里達在備受關注的同時,也遭到重重誤解。很多學者撰文批判德氏的觀點,認為解構主義就是一種“什么都可以”的理論,用到翻譯上就是“怎么翻譯都可以接受”。這樣的解說只是一種曲解,并未把握解構主義的真諦。事實上,絕對意義上的自由嬉戲并非德里達之本意,因為他強調語言的兩面特征,即意義的穩定性與不穩定性。[4]德里達只是通過延異說強調了過去被忽略的意義的不確定性以及在場的缺席,他的理論反駁將文本的意義看作是靜止的、孤立的傳統的翻譯理論,并未主張翻譯可以脫離原文,而是強調要用一種辯證的、動態的、開放的和發展的視角來看待翻譯。
根據德里達的觀點,意義隨著歷史的進程及環境的變化不斷地留下蹤跡。人們所理解的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意義,而是一種處在永無止境運動中的意思的蹤跡。如果一個詞具有多種含義,并且在具體的語境這些含義又能夠并存,譯者就會被“意義的嬉戲”所迷惑,進而作出不同的意義闡釋。正是這些各異或不盡相同的闡釋賦予了原文文本新的生命與活力;與此同時,不同的譯文文本之間也會產生一種相互關聯,也正是這種關聯性讓作為個體的原文文本得到了滋養和補充。以下兩個例子就是這一觀點在《老人與海》中譯本中的具體表現:
1.If they don’t travel too fast I will get into them.[1](P19)
海譯:要不是他們跑得太快,我會捉住它們的。[6](P51)
張譯:假使它們游得不太快,我就可以下手了。[2](P25)
吳譯:要不是它們游得這么快,我倒要趕到它們中間去。[7](P28)
黃譯:要不是它們游得那么快,我會沖到魚群里面去。[8](P43)
在《美國傳統英語詞典(雙解)》中,動詞“get”有“追求、獲得、趕上、到達”之意,盡管四位譯者具體的解讀不同,但都從不同角度表現了老人當時的心態,因為這位樂觀的老人已經連續84天沒有逮到一條魚了,此刻的他既信心十足又迫不及待。海譯表達老人的胸有成竹;張譯表達了老人的迫不及待;吳譯表達了老人的老當益壯;黃源深先生則是用了一個“沖”字,既表達了老人的老當益壯的心態,又顯示了他迫不及待的心情。
2.I wonder if he has any plans or if he is just as desperate as I am?[1](P25)
海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什么主意,還是跟我一樣沒有一點辦法呢?[6](P67)
張譯:不知道它究竟可有什么計劃,還是它和我一樣地拼命?[2](P34)
吳譯:不知道它有沒有什么打算,還是跟我一樣,不顧死活?[7](P36)
黃譯:不知道這是計謀呢,還是像我一樣已經絕望了呢?[8](P57)
四位譯者對文本中兩個核心詞匯plans和desperate的闡釋不盡相同,plan的釋義比較簡單,黃源深先生將plans翻譯為計謀,突出老人與魚的對立,其余三位譯者的理解都大同小異。而四位譯者對形容詞desperate的理解卻不盡相同,在美國傳統英語詞典(雙解)中,desperate有“不顧一切的,拼死的,絕望的,極想得到的”等含義,幾位譯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基本上把這幾種含義都闡釋出來了,海觀先生根據前文中提到的信息:“I can do nothing with him and he can do nothing with me,he thought.”[1](P24)把desperate闡釋“沒有一點辦法”,魚和老人一樣,此時此刻沒有一點辦法,只是一味地拖著船走了,而老人則是無奈地被拖著走。這樣的翻譯完全合情合理。然而張譯和吳譯的解讀是魚和老人一樣不顧死活,兩位的翻譯也在情理之中,因為老人在后文中表達了自己要奮戰到最后一刻的決心:“I’ll stay with you until I am dead.”[1](P28)
三、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The Old Man and the Sea被稱為一部女性角色缺失、全力彰顯男性的小說,但它的第一個中譯本卻是由女作家張愛玲執筆完成的,所以張譯有些地方把海明威的男子氣概給弱化了,如:“It was a man must do.”[1](P12)張譯:“活著總是要干的。”[2](P16)顯然,這是一個涉及譯者主體性的話題,在此一筆帶過。作為一篇短小的杰作,The Old Man and the Sea集中體現了海明威獨特的語言風格:遣詞簡短,較少使用形容詞,動詞豐富而準確;句式簡潔、短小,多用簡單句或并列句;敘述樸實、客觀、有力;然而正是這樣的一個文本卻被譯者闡釋得色彩斑斕,和而不同。不難看出,意義的不確定性使譯文的多樣性成為可能,并讓原文得到滋養和補充。The Old and the Sea這本當世的經典之作雖然已經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由海明威蓋棺定論,但是在譯者的筆下它必將一次又一次散發出新生的活力。
參考文獻:
[1]Hemingway,Ernest.The Old Man and the Sea[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3-69.
[2]海明威著.張愛玲譯.老人與海[M].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9:4-34.
[3]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74-77.
[4]Davis,Kathleen.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30.
[5]陳永國.翻譯與后現代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50.
[6]海明威著.海觀譯.老人與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3-67.
[7]海明威著.吳勞譯.老人與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3-36.
[8]海明威著.黃源深譯.老人與海[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7-57.
[9]吳定柏.美國文學大綱[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1.
[10]呂俊.我國傳統翻譯理論中的盲點與誤區[J].外國語,2001,(5):48-54.
[11]許鈞.試論譯作與原作的關系[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2,(1):15-21.
[12]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