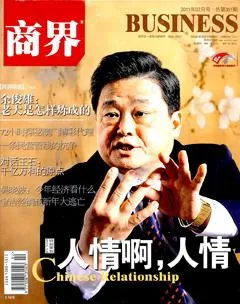一條民營管線抗爭
2011-12-29 00:00:00曹一方
商界 2011年2期


一個56歲的男人,究竟要經歷怎樣的內心掙扎和坎坷求索,才能搭建起一條短短100公里的管線?才能支撐起生命中最后一次奮力拼搏?
譚傳榮的心路歷程和商業智慧,無疑對所有在原國有壟斷行業門外躑躅不前、頻頻張望的民企來說,都是一個寶貴的參考坐標。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會議室外的走廊中,傳來譚傳榮一口地道重慶話:“來來來,見見我們家鄉的老朋友!”聲若洪鐘,熱情豪爽。
今年56歲的老譚,梳著卷卷的大背頭,留著濃密的絡腮須,一副久經江湖的大佬模樣。原本《商界》記者拜會這位老友,是為了解他公司籌備上市的故事。但是很顯然,老譚對此不愿多談,一見到記者,他大手一揮直奔主題,興奮地介紹起他剛剛在山西建成的一條煤層氣管道。
“這是中國的煤層氣第一次被商業化開發利用,更是中國民營企業第一次進入壟斷資源的規模輸送!”這樣氣勢恢弘的開場白,足以引起任何媒體記者的興趣——
倘真成事,從大巴山里走出來的譚傳榮,怎樣披荊斬棘突破行業桎梏,怎樣曲曲折折達到最終目的?或許對其他意欲進軍原國有壟斷行業的民企來說,他的心路歷程與商業智慧,將是一個寶貴的參考坐標。
重慶開縣人譚傳榮是民營能源產業的一名老兵。
1999年,重慶三峽庫區還沒有通上天然氣,都是燒煤。做飲料生意賺到第一桶金的譚傳榮,敏銳捕捉到這個能源空白,隨即組建三峽能源集團,在三峽庫區鋪設天然氣管道。此后,三峽能源集團不但牢牢把控三峽庫區這塊市場,還將天然氣管道進一步鋪到了湖南。
直到2004年,譚傳榮到北京發展,結識不少能源專家,又得到另一個重大訊息——目前我國煤層氣儲量跟天然氣差不多,達到36.8萬億立方米,而其年開發利用量卻不足20億立方米!顯然,能源、環保和安全,都是關系國家安定的大事。中央高層不僅把開發煤層氣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更已將實驗場圈定在山西沁水盆地。
沁水盆地是世界上儲量最大的高煤階煤層氣田之一,探明煤層氣地質儲量6.85萬億立方米,占全國總儲量的23%。照規劃,2010年,沁水盆地煤層氣產能可達33~39億立方米。但受輸送環節限制,大部分已建成的氣井被封閉,還沒有投入排采。
為了將沁水盆地的煤層氣盡快送出去利用起來,國家規劃了兩條輸送管道:一條連接西氣東輸的大管線,另一條從山西端氏出發,經晉城,最終到河南博愛。前一條管道由巨頭中石油負責,很快就緊鑼密鼓地籌建起來;可后一條由中聯煤集團負責的管道,卻遲遲不見動靜。
譚傳榮由此進一步打聽,原來中聯煤是由中煤集團和中石化組建的合資企業,2003年拿到這條管道項目,但直到2006年都遲遲沒有動工,在此期間國家能源局領導、山西省有關領導多次親臨現場考察,仍是毫無進展。
奇怪,這么好的項目,為什么竟陷入停滯不動的尷尬局面?譚傳榮立馬趕赴山西實地打探,這才發現其中牽涉到各方利益,形勢極為復雜。
一是中煤、中石化兩股力量在合資企業內并沒有合成一股力;二來能源大省山西素有地方保護主義情結,不愿能源出省;三則管道線路途經40多個鄉鎮,大型國企不可能放下身段到基層逐一突破。
看上去,這似乎是個死結。可面對煤層氣帶來的巨大商機和重大意義,譚傳榮偏不信邪,“這么一個關乎國家戰略的項目,中央又這么重視,雖然阻力重重,但總不至于推不動吧?!”
恰在這時,他聽說中聯煤董事長接銘訓,正為這個項目被無限期推遲而犯愁。譚傳榮頓時眼前一亮,這不正是自己的突破口?幾經周折,他終于拜會了接銘訓。
身為巨頭的國有企業既然毫無作為,何妨讓眼前這個充滿激情的民營企業家試一試?初次見面,接銘訓就問譚傳榮:老譚,你能不能跑下來?
譚當場拍了胸脯:我有這個能力,我試試!
接銘訓接著說:那行,你繳300萬元給我當擔保,如果跑不下來,我就全部沒收。
300萬元保證金博得一個機會?值!譚傳榮二話不說,交錢!
然而當時,在外界看來,身為國有巨頭的中聯煤都搞不定,你一個區區民營企業,就敢打包票十拿九穩?很多人甚至因此覺得,譚傳榮是不是瘋了?
妥協?!
譚傳榮自己究竟有多少把握?現在回顧,他坦承只有一半。其實當時他心里很清楚,僅靠自己一家民營企業是絕對不行的。既如此,何不把中央、地方、國企、民企都聯合起來,大家厘清股份、劃好利益、各取所需?
——說來易如反掌,實際做來卻難比登天。
2006年3月,譚傳榮正式從中聯煤手里接過管線項目。他把自己的這個想法告訴接銘訓,對方但笑不語,只是連連擺手。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似乎印證了接銘訓的判斷。當譚傳榮把各方企業代表召集起來開會時,每個與會企業都擺出一種不可一世的姿態,大家都在寸土不讓地討價還價,幾乎每個人都爭得面紅耳赤,話不投機就吵架,氣不過便扭頭走人——會場幾近失控。譚傳榮傻了眼。
怎樣才能將這些牛氣哄哄的“大爺”擰成一股繩?作為牽頭人,譚傳榮只得磨破嘴皮地跟這些大佬們逐個溝通、協調。然而在這個舉步維艱的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一個至關重要的現實:這些“大爺”是決不肯讓步的,但要大家聯起手來,就必須有人做出妥協。看來看去,這個妥協者只能是自己。
妥協嗎?不妥協,大家散伙,工程繼續遷延。不僅辜負了大家的信任,更斷絕了自己進軍國有壟斷行業的念想——譚傳榮似乎已經感受到那種極大的挫敗感。
妥協呢?自己吃虧,當然大家和氣。自己出錢出力把管道建起來,大家一起賺錢,自己只分其中一部分——憋屈!但做成一件利國利己的事,將會帶來一種強烈的成就感。
妥協還是不妥協?民企要想進入原國有壟斷行業,這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無奈選擇。身為商人,譚傳榮還算過這樣一筆賬:項目注冊資金需要兩三千萬元,總投資4個多億。而管道建成通氣后,保守估計每年將帶來八九個億的利潤,即便自己全部墊付注冊資金,隨后只占小部分股份,也能獲得不錯的投資回報。
也許不管是從情感上還是收益上,吃點虧、憋些屈,都是值得的。譚傳榮掙扎了一個多星期,最終選擇了妥協。他對記者說:“注冊資金全都是我墊的,你掛個名就可以占股份,我不要你出錢,你要權,我法人代表給你都可以。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認為把這個事情做起來,才是最重要的。也許這個最終感動了他們。”
原本爭執不休的各方利益集團終于聯手成立了山西通豫煤層氣輸配公司,其股權結構為:大股東是緊握資源的山西能源煤層氣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占股35%、隨后是占股26%的重慶三峽燃氣集團和占股20%的三峽國際能源,當然還不能少了占股10%的中煤集團,以及作為輸送目的地、占股9%的河南中原石油天然氣開發有限公司。
譚傳榮旗下的重慶三峽燃氣集團是唯一的出資方,但卻不是控股股東,他本人甚至也不是法人代表。中聯煤一位高層告訴記者:如果不是老譚多方周旋、曲折前進,如果沒有這種妥協與忍讓,這條管線不可能建起來。大家戲稱,老譚成了“老談”。
殊不知萬里長征,這才開始第一步。譚傳榮還必須在北京跑遍各個相關部委。雖然這個項目由國家能源部主管,但涉及的監管部門卻是一連串長長的名單:國土資源部、環保部、林業局、安監總局、水利部、鐵道部……這之間就有諸多矛盾和障礙,比如:國土資源部批礦的是一個司,批煤層氣的又是另一個司,一開始這兩個司的意見就不一致,搞得老譚一度不知所措。
怎么辦?譚傳榮急中生智,兵行險招,來了一計“死馬當活馬醫”。
2008年12月,管道開工儀式正式舉行,引來各方關注。外界看來,開工儀式張燈結彩,固然是一派喜慶。但事實上,這時的山西通豫根本不具備開工條件:各個股東還在明爭暗斗,資金還沒到位,管理上也存在一系列問題。
老譚究竟在打什么算盤?
他向記者吐露心聲:“我就是要通過開工儀式,讓輿論關注我們,把整個項目架上去,通過這一手段,迫使各項停滯的工作變得勢在必行,迫使股東們停止紛爭,好好想想怎么把事情辦成。”
中國的情況往往就是:當一個事情在國家層面被關注后,審批手續就順利多了。
關鍵時候,這就是老譚的不妥協。危急出智勇。在復雜的利益格局中,譚傳榮屢屢上演以超常規戰術取勝的好戲。
比如:由于手握能源的山西,已經形成一種我不求人、人必求我的老大心態。所以,這條把煤層氣從山西輸到河南的管道,在山西省內遭到重重阻礙。誰料,2009年6月,老譚并沒有把真正最初破土動工的地點選在氣源地山西,而是選在了輸送地河南。
老謀深算的他說:河南是能源需求方,巴不得早點供氣,所以一路大開綠燈。河南動工了,反過來把壓力轉給山西了,迫使山西不得不動工。
憤怒的時候要罵娘
采訪中,為了給記者講解得更清楚,譚傳榮一激動便站起來,拿起筆走到玻璃板前,邊畫示意圖邊給記者解釋這條大管線。顯然,56歲的他對這番事業傾注了滿腔熱血。
2009年夏天,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到山西考察煤層氣產業。回京送機時,已經登機的張局長透過機窗看到了送機人群中的譚傳榮。令在場所有人驚訝的是,張局長特意走下飛機,徑直走到譚面前,握住他的手說:“我知道,你非常不容易,辛苦了!”
老譚激動得熱淚盈眶,“這么大的領導,居然能體恤我們的艱難。”
可是重視歸重視,體恤歸體恤,感動歸感動,誰都清楚,這條路還很難。身邊朋友甚至提醒老譚,要他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他隨時可能成為悲情英雄。
這條100公里的管線橫跨兩省,途經5個縣區,20多個鄉鎮,80多個村莊,因為管道占地,山西通豫面臨不計其數的賠付,而且一提到利益,千奇百怪的狀況和問題便紛紛冒了出來。對譚傳榮來說,整個過程如同一次千難萬苦的西天取經。
比如,村民才不會管你什么國家戰略工程。村民的祖墳、田地和房屋擋住了管線的去路,無論賠多少錢都死活不讓挪,一些村民鉆進工程挖掘機里一躺就是好幾天,不讓工人們開工。
當下拆遷問題在中國又是敏感話題,稍微處理不好就會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譚傳榮和他的團隊只得放低姿態、耐心勸說,盡力在賠償上與村民們達成一致。
遇到老百姓的這種情況,從山村走出來的譚傳榮完全能夠理解包容。然而,跟目前中國很多事情一樣,在實際落實環節,大領導很著急,老百姓很著急,但就是中間的官員們不著急。不著急也罷,令老譚無比氣憤的是,一路上一些鄉鎮政府、村支部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使絆。
譚向記者回憶說:他和團隊一路下來,每天喝不完的酒,賠不完的笑臉。有好幾次,譚接到員工的電話說:老板,我們終于搞定了!那時電話那邊的員工已經喝得站不起來了。
更可氣的是,有些鄉干部、村干部假借民意,突然推翻之前已經簽好協議的賠償價格,坐地起價,其實背后干的是見不得人、假公濟私的勾當。
有一次,譚傳榮發現明明賠付給老百姓的是1200元,但真正到老百姓手里的,卻只有700元。老百姓不滿,就給工程添堵,其實中間的差價被鄉干部、村干部中飽私囊了。譚傳榮曾經指著一個鄉干部的鼻子罵娘:你根本沒資格當這個干部!
譚傳榮氣憤地說:有些基層干部動不動就拿領導架子來設置阻礙。我是在前線流血流汗的人,我也是有脾氣的人!
身邊人說,老譚是一個時刻準備獻身的人,他很瞧不起那些掌握一點權力卻打個人小算盤的所謂的領導。行伍出身的他身上有一股亮劍精神。
這種精神有時候是遇強更強。100公里的管線穿鐵路、穿公路、穿河流、穿森林,甚至撞上部隊的通信光纜。施工團隊想,此前什么田地、祖墳等,還可以通過跟老百姓商量和溝通來解決。這個可是雷打不動的部隊光纜啊,大家一時束手無策。
譚傳榮聞訊后心里暗忖:如果去找部隊談,要么吃閉門羹,要么漫天要價,管你國家不國家。遇到這種強勢群體,需要曲線救國,向當地政府尋求支持,再抓住出手的時機。
贏得當地政府支持的當天,譚傳榮立即下令來個先斬后奏,通宵達旦鋪管道。迅速完工后,再找部隊商量著將通訊光纜從一旁繞開。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譚傳榮的這場閃電戰合情合理,部隊也拿他沒有辦法。
穿越心中的太行山
2011年1月,山西沁南煤層氣田,寒風凜冽,冷氣刺骨。譚傳榮緊了緊大衣,目光順著口徑559毫米的輸氣管望向遠方。不久后,每年將有30億立方米的煤層氣,通過這條大管線往東100公里翻山越嶺、跨江過河,直抵河南省博愛縣。
在那些不眠不休推進工程的時間里,譚傳榮成天想著如何解決問題,時常晚上想得睡不著覺,有時候半夜想著村民們的賠付問題不能拖,越拖越出問題,竟會突然心慌得翻身起床。
此時再看這條他視之如命的跨省管線,回想這100公里的心路歷程,老譚忽然覺得一種激動在心中翻滾起來,難以言說。
曾經,中石油華北油田的老總專門找到譚傳榮,對他說:老譚,你這個管線不能再干了。
譚反問:怎么不干了?
這個老總懇切地說:你賣給我,不然很可能最終落得高價買、低價賣。
譚傳榮當場堅定回絕。
他向記者坦露:在內心深處,他把這條管線視為生命中最后一次拼搏。如果按照每年30億立方米的最大輸送能力,每立方米0.3元的利潤來計算,總投資4.6億元的管線,每年可帶來利潤9億元。按照這個業績,企業如果在中國大陸上市,市盈率達到20~30倍基本不成問題。
當然,中石油分公司老總預料的結局不是沒有可能發生。說不定哪天政策風向一變,管道所有權很可能全部收歸國有,老譚便成了悲情的出局者。
但是戰斗才剛剛打響,老譚對此不愿多想,不愿多談。采訪中他多次強調說:管道建成后對國家能源戰略意義重大,也是為中央領導分憂解難。不然,張國寶老局長也不會在已經登機后,又專門下飛機與自己握手。
——只身闖入國有壟斷行業的他,有一種尋求政治支持的強烈渴求,這雖然是迫于形勢,但更是一種夾縫中的生存智慧。
有一次,譚傳榮與中石化、中石油等幾個巨頭的代表一起到中央某部門匯報工作。大家把工作業績拿出來一比,幾個國有巨頭竟然遜色不少。中央領導當面數落了幾個國有巨頭,并希望他們多向民企學習。
不久前的一次國務院全國電話會議上,副總理張德江甚至專門提到譚傳榮的山西通豫。譚告訴記者:國家對煤層氣的開發心急如焚。每次礦難死人,溫總理就指示,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采取一切措施,然后副總理李克強就指出,要通過一種創新的體制來解決。
顯然,譚傳榮把央企、地方國企和民企整合成一支聯合艦隊,正是一種體制上的創新與突破。他向記者總結道:民企機制靈活,敢打敢拼,但要把事業做大,必須把國有企業的資源、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優勢整合到一起。
采訪接近尾聲,譚傳榮意味深長地說,山西有個古老的故事,不是“愚公移山”嗎?這是一種精神。沁水盆地往東100公里,翻越太行山,就是河南省。這個56歲的男人,正翻過了心中的那座太行山。在山那邊,他暢想著,他的管線從博愛輻射開來,直通鄭州、洛陽、焦作……再往后,南下湖北直到長江邊。 編 輯 彭 靖
E-mail:pzk@cais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