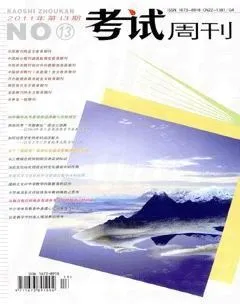讀或看?
長久以來,“通俗小說”、“游記連載”、“情感小說”、“連載小說”等都被簡單地認為是排除在文學領域之外的一種印刷品,也是一個很少有人研究并且沒有被嚴格限定的領域。大部分相關的此類作品都引來了隱晦的指責批評和消極負面的判斷。然而我們要補充一點,這類作品發展了起來,這些類型名稱也并沒有相互疊加其中的含義,而是分別代表了一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它們已經成為深入到我們意識中的范例詞匯,并實現了它們真正的價值。
人們總是將“文學”這個詞定義得過于官方和嚴肅,好像只有像巴爾扎克、福樓拜那些大文豪的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或是傳記才被列入真正的“文學”領域,而“文學”也不言自明,只包含那些在杰出的文人眼中具有長久價值的作品。但事實上,文學在發展,并出現了一些新的形式。我們稱其為“平民文學”。“通俗小說”這個詞匯也在很久一段時間內有著最廣泛的引申,然而它卻是模糊的,我們不能用一個模棱兩可的詞——“通俗”去定義這樣一個文化產物。
“類文學”,在法語中寫作“paralittérature”,我們先來分析一下這個詞,“para-”:前綴,意為“類—;副—”,“littérature”則是“文學”之意。所以“類文學”這個詞本身就包含了多種“正統文學”邊緣的文學作品。今天,在形成“類文學(paralittérature)”這個詞的同時,人們還試圖按照意識形態的和社會學的固有原因,根據文字的抒情配樂特點或敘事風格,將所有“類文學”的語言表達形式加以聚合。“類文學”的邊緣性其實與連載小說、偵探小說、愛情小說、流行歌曲及科幻小說等的本質是一致的,但在我們看來,這卻并不只是一種邊緣特征,也并非是一種文學性的缺乏。“類文學”存在于文學范圍之外,就像一種禁止的、忌諱的,甚至也許墮落的作品形式,但同時具有豐富的主題和觀念,而這些正是在“高級文學”中被壓抑的。
“真正的文學”一直在定義上被看作是沒有負面、沒有邊緣、沒有雜質的,而近期出現的“類文學”無疑重組了文學這個領域的和諧布局。事實上,“類文學”并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文學”的墮落形式,我更愿意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二者不能脫離對方而獨自生存。“文學”和“類文學”已經在異域和歷史的影響下成為一對不可分割的伴侶。
如今,“類文學”已被帶入到混雜的媒體網絡,我們不能忽視這么一個現象,那就是偵探小說的讀者同時也可能是犯罪圖片小說及同主題的電視連續劇的消費者。
二十年來,這個我們一直在試圖將其劃定界限的文字領域僅僅成為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軼聞或趣事的還原劑。然而在這個時代,我們卻驚訝地發現如此多的人都成為了同一種物品的消費者,那就是連環畫。根據表達方式的同質性準則來判斷的話,是否應該將“連環畫”從我們對“類文學”的研究中排除呢?很顯然是不能的,盡管這種文化產物有著以敘事為目的的句法結構,以及一個帶有符號學痕跡的形式。
連環畫是一種將文字和圖畫結合在一起的類文學產物,并且獲得了大眾普遍的接受。理論學家將它定義為:將繪畫的或其它的圖像及文字自主的并置,并將其組成片段,以用來轉化信息及(或)引起讀者的美學反應。對于一些人來說,連環畫混合了圖像和文本,而文本又多多少少以不自然的方式出現,就像歌曲中用來突出主題的聲部或是掛在桅桿上的燕尾旗。許多連環畫,比如非常經典的《小國王》,都反對這種“一部連環畫應當理所當然充斥著文字”的理念。還有一些人認為連環畫不止是一種表達方法,而應成為一種“屬性”。無論是業余的連環畫作者還是對連環畫的貶低者,對這種觀點都達成了共識。還應當注意到,那些認為連環畫應成為一種文學屬性的人還認為連環畫是屬于兒童和青少年的。
最初,連環畫只是在美國的報紙上以滑稽漫畫的形式流行,而在歐洲卻越來越局限于滑稽的內容和面向兒童的消費。在20世紀60年代,連環畫開始力圖脫離這個局限,并在70年代接連出現了一系列發展探索的試驗。然而在這個十年的末期,插圖式圖解小說和漫畫小說獲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說多種經典的圖文式文學占據了早期的市場,那么“連環畫”這個形式則在1980年在所有的插圖敘事式文學領域中,在人們的質疑中開辟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人們眼中已越來越被認可為一種正統的文學形式,盡管一些作家的尖刻批評曾造成這種文學形式的發展的緩慢。
在連環畫的巨大成功中,我們最耳熟能詳的當屬《丁丁歷險記》了。
丁丁的職業是一名記者,但他更像一個偵探。他勇敢、善良,不懼怕任何人和任何勢力,雖看上去瘦弱,卻表現出了驚人的力量,總能戰勝比他強大的敵人。他沒有任何權勢,卻可以輕松地應對各種看上去并不可能的事。在非洲、美洲,在印度,在中國西藏、上海,都留下了丁丁的腳印。他甚至還成為了在月球上探險的第一人。戴高樂曾說:“生活的坎坷能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