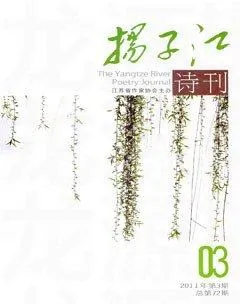歲月的裂紋(組詩)
一塊前清墓碑嵌在鄉村石橋上
他有良田數千,果園數百,貨棧幾十
以一顆茂盛的野心把藥材生意鋪到長江以北
最得意的一筆是
順治十二年,讓川中的黃蓮價格漲了三成
幾個嬌妻美妾在黃鸝鳴囀的四進庭院里
魚貫出沒。一群兒女在花園里玩耍,或者讀書
日后有幾個鯤鵬展翅,有幾個扶不上墻
他捐過一個官,不大不小,好看中用
并且與縣官州官關系良好,禮數周到
閑時邀幾個文人雅士到前院賞花,把酒吟風
在杜仲、麝香、白術、金錢草的氣味里
一張三尺宣紙上有驚龍嬌鳳游動
他的目光不時從筆端拿開,瞟一眼磨墨的
丫鬟
多少年來,一個人的名字飄零于前清的藥香
一本殘破家譜所記載不詳的部分
被一個詩人在文字的枯干上添枝加葉
若干年后,我們來到這條斷流的小河上
刮開時間淤積的泥層
刮開戰火、喪亂、盜墓賊的痕跡
看見他的墓碑鑲嵌在一座鄉村石橋上面
成為這座破敗簡陋的小石橋的一個部分
一位名動四方的前清藥材富賈
他的體溫和威儀就砌在這漫漶的鄉村時光里
但我還是認出了他
只是在我的嘆息聲中,他一聲不吭
石碑上,他煊赫的名字和生平
像一個遙遠的朝代模糊得幾乎無法辨認
不知何時開始,被踩在牛的腳下、馬的腳下
和一雙雙鄉下人的臭腳丫下
散落的稻草、牛糞,層層疊疊的足印
將一個人一生的光耀一層層掩埋
橋下的小河裸出一堆堆卵石。當年
他就是從這兒坐一只破渡船
到對岸那四十里地的縣城,掘下第一桶金
一個人內心的植物分布圖
他的一生中有一座高山。他生命中的植物,也是呈垂直分布
在低海拔地帶,他以常綠闊葉林的姿態,攤開寬大綠色的手掌
一只感恩的手掌,接受陽光和雨水的恩寵
他總是把冬天當作春天,讓愛情在一張碧綠的樹葉上放牧
他在一個少女眺望的眼中,寫下兩個詞:溫暖,濕潤
在他精神的地圖中,一座山脈在不斷生長,對應著一棵登山的樹的步伐
而往上,往上僅僅200米左右,就進入了落葉闊葉林。在那兒
他第一次感到了來自命運的涼意,冷颼颼地貼在脊背上
僅僅才是初秋,他的枝條就無力抓住那些綠色的愛情書信
他開始出賣生命中的那些珍貴的樹葉,他讓它們紛落,讓它們
在哭泣中去維護一棵樹虛假的尊嚴和價值。當一個人的靈魂
變成一棵光禿禿的樹,在山腰,他似乎才能夠從容地打量
昔日和身邊的落花、流水,保持一種高處的矜持和偉岸
他無法控制一種人生地理的宿命。再往上,往上
那是針葉林地帶。歲月凜冽的風吹進一圈圈的年輪
他把身子縮小,把夢想削成針葉的形狀。那種針葉尖銳的態勢
不是用以對抗廣闊寒冷的氣候。恰好相反,在切入肉體的風中
他避開了大面積的正面打擊,在蕭瑟中竭力保持水分和營養
……他仍然咬緊牙關往上,往上,在高海拔的山脊
他放棄了一棵喬木的站立姿勢,他必須是一棵低矮的灌叢
貓下身體,盯視著主峰,讓目光在酷寒中一寸一寸地攀升
在靈魂急遽墜落的高海拔地帶,那兒,是森林線和雪線的分野
在向上生長的目光中,他以植物的韌性頂逼著雪線
如同頂逼著一只企圖逾界的白色猛獸。他不能再犯錯
在絕境中,他堅持著,匍匐著,與千年皚皚的積雪怒目對峙
碎片:5月9日傍晚散步,在鐵道旁所見
紛紛揚揚啊,薄雪一樣紛紛揚揚
那一片片撕碎的信紙,那一片片撕碎的照片
那一片片被提速的時代
撕碎的心
從火車窗邊,飛旋著飄落下來
碎片,碎片
——殘破的晚霞和青春
我看不到她的臉。只看見一雙伸出的
白藕的手,在哀傷的返鄉途中
固執地撕碎一個初夏漸漸下沉的黃昏
我站在震顫的路基下,感到一陣更加猛烈的風
要把駛往遠方的一列火車和鐵軌
像紙一樣撕碎
在暴雨中點煙的人
一個地區猛烈的暴雨
壓在頭頂
把他逼得很小,小得像那頂斗笠
在翻滾的狂風中
他停下來,掏出火柴
哧的一聲
他用合攏的雙手緊緊護住火苗
他低側著頭,瞇縫著眼睛
熟練地點燃了一支煙
比閃電有韌性的火苗
照亮了他的左臉
一股嗆人的濃煙和咳嗽聲
在瘋狂的雨中隨即彌漫開來
在暴雨中大口大口吸煙的人
身上散發著雷電和煙草的混合氣息
他歪斜著身子
走上了水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