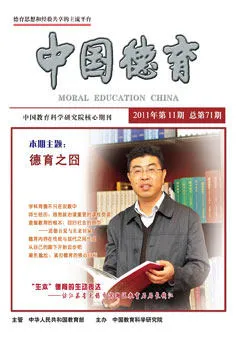德育內容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生成
[摘要] 在學校德育生活中,傳統道德是德育內容的重要構成部分,現代道德也是德育內容的重要構成部分。不過,由于時代與社會的復雜,德育內容陷入尷尬之中,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難以融為有機的統一的德育內容,二者呈現為一種緊張和沖突。如何化解這種尷尬,是德育需要面對的一個迫切問題。
[關 鍵 詞] 現代道德;傳統道德;德育內容
[作者簡介] 李長偉,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
人與動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道德的存在。進言之,人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自由使道德成為必需,理性使道德成為可能。不過,道德人的造就與道德共識的形成,根本上離不開教育,因為無論是自由意識還是理性能力都必須且能夠經由后天的有目的的培育。這就必然涉及一個無法繞開的教育問題:如果道德是可教的,那應該教什么呢?從教育理論的角度說,應該教什么取決于道德是什么;從教育現實的角度講,應該教什么取決于時代與社會的精神和氛圍。下面只從中國教育現實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
一、傳統道德是重要的
就當前的學校教育而言,道德是重要的,但傳統道德是重要的嗎?在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自由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看來,傳統道德是一種壓迫自由和進步的反動力量,應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一個無可爭議的史實是,自近代我國國門被轟開以后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對傳統道德的革命是時代和社會的潮流,從“五四”時代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時代的全面反傳統,都以革傳統道德之命為最高使命。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非歷史的存在,人無法與傳統道德決裂;人是歷史性的、尋根性的存在,傳統道德塑造著人性,人性內在地尋求傳統道德。倘若將傳統道德完全從社會、人與教育中革命掉,剩下的將是一片道德廢墟和普遍的人性虛無。保守主義者希爾斯在論說西方傳統時說:“沒有哪一代人創造出他們自己的信仰、機構、行為范型和各種制度,即使生活在現今這個傳統空前地分崩離析的時代的人也不例外。這一論點適用于現在活著的幾代人和整個當代西方社會。無論這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于想象力和創造力,無論他們在相當大的規模上表現得多么輕率冒進和反社會道德,他們也只是創造了他們所使用和構成這一代的很小一部分東西。”[1]50所以,希爾斯認為,一切人都“生活在過去”,“即使那些宣稱要與自己社會的過去做徹底決裂的革命者,也難逃過去的掌心” [1]64。社群主義者麥金太爾則針對自由主義者的反歷史的道德個人主義,提出人是故事性的存在的觀點,認為人們生活在宏大的故事之中,故事決定了人們如何行為。他說:“我從我的家庭、城市、部落和國家的歷史中,繼承了各種各樣的債務、遺產、正當的期望和義務。這些構成了我的生活中的特定成分和我的道德起點。”這意味著,敘事性的自我觀與個人主義的抽象性的自我觀明確區分開來,“因為我的生活故事總是內嵌于那些共同體的故事之中——從這些共同體中,我獲得了我的身份。我生而帶有一種歷史;個人主義模式中的那種試圖隔斷我自己與這種歷史的嘗試,就是破壞我現存的關系”[2]。 總而言之,無論是希爾斯還是麥金太爾,都強調傳統道德對于人性的塑造和教化作用。
回到中國的語境中,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的行為方式的獨特性究竟體現在那里?或者,中華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獨特的道德文化標識究竟是什么?這是一個不得不直面的嚴峻問題,因為它涉及個人與民族的“自我認同”問題與“歸屬感”問題,倘若不知道“我是誰”,那生存的意義、價值和尊嚴將蕩然無存。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回歸到中國的道德傳統,回歸到儒釋道那里去,是它們規定和塑造了我們的自我認同和歸屬感。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把老莊、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陽明、朱熹等人的道德思想和實踐完全從中國人的記憶和生活中抹掉,那將會是什么樣子?一個顯見的答案是,中國人將不再是中國人,“中國”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空洞的無意義的文字符號而已。也許有人說,綿延近百年的中國反傳統主義浪潮不是一直在革除傳統的道德文化,建立現代的新的道德文化嗎?而且,這樣的反傳統似乎也沒有導致社會道德秩序的崩潰和瓦解,社會仍舊在運轉,這證明了現代社會可以與傳統道德告別。但正如林毓生在《中國意識危機》中通過對反傳統主義者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個案解析,證明了“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并未如他們聲言的那樣做到和傳統徹底決裂。好像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始終翻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在中國某些文化傾向中所體現的某些傳統(如‘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已牢固地形成了反傳統主義者的觀點。”歷史學家陳旭麓在談到左的思潮時也談到:“‘左’的思潮拋棄了傳統,而在‘左’的思潮籠罩下形成的個人崇拜、造神運動卻來自傳統社會的土壤,我們既為拋棄了傳統而苦惱,又被傳統捉弄了而憤慨;被拋棄了的要回歸,被捉弄了的要解除,我們陷入了對傳統的拋棄和反拋棄、捉弄與反捉弄的困境”。[3]
敘說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應當意識到,在“教人做人”、“以道德社會化”為己任的學校德育中,傳統道德無法被拋棄,它必然成為學校德育的重要內容。進一步說,通過由教師對傳統道德的消化和傳遞,學生成為敘事性的存在,獲得生存的價值和自我認同。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當前的傳統道德文化的回歸熱潮,如學校教育中的“讀經熱”(很多孩子在幼兒園時就開始誦讀《三字經》和《論語》)以及傳統“禮儀熱”(如跪謝父母和老師),這證明了傳統道德在遭遇了一百多年的打壓后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強勢反彈。傳統道德從未徹底遠離中國人的生活和人性,它尋求的只是復興的時代機遇。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傳統道德在教育領域中的復興沒有任何問題。
二、現代道德是重要的
就當下的學校教育而言,現代道德是重要的嗎?筆者認為,現代道德是重要的。
首先,道德不是抽象的、與生活絕緣的存在,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能夠滿足人們過美好生活的內在需求。而對于何謂美好生活,古與今有著相當的不同,由此就產生了道德的差異以及現代道德產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對于美好生活,古代人有自己的獨特理解,他們強調按照有差異的“自然天性”生活,強調社會等級秩序的正當性,所以道德的等級性就非常明顯。中國古代人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以及對至上皇權的尊崇,就是明證。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新教改革運動以后,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自由、平等、權利成了美好生活的標準,“自然”與“等級”被人拋棄。就中國而言,自鴉片戰爭后開啟的中國的現代化不是自發的,而是西方推動的,所以西方所強調的自由、權利、平等的觀念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現代道德觀的建構。但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道德現代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天命”,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中國已經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由西方促動亦同時被卷入的現代性運動之中了。返回封閉的古代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非理性的,譬如說,與古代道德相連的“皇權社會”和“臣民社會”已經“煙消云散了”,強行回去,只會導致人們的普遍抵制。面對現代性的不可逆轉的浪潮,梁啟超基于傳統中國有私德和私民而無公德和公民的狀況,提出培育具有公德意識的“新民”,是必要的;同樣,“五四”一代反對傳統道德,提倡現代道德,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同樣,新中國成立后所提倡的“社會主義道德”,比如關心集體和他人,也是必要和必須的。這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是“小圈子倫理”,不具有公共性和民主性,不能適應現代生活。
其次,若從傳統而論,傳統并不僅僅指由古代孕育并流傳至今的古代傳統,也包括由現代孕育并流傳至今的現代傳統。這意味著,作為現代傳統之構成部分的現代道德,必將因為傳統自身的綿延和無法抗拒性而成為德育的重要內容。在這一方面,崇尚古代傳統但又客觀對待反傳統的現代文化的希爾斯說:“現代社會,尤其是西方現代社會,之所以一直在破壞實質性傳統,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它們已經以多種形式培育了某些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有害于實質性傳統的理想,而這些理想已經反過來成了傳統。人們一直用這些理想來督促統治者和公共輿論。”[1]384對國人來說,更多的是把傳統視為古典意義上的傳統,這顯然是不夠的。所以,學者高瑞泉評論道:“希爾斯不喜歡近代傳統,但并不因此抹殺近代傳統;不像漢學界的某些學者,因為憎惡‘五四’為代表的近代傳統,便一味指責‘五四’造成了傳統斷裂,拒絕承認中國近代一個多世紀以來也已經形成的某些近代傳統。它雖然可能不如西方近代傳統那么條貫有序,那么成熟,甚至還沒有從現實沖突中掙扎脫身,但它已經構成了當代中國人的共同意識和習焉不察的共同心理。”[4]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說,由于時代精神的變化,使學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識和能力,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現代道德對學生的重要影響。可以說,在德育內容中,現代道德不僅僅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根本的。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的“公民教育”在沉寂了幾十年之后又重歸人們的視野,也可以理解在德育的過程中對學生尊嚴、人格和自由的尊重和保護。
三、德育內容的尷尬:
傳統與現代的緊張
一方面,人是歷史性的存在,傳統道德是德育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是現實性的存在,現代道德亦是德育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人整體性的角度看,歷史感與現實感并不沖突,傳統道德理應與現代道德融為一個有機的和諧的整體,遺忘傳統而專注時下是不對的,但固守傳統而忽視時下也是不對的。當前,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并沒有融為有機的整體,而是充滿緊張和沖突,筆者稱這種現象為德育內容的尷尬——兩種道德都是重要的,但它們卻無法實現有機整合。這種尷尬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就傳統道德來說,它一方面是且應該是重要的教育內容,但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特質又使它作為教育內容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具體來說,中國的傳統道德文化不是一種大眾道德,而是一種精英道德,并且蘊含著濃厚的官僚政治色彩,其社會化主要依賴于政治制度。不過,中國自晚清以來一系列帶有斷裂性的激烈的社會變革尤其是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將中國社會逐步帶入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人的權利意識、民主意識、個人自主意識被喚醒,精英倫理日漸被大眾倫理顛覆,國家作為道德的立法者和實施者的角色逐漸遭遇挑戰和質疑,國家與道德逐漸呈現分離的態勢,這直接導致了傳統道德在教育領域這一重要的社會化途徑中的衰落。所以,盡管當前的學校德育強調傳統道德的重要性,也出現了“國學熱”和“讀經熱”,但傳統道德并未真正落實為德育內容。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傳統道德就失去了通過教育社會化的可能,只是需要知識人對傳統道德加以反思和“創造性的轉化”,尋求新的社會化基礎。
其次,就現代道德而言,它內涵的普遍性也遭遇了傳統道德所內涵的特殊性的“抵抗”,這種抵抗使得現代道德難以與傳統道德融為有機的整體。
現代道德之為現代道德的根本標識在于它的普遍性,因為它形成并服務于“開放社會”;而傳統道德之為傳統道德的根本標示在于它的特殊性,因為它形成并服務于“封閉社會”。雖然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普遍性完全取代了特殊性,事實上,盡管經濟開放與一體化在逐漸形成,但文化的封閉性與特殊性——文化是民族的——卻被人們加以強調。這是可以理解的,“文化就是洞穴”,布盧姆如是說。他分析道:“人需要為自己找個位置,需要給自己定位的意見,那些強調根基重要性的人強烈地表達著這種愿望。與外來者和睦相處的問題,不如成為內部人,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來得重要,有時甚至相互沖突。跟個人或民族的健康不相容才是極大的偏狹,而大開放的思想難免會讓文化解體。把至善與一己之善牢牢地綁在一起,拒絕承認它們之間的差異,以及對一個民族有著特殊意義的宇宙觀,這似乎構成了文化的前提。”[5]12由這種分析,可以理解現代社會中的“封閉”與“開放”之間的緊張,或者說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之間的緊張。
這一問題在今天的中國是突出的。眾所周知,自我國國門洞開,傳統的特殊的道德文化就長期遭受現代的普遍的道德文化的“壓迫”和“解構”,但伴隨著中國國力的極大提升,中國大國地位的逐步確立,傳統的民族的道德文化日益被人重視和強調。季羨林先生曾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紀,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將逐步讓位于三十年河東的東方文化”[6]。 事實上,這些年,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重新登上了歷史舞臺,而由西方推動的現代性運動與弘揚的現代價值觀遭遇質疑。人們相信,道德文化都是相對的,不存在超越的普遍的道德文化,即使存在,那實際也是西方的道德文化披上了普遍性的偽裝而已,西方人把自己的道德文化視為普遍,然后向全世界推廣,這是一種霸權主義。但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這個世界除了有特殊性,還有普遍性,因為人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沖動,有一種追求普遍真理和至善的需求。布盧姆說:“求善與忠誠之間的對立,給人生帶來難以消解的緊張。但是,對至善的認識和對擁有它的渴望,卻是教化人類的無價之寶。”[5]13其實,撇開這種哲學化的論述,審視當前,自由、權利、尊嚴實際已經內化到人的血肉之中,只要是一個正常人,都不會喜歡生活在沒有任何尊嚴的專制和極權社會之中。所以,我們不應僅僅基于民族的立場,拒絕普遍的道德觀。
總而言之,當前德育內容的尷尬已成為一個問題。如何反思和轉化現代道德與傳統道德,使二者有機地結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是今天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健全人格和健全社會的塑造和形成。
參考文獻:
[1] 希爾斯.論傳統[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