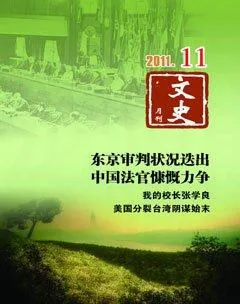方言害死人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調。
2005年,上海人掀起了“保衛上海話”浪潮,最近在廣東又有“普粵之爭”。
為什么要“保衛”且“爭”呢?就是因為方言也是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傳承千年,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
不過,除去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交流不暢等缺點外,在特定的歷史情況下,方言問題恐怕不僅僅是“爭”的問題,而且還極有可能成為血腥殺戮的“測謊儀”。
1911年,辛亥風云驟起。
據武昌起義者的回憶,當時,“革命黨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槍斃,很少有幸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
為什么旗兵“至死不講話”呢?因為旗兵大多是北方人,說北方官話,一開口就暴露了自己的旗人身份。而當時的革命黨人在“驅除韃虜”的教條下,對旗人任意殺戮。
當時的湖北咨議局曾遭不明射擊,這更引發了革命黨人對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
當時革命黨人在大街上任意攔下行人,盤查他們是否是旗人,方法是“那些頭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讀六百六十六”。也就是說,按照湖北方言,“六百六十六”要讀成“lóu be lóu shi lóu”,否則就要被殺頭。如果不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是不容易學的一模一樣的。
以發音判斷是否旗人的方法雖大致有效,卻并不科學。因為它會使那些發音并不怎么標準的人,遭受莫名的危險,即使本地人,如果在北方停留時間稍長也是一樣。何況,說北方官話的并不一定都是旗人。
還有,當時駐防武漢的旗兵包括旗兵家屬大多來自荊州,他們不講滿語而說荊州土話,所以但凡來自荊州一帶的人,其遭受的危險程度也很高。
當時,一個叫萬業才的革命士兵參加了起義當晚搜索旗兵的行動。他說:“午夜過后,我們聽見一處蘆葦沙沙作響。我們大聲喝叫:‘哪一個?快出來!’毫無反應。我們又喊:‘再不出來開槍了!’接著對準草動處開了一槍。果然草叢里爬出兩個人來,遍體泥污,渾身顫抖。我們問他:‘做什么的?為什么黑夜躲在這里?’一個不開腔,另一個嚇得結結巴巴,好一會兒說不成一句話來。從語音上判斷,顯然是個旗兵。
原來三十標的旗兵多半是從東北的滿族內征調而來,語音很容易辨別。天亮之后,將此二人送到軍政府處決了。”
八旗兵原本并不駐防武昌,只是因為清末新政,才被安排到這個省會城市的湖北新軍中受訓,結果遭遇辛亥起義,因為不會說當地方言,把小命給弄丟了。
無獨有偶。
民國初年,軍閥胡景冀的國民軍第二軍駐防河南。由于該軍源于陜西哥老會起義組建的民軍,以陜西人為主,成分復雜,又缺少政工人員的良好教育,所以《民國軍事史》中說該軍“軍紀之敗壞,國內罕見”,“倚之為骨干,就必然軍紀蕩然,成為擾民的害蟲”,這就使國民二軍成為河南民眾的冤家對頭。
后來,該軍與紅槍會在豫南血戰半年,西退時,河南紅槍會在邊界設卡捉拿第二軍的逃兵。
判斷是不是國民二軍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在地上畫一個圓圈,讓他說這是什么,凡是喊“圈”或者“屈圈”的人,就被認為是冀魯豫地方的人,便放過去,凡是操陜西方言喊“圈圈”的,紅槍會的人不由分說,上去就是一紅纓槍,解決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