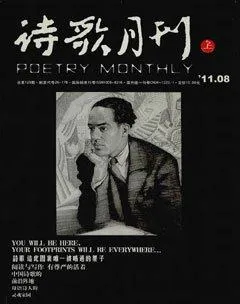丁小琪的詩(10首)
很多人都是這樣消失的
一個鄂倫春少女
從草原來到南陽 求學
要回內蒙參加高考了 臨行前
慕名前來找我學習聲樂
上了七節課 第二天
就要坐火車走了
她要先坐車到北京
再轉車去哈爾濱
然后去加格達奇
再坐很遠的汽車才能到達
一個少女 單薄的身子
要走很遠的路 我目送她走下樓梯
一出門 她就在夜色中消失了
很多人 都是這樣消失的
今生 也許再也見不到了
出手
這一天 還是來了
意料之中的
遲早要到來的
來的稍早些
比意料的 稍好些
沒有痛苦
沒有眼淚
眼睜睜看著一個人的消逝
消逝了
還會在別處存在
只要還活著
就很好
我要學習那些蟬
在危險來臨時
躲在暗處的家伙
舉起棒子
迅雷不及掩耳地
重重擊向我時
早已成了空殼
那天在牛鼻山
那天在牛鼻山
看遠處的城市
淹沒在燈火里
黑黑的牛鼻山
浮在上面
從山上走過
聽到他倆
躲在樹叢里
吃吃吃地笑
他們在笑什么呢
我們從旁邊走過
笑聲弱了些
再后來
我們走遠了
就什么也聽不到了
牛鼻山真的很像牛鼻
窄窄的 挺長的
走到牛頭處
就無路可走了
世界在這里
戛然而止
夜路
人們都去了哪里
一轉眼只剩下我一個人
街燈惺忪 黑夜更黑了
從教授家出來 沿著河堤走下坡去
越來越靜 突然 從左邊躥出來個黑影
尾隨著我 我停下 他也停下
我走快 他也走快
我跑起來 他緊追著
我從兜里摸出一張一百元面值
準備在他打劫我時 主動給他
他的速度很快 眼看著就追了上來
我停了下來 轉過身 驚悸地盯著他看
我想看清楚強盜長得是什么樣子
即便是死 我也該看清誰是兇手
他喘著粗氣停在我面前 怯怯地說:
把教授家的電話號碼告訴我 好嗎
我看到他的眼睛貓似地圓睜著
夜
就這樣 黑夜包圍了我
許多只黑手 鋪天蓋地的黑手
包圍了我 黑色之外
一些希奇古怪的想法
忽明忽暗 從我身體的不同部位亮起
一雙溫暖的大手 一棵搖曳的狗尾巴草
一杯酸奶 都可能成為這些想法的一部分
我要說的 是一只狗
寂靜中的狗 城府不深的狗
所有的窗子都閉上了眼睛
所有的喧鬧都閉上了眼睛
所有的欲望都閉上了眼睛
這只狗的叫聲 突兀地浮起
像游過水面的鴨 在夜色中
蕩起一層層漣漪
一根竹竿
早上醒來
坐在床上
我在想
用一根長竹竿捅過去
是否能捅到美國
婷婷剛脫下的那雙紅皮鞋
一條路
在27樓看遠處
一條土路
在那個村莊繞一圈
來到了城市
在舞廳里
我們的肢體
在光和影里
被分解 淡化
強切光 從頂部傾瀉
鐳射光束 黑夜裂變
多瑙河醉心的藍
我的腳
要學會適應這樣的節奏
左腳抬起 準確地楔入
舞伴兩腿的間隙
構成一個旋轉
再楔入 再旋轉
強弱交替的節奏中
不斷地拔出雙腿
在流光溢彩中
深入淺出
那么多腿
粗的 細的
長的 短的
直的 羅圈的
重復著同樣的動作
多瑙河之波
把我的面孔和胸脯
高高浮起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這持續的旋轉 滑翔中
這些腿 就要飛了
就讓我呆在枝頭吧
就讓我呆在枝頭吧
我要和秋天的落葉
一起 落 下……
五蛋的車從臺階上栽下來了
五蛋的車栽下來之前
他可以把方向盤左打
從寬闊的馬路上開過去
就在他打方向盤之前
就在他踩剎車之前
有個人叫了一聲:五蛋!
五蛋的車就栽了下來
五蛋是大學的體育教師
足球教練 五蛋不姓五
五蛋姓馬 叫馬曉寧
人們都不知道 一直叫他五老師
后來 五蛋說
他有四個姐姐 排行老五
他是鄉下家庭最盼望的孩子
母親生到第五個才等來的男孩子
村里人都叫他五蛋
就在剛才
有人叫了一聲:五蛋!
五蛋的車就從臺階上栽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