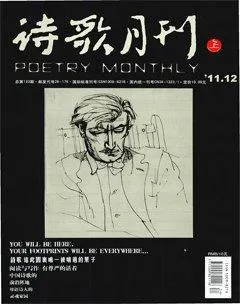舞在敖德薩(節(jié)選)
作者的禱告如果我為亡者說話,我必須離開我身體里這只野獸,我必須反復(fù)寫同一首詩,因為空白紙頁是他們投降的白旗。如果我為他們說話,我必須行走于我自己的邊緣,我必須像盲人一樣活著,穿走于房間而不碰倒家具。是的,我活著。我可以過街,問:“現(xiàn)在是哪一年?”我可以在睡眠中跳舞,在鏡子前笑。甚至睡眠也是一種禱告,上帝我將贊美你的瘋狂,以一種不屬于我的語言,談?wù)撃菃拘盐覀兊囊魳罚俏覀冇蝿佑谄渲械臉非R驗闊o論我說什么都是一種請愿,我必須贊美最黑暗的日子。舞在敖德薩(一)
在一座被鴿子和烏鴉聯(lián)臺統(tǒng)治的城市,鴿子蓋滿了主要地區(qū),烏鴉占據(jù)了市場。一個耳聾的男孩數(shù)著鄰居后院里有多少只鳥,然后造出一個四位數(shù)號碼。他撥打這個號碼,在線路上對著聲音表白他的愛。
我的秘密:四歲時我耳聾了。當(dāng)我失去聽力,我便看見聲音。在一個擁擠的電車上,一個獨(dú)臂男人說我的生命會與我祖國的歷史神秘地聯(lián)在一起。但我的祖國不見了,它的公民在夢中相遇,選舉。他沒有描繪他們的面孔,只有幾個名字:羅蘭,阿拉丁,辛巴達(dá)。舞在敖德薩(二)我們生活在未來的北面,日予以孩子的簽名打開信箋,一枚桑果,一頁天空。我祖母從涼臺上扔西紅柿,她掀動想象,如同從我頭頂扯起一床被毯。我畫我母親的臉,她知道什么是孤獨(dú),她把死者同黨派一樣藏于土地里。夜晚為我們解衣{我數(shù)它的脈搏),我母親跳起舞來,她用桃子,烤制的食物,填滿過去。對此,我的醫(yī)生笑了起來,他孫女撫摸我的眼睛——我吻她膝蓋的背后。城市在顫抖,一只鬼船出航了。我的同學(xué)為猶太人取了二十個名字。他是天使,他沒有名字,我們摔跤,當(dāng)然噦。我祖父坐在拖拉機(jī)上與德國坦克對仗,我提一滿箱布羅茨基的詩。城市在顫抖,一只鬼船出航了。夜里,我醒來小聲說,是的,我們曾經(jīng)活著。我們曾經(jīng)活著,是的,別說那是一場夢。在當(dāng)?shù)毓S,我父親抓起一大把雪,塞進(jìn)我嘴里。太陽開始了日常敘述,染自他們的身體母親,父親,舞著,移動著黑暗在他們身后述說。這是四月,太陽洗刷著涼臺,四月。我復(fù)述我的故事,光線浸蝕我的手:小書本,去那個城市吧,不要帶著我。
音樂療法——致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哀歌[一位現(xiàn)代奧菲斯:他被送往地獄,再也沒有返回,他的遺孀搜遍了地球六分之一,她緊緊抱住裝滿他詩歌的碟子,夜里背誦,以防止憤怒女神帶著搜查令發(fā)現(xiàn)了它們。]當(dāng)這頁紙上仍然還有一些光線時,他帶著妻子穿著陌生人的外衣逃跑了。衣服上有些汗味;一只狗在追蹤,舔他們走過和坐過的地面。在廚房,在樓梯,在馬桶上,他將向她展示通往沉默的路,讓收音機(jī)自言自語。他們關(guān)掉燈,做愛。但鄰居有望遠(yuǎn)鏡,而他也看,灰塵落在眼皮上。這是1930年:圣彼得堡是一只冰凍的船。大教堂,咖啡館,他們搬遷到涅夫斯基大道,因新政權(quán)找他們的茬。[在克里米亞,他召集富有的“自由派”,對他們嚴(yán)厲地說:在審判日,如果他們問你是否理解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就說“不”。是否喂養(yǎng)了他?——你必須回答“是”。]我大聲朗讀我在地球上的生命之書,然后坦白,我愛柚子。廚房里:人們舉杯,品嘗伏特加;香腸。我,一個穿白襯衣的男孩,用手指蘸甜蜜。母親為我擦洗耳根。我們說了許多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事情,也就是說這是八月,八月!樹上的光影,充滿憤怒。八月將語言填滿我們的手心,聞起來像煙熏。此刻,記憶,倒啤酒,把鹽撒在杯口,給我寫信的人,拿去你想要的吧:一枚金色的硬幣,置于我舌頭之上。(云彩的弟弟走來,他穿深綠色的褲子,未刮胡子。大教堂里:他雙膝跪下,祈求“幸福”他的話語在地板上,死烏的骨骸。)我愛過。是的。我洗手。述說我對大地的忠貞。而此刻死亡這美男子,正數(shù)我的手指。我逃亡,被捕,再一次逃亡被捕,再逃再被捕:在這首歌里唱歌的是一個瓷娃娃。詩歌就是自我,而我抗拒這個自我。在別處:圣彼得堡像一個迷失的青年站立在那里,它的教堂,船只,絞刑架加快我們的生命。[1924年夏天,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帶著年輕的妻子來到圣彼得堡。娜杰日遲正像法國人所說的“可愛而迷人”。一個偏執(zhí)狂?他當(dāng)然是。他把一個抱怨他沒有發(fā)表作品的學(xué)生掀倒在樓梯上,吼道:薩福發(fā)表過?耶穌基督發(fā)表過?]詩人是一種聲音,我說,就像伊卡洛斯墜落時自言自語。是的,我的生命如風(fēng)中的碎枝擊打北方的大地。此刻我寫一部雪的歷史,燈光沐浴著劃過紙面的船只。但在某些下午,詩共和國開啟,我害怕沒有生活過,死了,沒有活夠以將這狂歡化為元音,傾聽清晰的圣經(jīng)般的演說拍打出浪花。我讀柏拉圖,奧古斯丁。讀他們音節(jié)中的孤獨(dú)而伊卡洛斯不停地墜落。我讀阿赫瑪托娃,她豐韻的重量將我綁在大地山坡上的堅果樹呼吸著干燥的空氣,日光。是的,我活過。國家把我的腳吊起來,我看見圣彼得堡的女兒,天鵝,我學(xué)會飛鳥陣列的語法,永遠(yuǎn)落在普希金大道,而記憶坐在角落里,用海綿將我擦掉。我犯過錯,是的,我在床上將政權(quán)與我的女友相比較。政權(quán)!一只傲慢理發(fā)師的手在肌膚上剃干凈。我們大家圍著他歡快地跳舞。[他坐在椅子的邊緣,大聲夢想美妙的晚餐。他不在辦公桌上,而在圣彼得堡街頭,寫詩;他熱愛這樣的意象:公雞用他的詩撕開雅典衛(wèi)城墻下的夜晚。關(guān)在牢里時,他拼命在門上敲打:
“放我出去,我生來不是坐牢的。”]生命中有那么一兩次,一個男人像蘋果一樣被掰開。剩下的是聲音撕開他的身體一直撕到中間。我們看見:淫穢,驚駭,泥土但有種形式的快樂總是多于一種沉默。——在此地與涅夫斯基大道之間歲月,鳥兒一般地,伸展,——為他祈禱吧,那為面包和土豆而活著的人一群狗在每一條街上背誦他的詩。是的,數(shù)一下”三月”,“七月”用一根線把他們織在一起——是時候了,上帝,用這些詞語緊緊壓住你的沉默。——故事是這樣說的,一個人逃亡又被抓進(jìn)夜晚的書寫里:做愛之后,他坐在廚房地板上,睜大眼睛講述上帝的空虛,而我們就是由這樣的意象構(gòu)成的。——他失業(yè)了——在銀餐具和灰塵中,親吻妻子的脖子,直到她肚子抽筋。人們會想到一個小男孩用舌頭將音節(jié)鋪展在女人的皮膚上:這些詩句完全由啞音縫起。[娜杰日迭從書上抬起頭來說:奧西普、阿赫瑪托娃和我站在一起時,曼德爾施塔姆突然欣喜地融化了:幾個小女孩從我們身邊跑過去,想象她們自己是馬。第一個停下來,不耐煩地問:“最后那匹馬在哪里?”我抓住曼德爾施塔姆的手,不讓他走過去;阿赫瑪托娃也是,感覺到危險,低聲說:“不要跑開了,你是我們最后的馬。”]——我死去時,赤腳走遍我的祖國在這里冬天筑起最強(qiáng)大的孤獨(dú),拖拉機(jī)闖進(jìn)半人半馬王國,馳騁于白話語言:我二十三歲,我們生活在繭中,而蝴蝶交配。奧西普把手指伸進(jìn)火里,他早起,穿著拖鞋四處走。他寫詩很慢。祈禱者們在屋里倒下。飛蛾在窗外看他。當(dāng)他的舌頭劃過我的皮肉,我看見他的臉在下面,我看見痛的清晰——娜杰日達(dá)如是說,她站在橙色的光線里。雙手安詳,自言自語亞伯拉罕、伊薩克、雅格布的神啊在你的善惡尺度上,放一盤溫暖的食物。我丈夫從沃羅涅日回來時,嘴里藏著一只銀勺——他夢到,獨(dú)裁者沿著涅夫斯基大道跑像狼~樣追蹤他的過去,一只睜眼睡覺的狼。他相信人性。他無法將自己從圣彼得堡中拉回,治愈。他在心里默誦死者的電話號碼。哦他低聲說!——未說出的話語變成島嶼的痕跡。他煽了托爾斯泰一耳光,好啊。他們抓走我丈夫時,每一個字都消失在書本里。他們看著他說話,元音上有牙齒的印記。他們說:你,必須讓他獨(dú)處因為他背后已有石磚囤積,落下。[奧西普有著濃密的睫毛,直到他面頰的中央。我們走在普利西斯坦卡大街上,談?wù)撌裁次乙延洸磺濉N覀冝D(zhuǎn)到果戈理大道,奧西普說:“我已為死亡做好準(zhǔn)備。”他被逮鋪時,他們搜索詩,弄得滿地都是。我們坐在一個房間里。墻的另一邊是一個鄰居家里,有人在彈夏威夷吉他。我親眼看見搜查者發(fā)現(xiàn)了《狼》,拿到奧西普跟前。他微微點頭。離開時他親吻了我。他是在早上七點鐘被帶走的。]在視野的每一個盡頭,曼德爾施塔姆站立著,手里捏著土塊,扔向路過的行人。你會認(rèn)出他的,主說:——他討厭沙皇村,馬雅可夫斯基說:“別念你的詩了,你不是羅馬尼亞交響團(tuán)。”和諧是什么?它糾結(jié)又被解開;娜杰日達(dá)說。雪落進(jìn)她身體里,她聽到全身都是小雞的聲音。娜杰日達(dá),她的是與否總是難以分辨。她跳舞,裙子卷在大腿間,光線加強(qiáng)。在每個房間的四個角落里:他與她做愛,耳垂,眉毛,日子編織成結(jié)。他穿過她的廚房,撫摸家具,頭上有一個小螺旋槳隨著他說話而轉(zhuǎn)動。室外,一個小男孩對著樹撒尿,一個乞丐訓(xùn)斥他的貓——那個1938年夏天——墻壁熱烘烘,日頭打在城市的磚墻上,“這個愛屈服于威權(quán)的城市。”在每一個視野的盡頭,他用牛奶擦她的腳。她敞開身體,躺在他腹部。我們將在圣彼得堡相見,他說,我們已把太陽埋葬在那里。
旅行音樂家瑪麗娜·茨瓦塔耶娃㈠在每一行的奇怪音節(jié)中:她醒來如同一只海鷗,撕裂于天地之間。我接受她,與她站在一起,面對面。——在這個夢里,她穿著裙子,像一只帆,在我身后跑,我停她也停。她笑著,孩子一般自言自語:“靈魂=痛苦+其它所有一切。”我笨拙地雙膝跪下,不再爭吵,我需要的只是一扇人間的窗戶在以我生命為屋頂?shù)姆块g里。瑪麗娜·茨瓦塔耶娃㈢
在我耳聾的第一年,我看見她與一個男人在一起。她戴著紫色圍巾,半跳著舞,把他的頭抱在手中,放在胸前。然后她開始唱歌。我聚精會神地觀察她。我想象她的聲音有橘子的味道:我愛上她的聲音。
她是這樣一個女人,像個共謀犯一樣發(fā)出矛盾的訊號。“別吃蘋果核,”她威脅我,“吃了蘋果核,樹枝會長在你肚子里!”她摸我的耳朵,用手指撫摸。
我對她丈夫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在一輛開動的汽車上死TULm9ECFg4/CgW5FOYAIkb1JTit9cHJxfg4vHfOzyho=于致命的心肌梗塞。她臉上沒有抽搐,看著她的臉,我明白了悲痛的尊嚴(yán)。從葬禮上回來后,她脫下鞋子,赤腳走在雪地里。贊美……而有一天會有一些黃檸檬透過半開的大門朝我們閃爍這些金色的陽光號角在我們空曠的胸部傾吐他們的歌聲。贊美我們匆忙地離開敖德薩,忘了公寓前那只裝滿英語詞典
的箱子。我來到美國,沒有帶字典,但有幾個詞語存
留下來:忘記:光的動物。一只船抓住了風(fēng)和船帆。過去:手指來到水的邊緣,舉著燈盞。水可疑地冷。許
多人站在岸上,最年輕的把帽子拋向空中。理性:將我與瘋狂隔絕的不是隔絕,真的不是。一個巨
大的水族館,裝滿了水草,烏龜,和金魚。我看見閃
光:移動,刻在額頭上的名字。快速的笑她傾身過來,受騙了。我喝得太快。死:進(jìn)入我們的夢中,死者變成沒有生命的物體:樹枝,茶杯,門把。我醒來,渴望我也帶著這般的清晰。時間,我的孿生,拿去我的手穿過你城市的街道:我的日子,你的鴿子,在搶面包屑——一個女人在夜晚要我講一個結(jié)局圓滿的故事。我沒有。一個難民,回到家變成鬼尋找曾經(jīng)住過的房子。他們說——我父親的父親的父親的父親是一個王子同一個猶太女孩結(jié)婚違背了教會的意愿和他父親的父親的父親的意愿。失去了一切渴望失去:地產(chǎn),船舶隱藏這個戒指《他的婚戒),這個戒指我父親交給我哥哥,然后拿走。又給他然后拿走,匆忙地。在家庭相冊里我們端坐著如同學(xué)生服模特而破壞,像一堂講座,被推遲。然后母親開始跳舞,重新排列這個夢。她的愛很艱難;愛她卻簡單,如同把桑葚放入嘴里。哥哥的頭上:沒有一絲白發(fā),他唱歌,唱給他1 2個月大的兒子聽。而父親唱歌,唱給6歲的啞默。這就是我們?nèi)绾紊钤诘厍蛏希蝗郝槿浮:诎担粋€魔術(shù)師,在我們耳朵后面找到棲身處。我們不知道生活是什么誰給的,現(xiàn)實覆蓋著厚厚的渴望。我們放在嘴唇上,飲下。我相信童年,一個數(shù)學(xué)試題的故土歸與不歸,我看見——岸邊,綠樹。一個男孩從街上跑過,像一個迷路的神光線落下,觸到他的肩。記憶,一支古老的長笛,在雨中吹晌,狗睡去,舌頭半懸在外面;生死之間二十年我在啞默中穿行:1993年來到美利堅。美利堅!我把這個字放在一張紙上,這是我的鎖孔。我看見街道,商店,騎自行車的人,夾竹桃。我打開一個公寓的窗戶說,我曾經(jīng)有過主人,他們在我之上呼嘯我們是誰7為什么在這里?他們提的一盞燈籠仍然在我的睡眠中閃耀——在這個夢里我父親呼吸仿佛一次又一次點燈。記憶啟動舊引擎,開始移動而我以為樹木在移動。沾了土的紙角上我的老師在行走,走出一個聲音他在手掌上磨擦每個字:“手向泥土和碎玻璃學(xué)習(xí)你不能想出一首詩來,”他說“要看光線硬化成字句。”我出生在一個以奧德修斯的名字命名的地方我不贊美任何國家——伴隨著雪的節(jié)奏,一個移民的笨拙單詞墜落成語言。而你要一個結(jié)局圓滿的故事。你的孤獨(dú)拉響了琴音,我坐在地板上,看你的嘴唇。愛,一只腿的鳥,我幼時用四毛錢買回,然后放飛現(xiàn)在又回來了,我的靈魂在恣意煽動的羽毛中。哦烏的語言沒有訴苦的詞匯!——陽臺,風(fēng)。這就是黑暗怎樣用小指頭畫我的肖像,我已學(xué)會像蒙塔萊那樣看待過去神的隱秘念頭降落在一個孩子的鼓點中穿過你,穿過我,穿過檸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