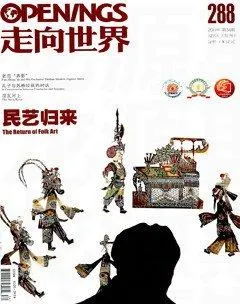魯迅當年的慨嘆
魯迅先生寫過一篇雜文,題目叫《上海文藝之一瞥》,是當年魯迅先生對上海文藝現狀發出的慨嘆。它其中寫到:在那個年代上海有一份畫報,叫《點石齋畫報》。“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而影響到后來也實在厲害。”“神仙人物,內外新聞,無所不畫,”然而“他畫‘老鴇虐妓’,‘流氓拆梢’之類,卻實在畫得很好的,我想,這是因為他看得太多了的緣故。”先生接著說:“小說上的繡像不必說了,就是在教科書的插圖上,也常常看見所畫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視眼,滿臉橫肉,一幅流氓氣。”“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在很受著這‘才子加流氓’式的影響,里面的英雄,作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頭滑腦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曉得怎樣‘折梢’、‘揩油’、‘吊膀子’的滑頭少年一樣。看了之后,令人覺得現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
可見當年上海的這一份畫報,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審美趣味。“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魯迅先生那一刻是憤怒遠多于幽默的。
今天看,出現幾個歪戴帽子的孩子并沒有什么不正常不可以,但問題是這樣的孩子不能是標準,更不能是前提——不歪戴帽子連做個孩子的資格都沒有了,這就荒唐可怕了。
魯迅先生當年的慨嘆、郁悶,今天看又是如何?
魯迅當年其實把今天的許多奧秘都說盡了。魯迅的偉大就在這里。他的書三四十年前印得跟“寶書”一樣多,結果引起了后來的反彈,有人反而不想再讀了,其實這與魯迅先生無關。不讀魯迅的書可是個了不得的遺憾,因為魯迅sjgv9eYkaaxKlWj0gBS9eA==談到的好多文壇問題、文化問題、精神問題,是從人性的幽暗切入的,大多都能言中今日,人性中的許多問題過去和今天都差不多,表現出來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就是魯迅的偉大。他深入了人性的大層。今天流行的文學讀物又是什么?今天歪戴著帽子已經不算什么了,已經遠不夠刺激了,今天還不知要把帽子戴在什么位置上呢。
下流,無聊,何止是無厘頭,何止是幼稚淺薄,更何止是蒼白。不可忍受的是如此骯臟——有時候,許多時候,這些竟然變成了文學的前提。
中國在走向所謂的全球化的過程當中,有兩個東西長成了無所不能的可怕的妖怪:一個是金錢,一個是性。這種欲望是人性中的合理部分,它屬于每一個人,是人性構成中的基本部分。但是當它公然作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全部理由,作為精神游戲的規則和標準去強化,并成為評判是非的法則的時候,就成為一種暴力,很少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擋它。人欲統領一切,作為一個硬道理放在那個地方,這個世界就危險了。
《西游記》塑造了一個力大無邊的猴子。他由石頭里邊蹦出來,拿了一個棒子,無論是何等神圣權威,更不要說權力金錢,只要不順眼,揮棒就揍。可就是這樣的一位齊天大圣,他有一次遇到一個妖怪,還是要仰面長嘆——因為這個妖怪法力之大,可以讓“土地佬”們“輪流當值”——七十二變的大英雄此刻痛苦郁悶極了,把那一張毛臉仰望天空,說蒼天啊,怎么還有這樣的妖怪?
“土地佬”本來是一個命官,用現在的話說該是“守土有責”,卻轉而去給妖怪“當值”了。為什么?就因為這個妖怪非同尋常,太厲害了。所以,我們今天的處境,都面臨著一個無所不能的巨大妖怪,它已經讓許多的“土地佬”輪流當值了。說到文學,只是一個方面而已,更不堪言而已。
文學文化人士、專家,他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區別作品,因為他有可能把一般讀者感受不到的、文字縫隙里邊的奧秘挖掘出來,有可能把作家最有魅力的那一部分給擴大出來,以抵達輸送到最偏僻的角落——可是一旦為妖怪“輪流當值”了,還有什么好說的。從這個角度上講,可以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非常絕望。真實的情況是,我們已經看不到東方的魚肚白。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又可以非常樂觀——種種情形古已有之,亂七八糟的向下的東西,對人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們非常好的文學、非常好的文學家仍然在產生,并且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傳承,我們的精神生活不但沒有中斷,而且還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人性里邊還有另外一種有力量的東西,這就是向善和追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