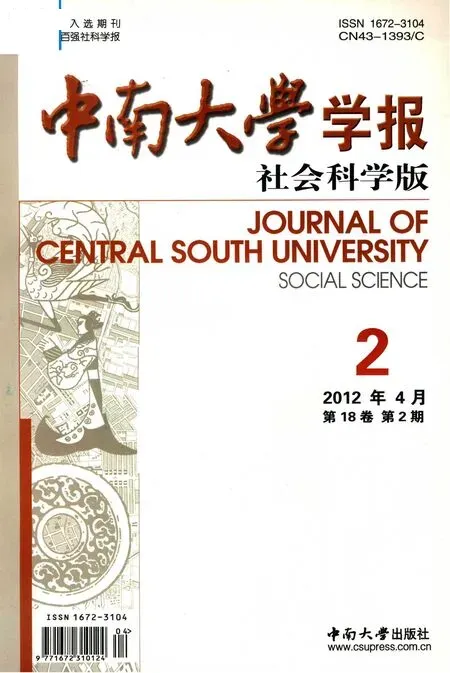微博客文化批判
歐陽友權,張婷
(中南大學文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自2009年年底微博客正式進入中國以來,便以其“零門檻”“高自由度”吸引了大量用戶,迅速覆蓋網絡市場,并在2011年出現爆炸式增長。截至2011年年底,我國已有注冊微博服務網站50多家,新浪宣布微博用戶達2.5億,騰訊稱已注冊微博用戶3.1億,各大網站注冊微博帳號累計達8億之多。不斷開發的針對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隨身客戶端技術,助推了“熱帖”不斷、熱點頻仍的微博客傳播,創造了2011年備受社會關注的“圍脖文化”現象。許多年度輿論熱點,如溫州動車事故、郭美美事件、免費午餐計劃、微博打拐、佛山小悅悅事件、藥家鑫案等涉及突發公共事件、公權力監督、公民權利保護、社會公德伸張等重要社會問題,都是通過微博傳播而引起社會關注的。
可以說,微博不“微”,力量巨大,出人意料也令人吃驚。微博的巨大力量是來自草根,來自社會人群金字塔的底端。微博客“技術平權”的理念似乎正不斷印證著尼葛洛龐帝1995年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提出的“讓弱小孤寂者也能發出他們的心聲”的構想。[1](7)微博所標榜的功能是:不管是精英還是草根、富人還是窮人、掌權者還是平民,只要注冊成為微博用戶,都可以自由發出自己的聲音。新浪微博宣布,人類已經不受時間、空間、物質、技術的限制,“隨時隨地分享新鮮事兒”;騰訊微博則以“你的心聲,世界的回聲”為口號,聲稱能給人們提供一個表現自我、成為焦點的夢幻舞臺。在全民“織圍脖”的時代,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微博的開放、自由、個性化等特征,足以為我們創造一個“草根話語權”“公共民主”“自由表達”的時代神話。然而,當我們把微博客當作一種公共空間和文化形態來考量時,卻不能不看到其背后蘊藏的話語中心化、“多數人暴政”和泛娛樂化本質。因而,對微博這一烏托邦神話予以理性祛魅,也許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認識微博文化的不同側面,調適微博輿情的價值取向。
一、技術平權——話語中心化批判
“人人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微博確乎給普羅大眾指明了一條通往話語權力中心的通關大道。不過在討論微博話語權時必須明確的第一個問題是:話語主體是誰? 發布微博首先需要有發布端,在有條件、有機緣上網“織圍脖”的人群中,可能會有城市低保戶、進城務工的農民、貧困山區的人們,不過這些解決溫飽的“弱勢人群”上網開博的比例并不大,因為他們中多數人很難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去擁有一臺電腦或手機,也難有時間與閑情去刷新微博,時下開微博、寫微博的主體人群仍然是那些在現實生活中本就生活優裕、擁有話語權力的人。
有研究者以微博的低門檻,即任何人可以自由進入,以及微博用戶中有眾多草根,他們通過微博發出自己的聲音,作為話語權下移的證據。他們認為,微博的流行使話語的平權化理念深入人心,每個人都可以借微博的力量發表言論,隨時、隨地且不受任何限制。微博將網民的話語權延伸到一個嶄新的平臺,在現實社會話語權力空間中處于弱勢地位的“草根”將有可能成為微博互動再建構的主導性力量。微博的出現不僅僅是傳播手段的變革,它同樣也是實現民眾話語權的“助推器”。[2](127)確實,表面看來,草根開博確實形成了一種“人人手握麥克風”的話語平權現象。但事實上這里忽略了微博話語中心化的第二個問題:可能擁有的“發言權”與實際掌控的“話語權”并不是一回事。
法國思想家馬歇爾?福柯曾多次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3](159)這就意味著要取得話語權得確保“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和“確立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這樣的話語權才會有實際的傳播效果。在傳統媒介如報紙、廣播、影視媒體中,其話語權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臨場“說話”的機會,而在可以無限延展的微博空間,衡量是否具有話語權的標準也要隨之改變。微博場域就如一個人人拿著麥克風的廣場,大部分聲音在發出之后除了被身邊的幾個人聽到外,都會湮滅在“眾聲喧嘩”的廣場中,無法大范圍傳播,只有少數人能憑著優質的“嗓音”使自己被眾人聽到,在這種情境下,話語權的關鍵在于誰的聲音能被眾人聽到,而是否獲得發言權、能否“發出聲音”則降到次要位置。
在微博世界中,個體的聲音被多少人聽到、產生多大影響最直接地體現在粉絲量上,粉絲量就是微博話語權分布的最重要指標。對粉絲量排名靠前的微博用戶的身份進行考察,也許可以說明微博話語權的分布情況。為此筆者對影響較大的新浪微博、騰訊微博、搜狐微博、人民微博中關注度排名前100位的微博用戶的不同身份類型進行了統計(見表 1),截止時間是2012年1月2日21時。
從表1可以看出,在這四大微博空間受關注度最高的用戶中,娛樂、體育明星所占比例最大,達到54%,他們通過向大眾曝光自己或身邊人生活的細節吸引更多的粉絲,微博平臺成為他們自我包裝、塑造公眾形象的工具。另外,包括傳媒從業者、作家、教育專家、經濟學家等在內的知識精英和政界精英、商業精英也占據著重要位置,在關注度前100位用戶中占35.75%。與明星、知識分子、政界精英、商業名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統計到的400名微博用戶中,普通平民只有18位,只占總數的4.5%。可見,在微博空間,各階層與團體擁有的話語權并不是均等的,占據話語中心位置的仍舊是那些在現實世界中本就處于主流中心位置的名人。
與傳統媒介的“推式”(push)傳播相比,微博傳播是一種“拉式”(pull)傳播,也就是說,微博用戶可以自由選擇關注對象,而不像報紙、廣播、電視、電影那樣,受眾接觸到什么內容由媒體決定。這里,我們需要注意一個重要的節點:在微博中存在著桑斯坦所謂“信息的蠶繭效應”,即人們只關注自己感興趣的人和事,只跟隨與自己有共同點的人,決定“微博用戶關注誰”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其認知與經驗。那些通過實名認證的名人們,他們在現實世界中本來就擁有較高知名度,只需把在現實社會中積累的高知名度移植進微博場域,很快就能得到粉絲的熱情回應。因此,娛樂明星、知識精英們就成了得到關注最多的微博用戶,也就是最有話語權的人,是他們牢牢占據微博場域的主導話語權。可以說,正是聚集在這些名人微博上的“粉絲”人群加強了名人微博的話語中心性,大眾與名人之間的話語區隔正是由他們對于名人的“仰望”造成的。人們不僅“自由地心甘情愿地”認同這種安排,而且積極投入到這一權力關系的構建中,時刻關注或追隨名人的一舉一動,甚至將其納入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它實際上并不合理。

表1 各主要微博中關注度前100位的微博用戶中不同身份所占人數統計①
微博的名人認證在擴大了微博影響的同時,也使微博喪失了獨立精神,成為名人們提升人氣的名利場和大眾窺視明星隱私的萬花筒和放大鏡。這時候,所謂微博的話語平權只是話語中心化的一種策略,是自由表達的傳媒技術為強化中心話語提供的一種權力認證,也是“名人加冕”以“合法”的方式將平民納入主流意識形態而做出的一種假意的妥協。當人們置身于微博空間,掙脫現實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羈絆,盡情宣泄內心或喜悅或悲傷或憤怒的情感時,微博似乎給了他們一個“自由言說”的夢幻世界,一種狂歡化的“第二生活”,然而不幸的是,蕓蕓草根在此能得到“發言權”卻得不到“話語權”,“表達自由”離他們的“話語中心化”相距甚遠;并且,當他們回到現實,卻發現自己“實際上仍不得不過著日益慘淡的生活”。[4](78)所謂微博帶來交流的去中心化、話語的平權化,看來都還只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幻想。
二、盲從圍觀——“多數人暴政”批判
“多數人暴政”又稱多數人暴力、群體暴政,②即以多數人名義行使的無限權力,并將這種權力凌駕于少數持異議者的利益之上,在微博上通常表現為“盲從圍觀”“語言暴力”和“媲美寡頭”的從眾心理。
人們常常以“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來詮釋微博帶來的民主進程。樂觀的研究者認為基于WEB2.0基礎上的微博,打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為人們突破民主參與的技術瓶頸提供了解決之道,為公民參政議政提供了新平臺,彰顯了商議性民主的核心精神,因而是在“近似地”實踐著協商民主的精神和價值。[5](1?4)應該說,這種觀點有其現實基礎,如微博的低門檻及高自由度,弱化了“把關人”的位置,其虛擬性又為人們的言論自由提供了“保護傘”,給用戶構造了一個寬松的信息環境;微博將字數限制在140字左右,篇幅短小,大大減少了人們思考的時間,其所具有的即時發布、即時留言、即時回復的功能,為輿論分布和群體交流創造了條件。
同時不得不看到的是,微博交流是一種“身體不在場”的交流,無論信息如何圖文并茂,始終有一塊電子屏幕擋在用戶之間,人與人的交流被簡化為人機交流,“人”成了一種虛擬的存在。這種匿名和虛擬的交流分解了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和統一,發言者擁有“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的自由權利,卻少了相應的責任擔當和監督機制。另外,140字的篇幅限定使微博信息過度碎片化,無法對事物進行深度解讀,更容易形成淺表化感性敘事。這一機制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們遇到任何事情都有即刻通過微博表達的強烈沖動,為了追求片刻的快感而一吐為快,這就使得平日里因種種束縛而處于“蟄伏”狀態的表達欲有了充分的釋放空間,人們的自我約束力出現下降,許多用戶不再像平時那樣認真而審慎,而是隨心所欲,脫口而出,很少考慮后果或承擔責任。如周立波發表“網絡公廁論”后,方舟子直言周立波為“小丑”,周立波則立刻反唇相譏,稱方舟子為“剩斗屎”“變態”“應該進精神病院”,最后演變成對立陣營之間的一場荒誕的口水仗。[6]南京農行槍擊搶劫案后,許多用戶把矛頭指向公安執法部門,出現諸如“警察靠得住,母豬都會上樹”“納稅人的錢都白養他們了”“如果他專殺貪官,我不僅不舉報他,還要贊助他”等“圍觀式”過激言論。
由于“多數人的暴政”表現為群體的情緒化,會誘導網民認同“人多勢眾”的力量感和“罰不責眾”的盲目性。如在“我爸是李剛”事件中,肇事者李啟銘的“官二代”身份迅速點燃了微博用戶的怒火,一時間,責罵、人身攻擊、侮辱的詞匯屢見不鮮,有網友對李啟銘、李剛、河北大學校長等人發起“人肉搜索”,李啟銘及李剛在央視公開道歉后,又攻擊其是在為博取同情而逢場做秀,并討伐央視的采訪為一場“央視與李剛的雙簧”。在司法機關進行審判之前,早有微博用戶對李啟銘及李剛進行了一次“審判”,這種情緒化的審判言辭犀利,不允許被告方提出任何申訴,并試圖以此影響司法判決,終而由從眾圍觀變成輿論暴力,讓原本正義的輿論走偏方向。又如最近的“肖艷琴事件”,在“肖艷琴遺書”發布之后,微博用戶幾乎是一邊倒地集體聲討前夫 J與“小三”Y,而當事實的真相揭開——肖艷琴并沒有自殺而是詐死,許多用戶深感自己被欺騙愚弄,轉而對肖艷琴發起攻擊。在這起事件中,許多微博用戶表現出盲目與輕信,他們的質疑大多來自網民沒有根據的推論以及對“小三”的偏見,因而輕易被人利用,偏離了理性的軌道,最后只能大呼上當,成為鬧劇的參與者和圍觀者。
由于微博用戶的良莠不齊以及微博傳播的迅捷廣泛,又沒有一個快捷準確的方式來驗證海量信息的真假,有時難免會使這里成為虛假消息滋長的溫床。我們不時看到,在微博論戰中為了占得上風,一些微博用戶不惜歪曲事實真相,乃至捕風捉影、斷章取義、移花接木、任意刪改的情況時有發生。如在2011年6月23日北京遭遇強暴雨天氣后,有網友通過微博發布城區各處積水的照片,更有網友將照片匯集起來,起名為“陶然碧波”“安華逐浪”“白石水簾”“蓮花洞庭”“二環看海”“機場觀瀾”等,稱為“新燕京七景”,這些微博包含了時間、地點、圖片等信息,看起來“證據確鑿”、真實可靠,很容易使大眾得到想象、暗示、確信并相互傳染,引起“圍觀”的同時被大范圍轉發,其實這些看起來“真實可靠”的照片并不真實,七張照片中竟有三張造假:水淹地下通道的照片在 2004年便已出現,大望路汽車被淹的照片為2004年7月10日新華社記者拍攝的蓮花橋被淹場景,首都機場飛機跑道被淹的照片則是挪用海南某機場被淹的照片。在這起事件中,微博用戶表現出感性、急躁、狂熱、盲從等心理,對真假的辨別力急劇下降。這種“多數人”的群體行為常常表現出排斥異議、極端化等特點,極易引發群體性突發事件,產生不良的社會效果,如網民可能被一時的沖動驅使,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對意見相左者發起人身攻擊、地域攻擊等等。占主導地位的多數派不是用理性說服的方式而是以其數量上的優勢將少數派的意見壓制下去,此時的民主絕不是我們所期望的真正民主,而只是一種“非理性的沖動”,是“多數人的暴政”對事實的歪曲和對民主的踐踏。
三、話題熱炒——泛娛樂化批判
有研究者指出,微博客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自覺地成就了以下幾個事實:培育良好的公共話語空間;推動“輿論”趨向理性;實現潛在民主。微博客讓虛擬的社群實現“面對面”交流,在網絡的匿名、異質和多元的公共場域,達到溝通理性。[7]但我們知道,公共領域是一個與公共政治緊密相連的概念,其前提是具有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公眾能夠在理性基礎上就公共利益問題展開討論。然而,微博從一開始就受到商業資本的操縱,從最開始的Twitter,到國內比較火熱的新浪、騰訊、網易微博等都是商業性的,誰也無法否認它們與“為它服務并利用它的工業之間有著極為曖昧的關系”,商家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經濟利益,千方百計地迎合大眾需求,而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更多娛樂元素。于是,商業元素的全方位滲透,讓微博的價值理性和批判意義讓位于泛娛樂化乃至“娛樂至死”,微博也就成為商家炒作和盈利的工具。
微博的泛娛樂化是通過主體身份認證和話題熱炒的方式實現的,由此形成的“吸引眼球”與“聚焦跟帖”是它屢試不爽的兩把利劍。小S開通新浪微博的第一天,單憑一張近照,就有 3萬多的點擊,2 000多人轉發,近3 000人評論;姚晨發布一條與寵物“巴頓”在一起的照片則引來1 700多人轉發,2 800多條評論。筆者隨機選取了新浪微博2011年12月5日至12月11日一星期的周話題榜(見表2)。

表2 “新浪微博”周話題榜(2011年12月5日至12月11日)
在這個排名前十位的周話題中,其中有六個是娛樂類話題,如2011電視劇華鼎獎,膝蓋中箭體,《我可能不會愛你》等,唯一可以稱得上嚴肅的話題是“冬季霧天,你那里的空氣質量還好嗎”。[8]新浪微博專門設置了名人人氣榜、達人人氣榜等,在人氣總榜中排名前十位的是:姚晨、小 S、謝娜、楊冪、蔡康永、趙薇、何炅、王力宏、李冰冰、NBA,無一例外都是熱門明星和熱門話題,抑或是有熱門話題的熱門明星,排名第一的姚晨的粉絲達到16 142 564人③,新浪微博還設置了“微話題”“微訪談”“微直播”“微活動”“名人堂”“媒體匯”“微博達人”“草根微博”“同城微博”等欄目,目的是把社會公眾的眼球一網打盡,至少是越多越好。這樣,當人們一打開微博,看到的便是各種生活談資、明星趣聞、娛樂八卦,如某位名人吃到一塊美味的蛋糕,買了一個名貴的背包,去了某個風景迷人的地方享受假日等等。于是,微博逐漸成為粉絲們集體圍觀偶像明星的陣地,娛樂精神也就成為微博的主要價值取向。
麥克盧漢說過,“一切媒介作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轉換事物的新視野和新知覺”,[9](80)媒介技術的影響不止發生在意見和觀念層面上,而且改變著人的感知模式和生活方式。微博的娛樂性裹挾了人們的思想,人的個性特點及原創精神在不知不覺中被淡化,主體性終將在這些娛樂轟炸中被無形消解,“人們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號的電子化傳輸中被維持分解和物質化”。[10](25)人們發現,他們已經變得無法自主地使用微博,而是熱衷于追求身體的快感和感官的刺激,微博公眾逐漸淪為文化消費的“被消費者”。在這種娛樂化語境的浸淫下,博主的目光會被應接不暇的娛樂信息所吸引,并被無限追蹤直至深陷娛樂泥潭而難以自拔。一旦微博娛樂與消費文化結盟,必將與它最初追求的“獨立”精神漸行漸遠。
微博客讓更多的社會群體登上網絡輿論的平臺,顯示出輿情的豐富和輿論的能量,深刻改變了社會輿論的生成機制。微博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深度關注、對社會公德的伸張、對政府公共治理的審視與監督,以及互聯網民間“自組織”力量的成長等,都具有開通民意、啟迪民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民主平權的“輿情革命”意義。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文化資本的深度介入、商業利益的幕后推動,以及爆炸式增長帶來的管理缺失,我國的微博客還存在數量飆升而功能失范、輿情復雜而監管乏力、眾聲喧嘩卻真假莫辨的現象,對微博的內容生產和輿情功能應當給予必要的規制與引導。開設微博客、用好微博客,還需要堅持“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基本方針,用價值理性調適技術平權,以人文關懷消解“多數暴政”,以自律與他律的結合規制“全民娛樂”背后的市場操手,用積極健康的文化力量創造網絡時代的文化微博和“圍脖文化”。
注釋:
①為方便統計,將“NBA官方微博”“快樂大本營”等歸入娛樂、體育明星一類,將“平安北京”“國家林業局”“南通公安”等政府機構官方微博歸入“政治人物”一類,將“新浪頭條新聞”“新周刊”“財經雜志”“《人民日報》求證欄目”等歸入傳媒從業者一類,將漫畫家“朱德庸”“照心”等歸入作家一類,其他不便于歸類的如“冷笑話精選”“微博名人”“微博搞笑排行榜”“新浪短信微博” “微博iPhone客戶端”“全球熱門排行榜”“微博Android客戶端” “精彩語錄”“星座小王子”“生活微百科”“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等統一歸為其他一類。
②“多數人暴政”一詞最早是法國人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將多數人的利益置于少數持不同政見者的利益之上便會形成“多數人暴政”。
③該新浪微博排行榜的截止時間是2012年1月17日。
[1][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M].胡泳, 范海燕譯.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2]周馨.微博——實現民眾網絡話語權的“助推器”[J].新聞世界, 2011(6): 127.
[3]王治河.福柯[M].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4][德]霍克海默, 阿多諾.啟蒙的辯證法[M].洪佩郁等譯.重慶: 重慶出版社, 1993.
[5]魏楠.微博——政治參與和協商民主的新陣地[J].山東行政學院學報, 2011(4): 1?4.
[6]周立波、方舟子微博互罵[EB/OL].http://tech.ifeng.com/internet/special/wangfeifangzhouzi/content-2/detail_2011_02/08/4578239_0.shtml, 2011?12?30.
[7]李琤.論微博客公共領域的建構[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6月.
[8]整理自“新浪微博風云榜”[EB/OL].http://data.weibo.com/top?topnav=1, 2011?12?11.
[9][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理解媒介: 論人的延伸(增訂評注本)[M].何道寬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1.
[10][美]馬克·波斯特著.信息方式[M].范靜嘩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