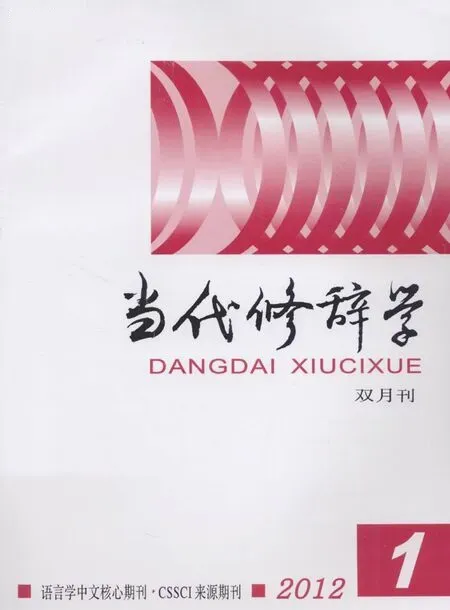言語交際當代語境觀:主客體與靜動態的新思考*
林大津
(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福州350007)
提 要 語境是否包括交際主體因素?語境是給定的還是通過主體選擇而建構的?有些學者力主語境必須排除交際主體,而絕大多數持有語境“主體建構擇定觀”的學者理所當然地將主體因素視為語境最為關鍵的主體部分。根據言語交際實際情況和研究者的有關論述,我們發現,即使持有主客分離觀的研究者也大都陷入自相矛盾的研究實踐,而一味強調語境動態建構觀的學者也很難排除語境要素的給定性。本文結論是:主體因素必須保留在語境要素中,語境作為一個集合體可以是交際過程中建構的,流動的,但其建構基礎必須假定語境要素的給定性。
一、引 言
語境對于言語交際之重要,無須贅述。但二十多年來國內語境研究都涉及一個模糊與矛盾的認識區間:語境是否涉及交際主體?語境是靜態給定的(given)還是動態擇定的(chosen)?這不僅是兩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而且主客體的分界與靜動態的分歧從本質上看可歸結為二者相互關聯而導致的一個結果,如果不結合起來考察,就無法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得出符合言語交際客觀實際的結論。有感與此,本文擬從修辭學和語用學視角,聚焦于“主客體”與“靜動態”討論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分析其成因,探究其矛盾,最后提出我們的新思考。
二、語境定義與語境構成要素:主客體矛盾觀
大量學術文本定義的“語境”,是一個抽象概括的“統一體”,如認為語境是“使用語言的環境”。這類概括是否失之空泛、是否科學暫存不議,幾乎所有研究語境的文獻在這樣的高度概括之后,接著就開始具體表述語境的構成要素及其層次。針對國內外研究語境的學者把言語主體之間的關系及主體的各種因素如交際雙方的關系和交際主體的身份、職業、經歷、思想性格等當作語境的一個要素,劉煥輝(2007:16-17)提出:
我感到把言語主體當作其賴以使用語言的環境來研究,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故在后來的書、文中明確主張把語境與言語主體區別開來。
劉煥輝(2009:61)重申了這一觀點:“在討論語境問題時曾多次提出要把言語主體排除在語境因素之外……把言語主體跟它賴以使用語言的環境混為一談,就連形式邏輯也講不通。”此前,鄭榮馨(2001:10)對語境“主客分離觀”也有過鮮明的表達:
將語言的使用者也包括進語言環境中去,就意味著語境自己把握自己,豈非不合情理?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將語言的說寫主體從語言環境中分離出來……否則,眾多因素交織混雜,很難將語言環境的理論論析透徹。鑒于上面的認識,我們給語言環境下這樣的定義:語言環境是與說寫主體有關的客觀環境。這一定義嚴格排斥語言表達主體的各種因素,與現在流行的解釋有原則的區別。
除了邏輯上的擔憂外,劉煥輝(2007:17)引入“言語行為”的概念作為附加論據:
如果我們認可胡范鑄教授最近提出修辭學的核心概念是“言語行為”這一見解的話,那么主體便是言語行為的主體,語境便是言語行為賴以進行的環境,二者不是同一性質的東西。
引文中提到的胡范鑄的修辭學“言語行為核心觀”,出處應是胡范鑄(2003)。劉和鄭兩位都非常重視邏輯問題,可我們研讀了胡范鑄(2003)后,卻找不到任何修辭學“言語行為核心觀”與語境研究必須排除言語行為主體的闡述或邏輯關系,有的只是以言語行為為核心的修辭觀該如何開拓研究新領域的闡述,尤其是如何構建言語行為的構成性規則(詳見下文)。我們的疑問是,從言語行為入手,修辭學研究就不能將交際主體納入語境范疇,即作為語境構成要素來研究嗎?
綜而觀之,語用學研究言語行為主要探討表達者如何表達語用意圖,接受者如何推斷語用意圖;修辭學研究言語行為主要探究表達者如何達到預期的交際效果,交際效果如何在接受者一方從可能性轉換為現實性。如此看來,圍繞言語行為的語境觀可以是:
語境是影響表達者實施言語行為和接受者感受表達者言語行為的所有因素。
我們知道,“知己知彼”是任何帶有目的性言語行為所必須考慮的因素,而“知己知彼”就是考慮交際主體。如果說“知彼”僅涉及相對于言語表達主體的接受對象,尚未陷入“主客相混”的邏輯麻煩,那么“知己”是否必將陷入這種邏輯困境呢?如果尊重言語交際的客觀事實(帶有目的性的言語行為實施者從來必須進行自我角色定位,至于定位是否準確,是否成功,另當別論)而又能避免陷入這一邏輯困境,我們就必須為“知己”尋找“主客相離”的想象空間。這一想象空間,我們以為,就存在于言語交際者的多重身份之中。
首先,表達者既有顯性的一面,又有知識結構中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導致的隱性一面。接受者一方或交際場外的第三方,面對所聞所見的表達者一方,直覺表象是表達者的顯性一面,而作為交際場中的表達者,其言語行為總是受其“互文性復數隱性角色”的支配;通俗地說,一個表達者在任何一個交際場景中的言語內容與言語形式,必然受其曾接觸過的各色人等通過各種渠道和各種交際事件對其所形成的長期記憶和短期記憶的影響,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何在同一交際事件中人言人殊,而不是千人一面,眾口一詞。“互文性復數隱性角色”是“話在說人”的一種表現形式。但一個顯性表達者固然有其對自我隱性角色的潛意識默認,更有主觀能動性作用下的有意識認證,即從個人認知環境中自覺選取“互文性面孔”。從這個意義上說,自覺選取自身隱性角色,也可謂某種程度上的主客分離,也就是利用語境因素的一種活動。在日常言語交際過程中,當一個表達者一時陷入沉思而后開口的過程是一種比較明顯的顯性自我與隱性自我的對話(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與語境要素選擇過程。這一藝術色彩稍顯濃厚的比方從表達者角度看,可表示為:
(隱性客體)復數他人→(顯性主體)表達者→(顯性客體)接受者
同樣,交際場中的顯性接受者個個都兼有“前結構復數隱性角色”。為闡釋學帶來本體論轉折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的所謂“前結構”(prestructure),有個最通俗的解說:“闡釋者不可能用一個空白的頭腦進行闡釋。”(南帆2002:271)當一個接受者搜腸刮肚努力解讀表達者的言語意圖時,也可謂一種主客分離的顯性自我與隱性自我的對話與語境要素選擇過程。從接受者角度看問題,交際主體雙方的表達與接受過程可圖解為:
(隱性客體)復數他人→(顯性主體)接受者→
(顯性客體)表達者←(隱性客體)復數他人
既然言語交際者的隱性角色選取與認證是言語交際的客觀存在,我們還可以進而探討交際者的互證身份。交際者的自我身份是交際場外的自然身份,互證身份是交際場中交際雙方映襯下的身份。互文性給人提供的是一個混雜的文本或文本背后具有多面體性質的表達者;前結構給人提供的是一個帶著有色眼鏡解讀文本的接受者。將表達者與接受者的互證身份導入言語交際互動中考察,則在當時當下的言語互動中,互文性添加了接受者的成分,前結構也增添了表達者的成分。于是,表達者與接受者的互動關系可最終圖解為:

言語交際有其科學規律,更有其藝術特點,因此我們大可不必為了避免主客相混的“科學邏輯”,而放棄用藝術眼光來挖掘影響言語行為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其實,持有主客分離觀的學者,在具體語境研究過程中,無論如何擺脫不了對主體因素的考慮。例如,鄭榮馨(2001:13)在理論上樹立了主客分離觀之后,緊接著對語言環境做如下分類①:

而后明確指出:“心理語境指的是人的經歷、思想、修養、個性、心情、氣質等等”,而且強調:“說寫者是掌握、使用語言材料的人,不論是自覺或不自覺,一方面要正確把握自我,使語言材料符合自己的經歷、性格、身份、修養等因素;另一方面又必須在輸出語言時,吻合語言環境諸因素。”這一表述不是繞了一圈,又回到了他本人所批評的主客相混,“把握自我”的具體實踐?
因此,筆者不贊同將交際主體排除在語境因素之外;與此相反,語境因素應包括表達者與接受者身份的自我確認與相互認證,無意識的確認與有意識的認證。我們利用“互文性”與“前結構”兩個概念,從理論上將自我一分為二,是一種符合“科學邏輯”的主客分離,這與其說是為了迎合“科學邏輯”的嚴密性要求,還不如說是為了尊重言語交際實踐的客觀事實,這一客觀事實與關聯理論為代表的認知語用學之“語境擇定觀”息息相關。
三、語境要素的給定與擇定:靜動態分歧觀
劉煥輝(2007:16)反對在還沒有研究透通常“語言使用意義”上的“語境”概念的情況下,將西方語用學中以斯波伯(Sperber)和威爾遜(Wilson)關聯理論為代表的“認知語境”概念攪進來。然而,他(同上)“關于語境構成的變數,皆因人們使用語言的情形不同而臨時形成不同的語境”這一動態語境觀使我們想到,恰恰是關聯理論(the relevance theory)由沈家煊1988年引入中國后,對國內語境研究形成巨大沖擊波,并漸成占據主導地位的當代動態語境觀。②
事實上,外語界對關聯理論“語境擇定觀”的直接評介數不勝數,漢語界的有關表述或顯或隱也受到關聯理論“語境擇定觀”的影響。既然我們提到將交際主體納入語境要素來考慮與認知語用學的語境觀息息相關,就有必要對關聯理論的語境觀作個簡要回顧,從而提出我們對“擇定”與“給定”的新思考。
關聯理論作為認知語用學的主要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對格賴斯(H.P.Grice)語用推理程序的挑戰。格賴斯(1975)提出言語交際合作原則(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及其四大準則(數量準則、質量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認為:交談者雙方都要有相互合作的愿望,交談才能成功,雙方都要根據當下交際的目的或方向,使談話始終符合交際需要,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才可促進交際順利進行,即雙方都要遵守合作原則;如果一方表面上違反了合作原則,那么另一方就要通過推理尋找對方表面上違反合作原則所要表達的會話含義。在批評傳統言語交際代碼模式方面,在言語交際需要聽話者推斷說話者語用意圖方面,關聯理論倡導者與格賴斯沒有多大分歧,主要分歧在于如何推理:合作原則認為,說話人與聽話人具有共享知識(mutual knowledge),共享知識形成的語境可以為聽話人的語用推理提供線索——給定性(given)語境觀;關聯理論先假定任何話語都具有關聯性,尋找關聯性過程是選擇語境因素的過程——擇定性(chosen)語境觀。后者的分析可簡括為如下兩個邏輯步驟:
1)揚棄“共享知識”:“誠然,所有人再現世界的能力發展都受到人類自身種屬的制約,同一文化群體的成員都共享一些經歷、教誨和觀點。然而,除了這一共有框架外,個體傾向于高度個性化。人生經歷的不同必然導致記憶信息的不同,更何況屢被證實的情形是:兩個人目睹同一事件——即或是像車禍這樣非常明顯、極容易被記住的事件——也可能對同一事件做出極不相同的敘述,不但解釋各異,而且對具體事實也形成不盡相同的記憶。如果說語法使不盡相同的經歷同化,那么認知與記憶則使同一經歷異化。”(Sperber&Wilson 1995:16)
2)突出語境的“心理建構體”要素:“一個語境是一個心理建構體,是聽話人對世界假設的一個子集。當然,正是假設而不是世界的真實狀態影響到話語的解釋。從這個意義上看,一個語境不僅僅局限于現實中的物理環境或緊接著的上文話語:對未來的期待、科學假設或宗教信仰、片段記憶、一般文化假設以及對說話人心智狀態的想法都有可能對[話語]解釋產生影響。”(同上:15-16)
我們認為,國內對關聯理論的評介既有認真分析的一面,也有忽略原著“揚棄”格賴斯觀點時的“保留信息”乃至一味追風,全盤接受“語境擇定觀”的一面。限于篇幅,我們先直接針對關聯理論的代表作《關聯性:交際與認知》()的表述闡述我們的思考。
以上所引第一步驟,我們之所以用“揚棄”而不是“否定”,是因為關聯理論先肯定“同一文化群體的成員都共享一些經歷、教誨和觀點”,然后才進入個體認知差異的敘述。關聯理論用極為苛刻的眼光看待交際雙方的“互知”(mutual knowledge),作為否定“互知”的典型例子是:
Ann和Bob早晨一起談論報上登載某影院當晚放映影片甲,下午Bob在當天報紙上發現已改為放映影片乙,于是用紅筆在報上作一記號。后來Ann也發現有此改動并認出Bob標出的記號,同時她也知道Bob無法得知她是否已看到這一改動。夜晚Ann見到Bob問:‘你看了那部影片沒有?’Bob應該理解Ann指的是哪一部片子呢?雖然兩人都知道放映的是影片乙,Ann也知道Bob知道放映的是影片乙,但這種共有知識并不能保證有效的交際,因為Bob可以作出種種推想:雖然我知道放映的是影片乙,Ann可能還認為是影片甲;也許她已看到我標出的記號,因此提問所指的是影片乙;她雖然看到我標出的記號,但知道我不可能得知她已看到那個記號,因此還是指的影片甲。如此推理下去,未有窮盡。總之,要實現交際,雙方必須互相知道每一點有關信息,包括“雙方互相知道”這點信息本身。(轉引自Sperber&Wilson1995:18)
“這種情況顯然不可能在話語產生和理解的時段內進行的”(同上)成為關聯理論否定“互知”的殺手锏。也正因為如此,關聯理論關注的不是言語交際推理失誤,而是成功的推理是如何成功的。用關聯理論的話說,“交際受到一種不盡完美的誘發式研究法的支配。這一研究途徑說明交際失敗是情理中的事。具有神秘色彩因而值得解釋的是成功而不是失敗。”(Sperber&Wilson 1995:45)于是,話語的關聯性成為給定的先決條件,“心理建構體”中的詞語信息、邏輯信息和百科信息等成為語境選擇項,于是又有了新舊信息作用下的最大關聯性,又有了值得聽話人花費努力去理解的最佳關聯性,等等。
最讓人困惑的是,持有語境擇定觀或動態語境觀的學者在論證過程中,總是有意或無意地給人們提供了對給定因素的動態選擇表述。例如,曾方本(2006:63)認為:“首先正式提出‘動態語境(dynamic context)’這個概念的是丹麥語用學家Mey,他將其解釋為交際過程中持續變化的場景,只有如此,交際才能不斷地進行,話語才能被理解。”可是梅伊在論述動態語境觀過程中,認為語域(register)也是與語境相關的一個要素,他(Mey2001:41)接著提出:“通過語域,人們可以了解說話者所擁有的語言資源來表達對交際者的態度。”(By register,one understands the linguistic resources that speakers have at their disposal to mark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ir interlocutors.)如此看來,說話者所掌握的帶有語域特征的語言資源必須是靜態給定的要素。
Teun A.van Dijk是國際話語分析領域的著名學者,其近年出版的專著主要論述動態語境觀,但他在論述過程中,卻不時地給出“語境給定性”的表述,如《話語與語境:社會認知模式》(2008)一書往往跳躍式地冒出不少以下表述:
因此累積而成的日常交際情景經歷可能導向抽象的模式腳本,其中諸如場景(時間、地點)、交際參與者(以各種角色和關系)和行為多多少少都是類別。(Accumulated experiences with everyday situations may thus lead to abstract model schemas in which for instance Settings(Time,Place),Participants(in various roles and relations)as well as Actions are more or less stable categories.)(p.61)
于是我們總體知識中有多少內容被激發并已包含在我們心理模式中語境(場景、讀者知識,目的,興趣,等等)。(How much of our general knowledge is thus activated and included in mental models depends on the context [Setting,readers’knowledge,goals,interests,etc.])(p.64)
以上譯文中加粗的著重部分均為筆者所加,意在凸顯“給定性”的表述。國內研究者在論述動態語境觀過程中與國外學者一樣,一時“動態”,一時“給定”,不無矛盾,催人深思。我們認為,探討語境是靜態給定的還是動態擇定的,要做以下兩點區分:
1)語境(context)與語境要素(contextual factors)的區分
2)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與語境要素(contextual factors)的區分
首先不能把語境作為一個“統一體”來看待,而應針對具體語境要素進行具體分析,不能過分強調一切都在動態發展中呈現,因為這既不符合言語交際實際,更可能導致缺乏理論與實際指導意義的語境虛幻化。試看關聯理論的一個例子The door’s open(.門開著。英文原例轉引自 Sperber&Wilson1995:20)。
關聯理論認為:“說話人和聽話人可能具有成千上萬種不同門的共有知識;因此互知無法說明人們是如何擇定‘門’的具體所指。”錯了,表達者和接受者首先不是依靠共享成千上萬個門來推斷“門”的具體所指,而是通過共享抽象之“門”的信息(“門”的語言意義)以及共享具體情景才使交際雙方鎖定成千上萬種不同之門中某一特定、具體的門。假定我們現在與同學們一塊在課堂上進行言語互動,此時在特定的教室語境中,在師生共有的教室語境中,“門開著”(“外面太吵,請把門關上”是一種可能的請求行為),如果沒有其它特指的話,唯一的具體所指就是“本教室的門”,而這個教室地點語境要素只能是給定的。
然而,與關聯理論動態語境觀或顯或隱“相關聯”的研究者堅持認為“語境就在你頭腦里”(張春泉、張艷玲2004:52)。是的,動態語境觀完全可以認為即使往同一教室掃一眼來鎖定具體的教室之門,不但需要行為實施者動用大腦細胞,而且大腦細胞動用者還必須就自己的大腦“雜貨店”做出某種提取選擇,可這種萬物萬事均需人腦過濾的語境觀除了見證人之所以為人的普通常識之外,對于人們言語交際實踐的解釋是否過于籠統,因而缺乏足夠的實際指導意義呢?
近年中國修辭學研究中較多地滲入語用學理論資源,胡范鑄在多篇文章中致力于構建言語交際事件的構成性規則,如新聞言語行為的構成性規則(胡范鑄2006a)和法律言語行為的構成性規則(胡范鑄2006b)等。構成性規則正是言語游戲之所以能成為游戲的潛在、先在、給定性的規則。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認為,語境要素是給定的,至少是給定的“假想集”,而選擇給定要素是一個動態擇定過程。沒有原有,無從選擇,更有一些語境要素是必須接受而無法選擇的。在書面言語交際中,上下文語境要素是不能選擇的,你必須面對提供的文本進行解讀;在日常口頭言語交際中,上文也是不可選擇的給定語境要素,你可以預測卻無法規定交際對方必須說什么,一旦對方說出什么,你就別無選擇,而只能面對。關聯理論對于我們大腦中的“心理建構體”做了一個“聽話人對世界假設的一個子集”的界定,這一界定從理論上講可以接受,但在言語交際實踐中,交際雙方是針對“給定語境要素”進行種種假設,從而靈活利用這些“給定語境要素”,爭取言語交際的預期效果。事實上,就日常口頭言語交際事件而言,關聯理論的“交際失敗是情理中的事”,雖然暗含著對給定共享語境要素的預測可能失誤,但預測成功卻是一種常態,否則人類言語交際將永遠處于“你說東我道西”的混亂局面。即使在書面言語表達中,表達者仍然需要對心目中的接受者進行給定因素的預測,例如一個充滿文史哲典故的文本必然預設了文史哲知識豐富的讀者。一個完整的言語交際事件始于靜態給定語境要素(比如時間和地點乃至交際對象自身諸特點)的選擇或預測,結束于靜動態轉換過程,一切已發生的均為給定要素,至于如何對給定要素進行動態處理屬于另一層面的問題。“語境要素的選擇”意味著“要素”是事實或假設中的給定要素,“選擇”是過程,分屬兩個不同概念。
四、結語:主客體與靜動態語境觀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本文非關聯理論專題研究,只是針對關聯理論對國內漢語界和外語界語境研究者所形成的或顯或隱的影響,闡述我們對“主客體”與“靜動態”的思考。我們傾向于認為,將言語交際主體納入語境要素來考察,既是尊重言語交際事實,同時也有利于交際主體為實現預期交際目標,時刻不忘自我角色定位的重要性,當然也是以關聯理論為代表的認知語用學動態語境觀的主要立足點。我們知道,關聯理論有其自身的研究目標:交際者面對自身“心理建構體”中的種種假想集,為何在交際瞬間做出了某種選擇,其認知機制是什么?探究人類認知機制自然有其科學意義。但回到言語交際實踐,對語境要素靜態給定性質的定位既有符合客觀事實的一面,同時還有利于人們積累生活經驗,豐富人生閱歷,提高言語交際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代偉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名言,具有永恒的真理啟發意義。當“語境就在你頭腦里”這一極端動態語境觀已成蔓延之勢時,我們有必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理論清醒,因為給定語境要素的動態選擇,如果就科學且藝術地選擇與組合給定語境要素而言,有其實踐啟發意義,但正是假定中的靜態語境要素為人們的動態選擇提供了資源,動態選擇本身則是言語交際科學化和藝術化相結合的過程。只有科學化沒有藝術化,世界只能成為“機器人”的加工場;只有藝術化沒有科學化,世界無法被理性地認知。
注 釋
①原文為文字闡述,為醒目起見,本圖示為筆者據原作文意所制。
②束定芳(2009:175)等主編的《中國國外語言學研究(1949-2009)》認為:“沈家煊1988年發表在《外語教學與研究》上的《訊遞與認知的相關性》一文標志著關聯理論進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