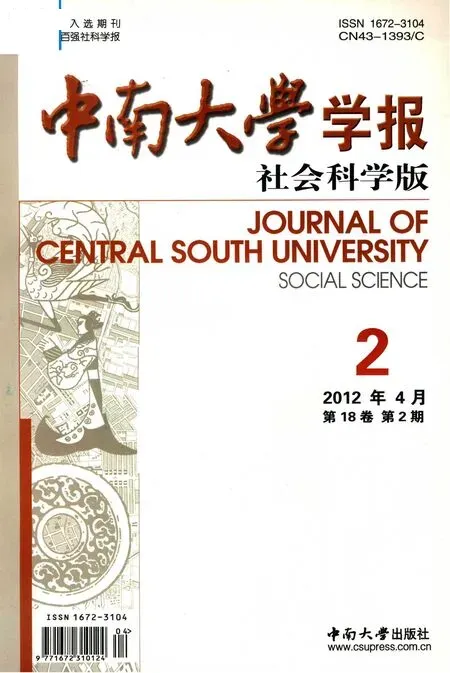交心運動與反右運動辨析
倪春納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江蘇南京,210093)
交心運動又稱“向黨交心”,是指1958年3月至7月,知識分子“自覺自愿”地把自己內心深處的非社會主義思想,公開地揭露出來加以批判,并制訂相應的規劃以踐行改造。交心運動始于黨外知識分子(包括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無黨派知識分子)并蔓延至黨內,最終席卷了當時整個知識分子群體。交心運動中所指涉的知識分子,在當時包括高校教研人員、新聞出版人員、醫務人員、中小學公辦教師和具有中專以上學歷的國家干部等。
一、交心運動的來龍去脈
早在1958年2月即已有零星的“交心”運動的相關報道,但是引發全國性的政治效應則是以 3月 16日北京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門舉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為標志。以這次事件為契機,中國共產黨把知識分子“自發主動的”的“交心”形式向全國推廣。運動過程中,中央和地方、部門、群體、行業之間進展的速度不一,從全國范圍來看, 5、6月份大規模的知識分子個體的實質性“交心”把運動推向了高潮。交心運動以1958年7月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四級干部會議為轉折點。這次會議決定對知識分子從以斗爭為主轉入以團結為主,[1](47)明確提出了統戰工作將轉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上來,提出知識分子要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進行自我改造,因此,它事實上成為交心運動的結束標志。
從1958年的2月初到3月中旬,大多數的“交心”都是以協會、單位、黨派組織的“集體交心”形式,實質性的交心鮮有涉及,它更多的是起到政治態度的宣示、號召和動員的作用。甚至在運動的擴散和蔓延過程中,即3月中旬到5月初這一段時間里,各地的交心運動大部分仍停留在知識分子大規模的集會動員表態和零星的示范性交心狀態。在“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之后,交心運動逐漸產生全國性的政治影響。尤其是在4月中旬以后,黨開始關注天津工商界交心經驗和上海知識界的改造規劃的形式,決定在交心運動中加以推廣,并在黨內同時展開。5月中旬,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央統戰部關于開展“向黨交心運動”的報告,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交心運動,[2](300)交心運動逐漸演變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
一般來說,知識分子的交心要經歷三個階段:首先,學習文件,并以文件精神來鳴放交心,進行自我檢查、分析和批判。交心的基本內容是“五交”,即交對共產黨的認識;交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交大鳴大放時期的言行和思想活動;交個人所受右派分子言行的影響;交反右斗爭以后的思想認識。[3](111)其次,組織大辯論,提高覺悟水平。通過大字報、小字報、舉行座談、舉辦思想展覽等各種交心形式對暴露出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批判,甚至有人把個人的思想問題編成活報劇、詩歌、洋片、相聲和快板等進行表演。[4]最后,制定和修訂自我改造的個人規劃,即“紅專規劃”,并通過各種座談會、大字報、思想展覽會、自由辯論會和各種交心、談話活動等對紅專規劃進行檢查評比,并以實際行動踐行改造。
交心運動中,盡管知識分子所要“交心”基本內容是“五交”,但是實際上,知識分子的交心內容遠遠超出這些方面。農工民主黨南京市委提出“九交”,即在“五交”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對新社會的認識,對過去參加歷次政治運動的態度,對整風、雙反、雙比、大躍進的認識以及一切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態度。河南醫學院的交心運動一般是由政治立場問題開始,交代的有對歷次政治運動和對黨的各項政策措施的抵觸不滿,個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對社會主義三心二意等;以后逐漸轉入教學、科研、醫療等方面的問題,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進行大暴露和批判。上海水產學院民主黨派交心范圍包括:對黨和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態度;在反右派斗爭前后自己的思想活動和錯誤言行;名利觀點、文人相輕和自由主義;對黨政領導的意見。[5]武漢地區許多學校師生員工提出向黨交心,不但交過去,還要交現在、交將來。[6]交心運動中五花八門的交心內容甚至包括個人工作和生活中的許多瑣碎的細節,但是其內容一般涉及知識分子政治立場、政治情感和世界觀三個方面。
二、交心運動與反右運動
現在學術界所指的“反右”運動其實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時間跨度為1957年6月到1958年夏天。但是根據當時的資料來看,很多事件經歷者都是將反右和交心運動作為兩個獨立的政治運動來加以認識。當時所認為的反右斗爭是指從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至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這一時間段。1958年4月,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指出全國有右派30萬人,但是截至1959年,中央文件公布的右派人數為 45萬人,[7](106)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右派即是由交心運動中“補課”產生的。
但是,無論從何種角度分析也難將兩者完全區分清楚。由于交心運動中所暴露的思想,很容易與右派發生混淆。為消除廣大知識分子的顧慮和擔憂,毛澤東對兩者進行了劃分:“右派的特征是他們的政治態度右。他們同我們有一種形式上的合作,實際上不合作。(傅鷹)這些人的批評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系,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8](472?473)《文匯報》社論《談交心的幾個問題》詳細闡述了兩者的不同之處:“右派分子釋放毒氣,向黨進攻,是站在與人民為敵的反動立場,抱著企圖使資本主義復辟的罪惡的目的。而今天我們許多同志向黨交心,則是站在人民的立場,愿意同黨、同人民站在一起,自覺自愿的來揭露自己,這與右派就有原則的區別。兩者之間,立場不同,態度不同;因此問題的性質也就不同。這就是區別兩類矛盾、采取兩種不同處理方法的關鍵所在,也是正確對待交心的第一要義。”[9]
這種帶有強烈主觀性色彩的區分標準在實踐中得到了一定的響應。天津大學校長、民盟天津市主委張國藩認為交心與右派的區別在于:“現在大家談出的問題和右派向黨進攻有本質的不同,大家自己談出來時要把這些東西挖掉,而右派分子是要發展這些資本主義的東西,要向黨進攻。只要自己拿出來,是進步的一種表現,不管情況怎么樣嚴重,性質是不一樣的,這完全是人民內部自我改造的問題。”[10]民主建國會天津分會常委李勉之認為,“右派是向黨猖狂進攻的,他們的目的是要資本主義復辟。而我們是接受黨的領導、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我們暴露自己交出心來,是為了徹底拋棄思想上腐朽骯臟的東西,更好地改造自己,更緊密地向黨靠攏,這和右派想利用這些東西來向黨進攻是根本不同的。反右派斗爭中,右派交代問題,是他們向黨向人民低頭認罪;而我們交心是自覺自愿、歡欣鼓舞的,是為了更迅速有效地進一步改造自己。我們和右派根本沒有共同點”。[11]
“從理論上說,交心運動的重點在于深挖靈魂深處的所謂資產階級思想和觀念。誰把自己的舊思想暴露的越多,上綱高、自責狠,誰就越能表明自己是在向黨交真心。”[12](155)同時盡管很多地方也宣布了交心運動中的“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但是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還是心存猶疑、顧慮和抵觸。“在交心過程中要經常與思想障礙作斗爭——人們的顧慮是因人而異的,最一般的顧慮是怕交了心領導對自己不信任,交了心在群眾面前丟面子,今后抬不起頭來,還有的人有進步包袱,怕交了心就把過去的進步一概否定了。”[13]廣元師范聶鳳遠老師在自己的交心體會中說:“在交心前夕,我顧慮重重,怕交出黑心來,當典型批判,不好過關。”[14]九三常委、古脊椎動物研究所研究院裴文中在萬人“交心大會”上揭露自己“經過大約一個星期的思想斗爭,最后才下定決心,向黨交心”。[15]武漢工商聯常委徐雪軒擔心“交,怕別人說自己落后,不交又不能改造好自己”。[16]張國藩在交心中坦言:“一是怕當右派,因為有些想法和右派差不多,一端出來,豈不成了右派;二是怕黨不信任,怕群眾不信任;三是怕失掉威信。”[17]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常務委員陳祖望擔心“怕交出臟東西被人說成是放毒,經過分析變成右派,也怕黨把這些東西記下帳來。因此,在交心開始,在內容上是普遍性的問題交,個人雞毛蒜皮的問題交,籠統概括性的問題交;而對黨的根本制度、方針政策,或自己認為重大的問題不交”。[18]上海水產學院某教授,交心時顧慮重重,經過小組同志多次說理、幫助,使他三次“交心”,“第一次只交了一鱗半爪,第二次仍未觸及關鍵問題,直到第三次才交出全部真心話”。多次反復“交心”,在交心運動中是普遍現象。
誠如許多知識分子所擔心的那樣,交心運動中所暴露出來的思想因其實質上與右派存在“共鳴”,而且交心又需要“和前一階段整風、甚至歷次運動聯系起來看”,所以很容易與“右派言論”相混淆,所以,交心運動中有很多人又被補成右派。1958年4月23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發出的關于號召全盟展開“向黨交心”運動的通知中,有“以上辦法對右派分子同樣適用”的字樣,但是同年夏季反右“補課”的右派分子大多都是掉進了“向黨交心”的陷阱而被“補劃”。[19]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截至1958年底1月15日,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占全體成員總數的9.4%;團結委員中劃為右派分子的 56人,占團結委員總人數的24.3%;省市一級的委員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153人,占省、市級委員總人數的23.1%。但到1958年10月末,全黨被劃為右派分子 2008人,占成員總數的12.7%,較之前者增加了3.3%;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增加到 39人,新劃右派 4人;團結委員中被劃為右派的增加到63人,新劃右派7人;省和直轄市組織的委員中被劃成右派的增加到174人,新劃右派21人。[20](409?410)
三、交心運動的情境認知
(一) 知識分子對交心運動的認識
首先,交心運動中知識分子把交心作為一個政治問題來加以感知。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強調交心運動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于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政治態度。[21]楊東莼認為,交心實質上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能否把心交出來,是整個地交還是部分地交,這對自己的政治立場將是一次嚴重的考驗。把心交出來,是一個對待黨、對待工人階級、對待人民、對待社會主義的基本態度問題。”[22]上海一位歷史學家坦言,“交了心,認識了自己。從不承認自己需要改造,變為要求加速改造了。不承認自己需要改造,轉變為要求加速改造,證明在這個戰場上,社會主義在政治思想上打了一個決定性的勝仗,交心運動的意義深遠,由此可見一斑”。[23]
其次,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以進行自我改造的途徑來理解交心運動。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金克木“交心”說:向黨交心,檢查錯誤思想,是改造的起點。張國藩認為交心是改造的關鍵之一,“首先,公開的錯誤言行,能交出沒有見諸言行的錯誤思想活動,這是決心改造自己的起碼的條件;其次,大家都交出大量的錯誤思想活動,自己排排隊,才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同時也互相有所了解”。[17]李勉之提出交心就是要暴露思想,主要應當暴露自己對黨、對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制度等的抵觸和不滿。[11]華東師范大學物理系主任張開圻在民主黨派整風大會上表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得到徹底的改造,應該忠誠老實地向黨、向社會主義交心,暴露資產階級的丑惡思想,這是解放以來思想改造過程中的一個大轉折點。
“交心”之后,很多知識分子表示“覺得向黨靠攏了,和黨是一條心了”,[24]“心情更加舒暢,積極在工作上發揮作用”。[25]輕工業部有人以詩來抒發他們經過思想改造以后的心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心情舒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情緒開朗,并不是我得到了什么寶貝,實在是因為我把心交給了黨。”但是,也有知識分子流露出對交心運動的反感、疑問和抵制情緒。運動中不少知識分子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提法有抵觸情緒,認為黨中央對這一問題的提法不符合事實,是對知識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壓力”和“打擊”。梁漱溟說:“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許多疑問而已。其中亦有抵觸情緒,但并不敢吐露真言。”[26]1958年6月,系領導要求吳宓在兩天內寫足大字報500張,但是吳宓僅完成90張,領導責勸吳宓務必完成500張指標,吳宓生氣的說:“宓惟有投嘉陵江而死,請君陪伴我往可也。”[27]華東紡織工學院副院長在其交心的材料中“檢討”:“‘交心’這一名詞本身對我似乎是刺激性過大的,對黨忠誠坦白是我所樂意的,又何必赤裸裸地說成是‘交心’呢? 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向市委會呈交決心書的大游行我是參加的,并且還手持領袖旗走在前列,但是,我心想這未免過于著重形式。”甚至有人直接反對:“就是不交,一條也不交。”[28]
(二) 黨對交心運動的認識
交心運動爆發后,出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運動的需要,黨內也開展了交心運動。一般由黨員帶頭,主動檢查自己,在運動中“引火燒身”。“事實證明,入了黨并非全是真紅或者紅透。有的褪色,有的粉紅,有的還是外紅里白等等。運動中揭發出來的某些共產黨員有官氣、暮氣、驕氣,也有闊氣、嬌氣,甚至還有其它的歪風邪氣;這些共產黨員不正是褪了色的或者粉紅色的嗎? 要想真紅或者紅透,就要首先引火燒身,燒紅燒透”。[29]北京大學黨組織在3月20日召開全體黨員動員大會,黨員領導同志在會上首先引火燒身。[30]黨委第一書記陸平在大字報中表示要克服領導工作不深入的缺點,并決心教一些政治課;黨委第二書記江隆基檢查了自己的官氣和暮氣;黨委第三書記馬適安批評了學校和黨委沒有足夠地重視對工農學生的培養問題等。[31]
針對黨外知識分子,4月25日,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指出:“交心運動是一件好事情。中共中央贊成并且支持這個運動。民主黨派不交心,要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困難的,交心的目的是為了改造思想,把六億人民團結在一起,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斗。”[32]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長勝認為,“向黨交心運動是我國知識分子深入的思想改造運動,也是把我國知識分子改造成為又專又紅、紅透專深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運動”。[33]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5月17日在江蘇省和南京市衛生干部會議上號召衛生醫務人員向黨交心,“開展交心運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變革我們政治思想政治立場的起點,決定著今后我們能否實現思想躍進工作躍進,能否‘又紅又專’的關鍵……現在向黨交心運動,是立場轉變的一個重要步驟。只有把思想上陰暗的東西交出來,經過黨和群眾的幫助,加以分析、批判,才能更加清楚的劃清資產階級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的界限,才能破資產階級立場,立無產階級立場。只有大破才能大立,‘大破’就是要交深交透,把資產階級思想搞臭,‘大立’就是思想上的大躍進”。有些人懷疑:“把那些資產階級丑惡的思想交出來,黨會不會信任我呢? 會的,交的深透,黨是會更加信任的……很明顯的,交心徹底,就是證明我們的立場有了根本的轉變。真正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黨就會給你更大的信任……要做到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就要改變立場,改變階級感情。”[34]天津市紅橋區統戰部長表示:“能否向黨交心就是能否靠攏黨、依靠黨、相信黨的表現,就是是否把自己心里的話都掏出來給黨看看的表現。否則,要求進步只是空喊口號而已。”[35]
四、余論
自交心運動之后時至今日,中國都沒有出現獨涉知識分子群體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一現象迄今為止仍被許多專家學者所忽視,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政治學者都對交心運動鮮有關注。目前,學術界對交心運動的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朱育和[36]在其《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根據報紙上的相關摘錄對交心運動進行了片段式的總結;羅平漢[37]的《1958~1962年的中國知識界》也依據同樣的方法對交心運動有所闡述;此外汪東林[26]的(2003)《梁漱溟一九五八年向黨交心》、姜東平[38]的(2008)《“向黨交心”資料披露一段往事》、張錫金[39]的(2010)《“向黨交心”的北大教授傅鷹》、張刃[19]的(2010)《“向黨交心”前因后果》四位學者分別以某一位歷史人物的交心材料為依托對交心運動進行了相關解讀。除此之外,交心運動雖曾在一些著作中略有提及,但均是浮光掠影地一筆帶過。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于反右運動的則已相當成熟,幾近于婦孺皆知的程度。因此,學術界對于交心運動的相關研究尚有待于拓展和深化。
[1]陳忞.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M].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2]朱企泰.統一戰線大事記[M].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1.
[3]楊愛珍.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研究[M].上海: 學林出版社,2004.
[4]本報訊.人人燒身躍進, 自覺革命成綱[N].光明日報,1958?05?12(2).
[5]本報訊.交真心、樹紅旗[N].文匯報, 1958?04?20(1).
[6]本報訊.武漢地區十四所中等專業學校師生把心交給黨[N].光明日報, 1958?04?14(2).
[7]劉友于.中國20世紀全史·第八卷[M].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M].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9]本報社論.談交心的幾個問題[N].文匯報, 1958?05?04(2).
[10]本報訊.學習天津經驗, 開展交心運動[N].光明日報,1958?04?12(3).
[11]本報訊.突破三關, 徹底交心[N].光明日報, 1958?04?18(3).
[12]楊鳳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研究[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5.
[13]吳克.向黨交心是向紅專躍進的第一步[J].黑龍江教育,1958(6): 7?8.
[14]聶鳳遠.向黨交心的體會[J].四川教育, 1958(4): 9?13.
[15]本報訊.向黨交心, 快真深透[N].光明日報, 1958?04?11(1).
[16]本報訊.武漢各民主黨派開展交心運動[N].光明日報,1958?04?13(1).
[17]本報訊.學習天津經驗, 開展交心運動[N].光明日報,1958?04?12(3).
[18]本報訊.排除障礙向黨交心[N].南京日報, 1958?06?5(3).
[19]張刃.向黨交心的前因后果[J].炎黃春秋, 2010(12): 58?62.
[20]朱健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M].長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9.
[21]本報訊.做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N].人民日報,1958?01?05(7).
[22]楊東莼.把心交出來[N].人民日報, 1958?04?05(7).
[23]本報訊.再接再厲, 向黨交心[N].光明日報, 1958?04?27(1).
[24]本報訊.交心: 知識分子改造的一面鏡子[N].光明日報,1958?04?24(2).
[25]本報訊.真心誠意走社會主義道路[N].人民日報,1958?04?30(3).
[26]汪東林.梁漱溟一九五八年向黨交心[J].百年潮, 2003(11):23?31.
[27]何蜀.1957年中的吳宓[J].社會科學論壇, 2010(10): 133?149.
[28]萬一.“自由”與“交心”[J].讀書, 1994(7): 5?6.
[29]本報訊.要真紅[N].人民日報, 1958?3?31(3).
[30]李梓.黨員要先引火燒身[N].人民日報, 1958?3?22(7).
[31]本報訊.黨員帶頭引火燒身推進運動[N].人民日報,1958?03?22(7).
[32]本報訊.再接再厲、交深交透、迎接五一[N].新華日報,1958?04?28(4).
[33]本報訊.向黨交心, 紅透專深[N].光明日報, 1958?05?01(5).
[34]本報訊.興無滅資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N].新華日報,1958?05?24(5).
[35]本報訊.民盟天津市紅橋區組織召開向黨向黨交心現場會議[N].光明日報, 1958?04?01(3).
[36]朱育和.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M].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7.
[37]羅平漢.1958~1962年的中國知識界[M].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8.
[38]姜東平.“向黨交心”資料披露一段往事[J].文史精華,2008(5): 28?34.
[39]張錫金.“向黨交心”的北大教授傅鷹[J].世紀, 2010(5):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