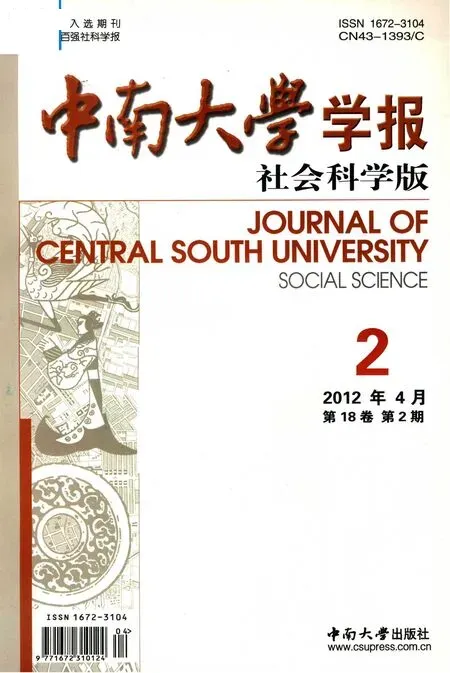從浪漫的質疑到自我的否定:魯迅對啟蒙的反思
李美容
(湖南工業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株洲,412007)
魯迅是一個啟蒙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啟蒙者,這是毫無疑義的。魯迅面對頑不可破、堅不可摧的封建傳統,面對愚昧、麻木、自私的國民靈魂,面對因循守舊、野蠻血腥的社會現實,發出了一聲聲振聾發聵的吶喊。他一加入新文化陣營,就成為最得力的啟蒙干將。即使在新文化陣營風流云散后,魯迅仍堅持啟蒙主張,終其一生,都不曾卸去肩上的啟蒙重擔。可就是這個最堅定、最頑強的啟蒙者魯迅,一直持續不斷地對啟蒙本身進行著拷問。一邊執著地進行著啟蒙工作,一邊懷疑和反思著啟蒙行為,痛苦、絕望而又無比堅韌。因而,魯迅的啟蒙較之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更持久、更深刻。魯迅不僅超越于現代中國其他啟蒙者之上,更不斷超越自身,超越了啟蒙者魯迅自己。
一、浪漫的質疑
魯迅對啟蒙的懷疑和反思,最初是以一個浪漫主義者的姿態表現出來的。
從17世紀中后期到18世紀的百余年,以法國為中心,啟蒙運動的思想狂飆席卷了西方,帶來了一系列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深刻變化。啟蒙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思想革命,它所帶來的現代文明是令人驚異的,幾千年的古代文明在它面前黯然失色,成為落后、蒙昧的象征。啟蒙者毫不懷疑地認為,“我們正在進步,我們正在發現,我們正在摧毀古老的偏見、迷信、無知和殘忍,我們正在建立某種科學,以使人們生活得更幸福、自由、道德和正義”。[1](26)民主、科學、理性、進步等啟蒙價值和觀念,直到19世紀初都未曾受到過任何懷疑。
是浪漫主義者最先打破了啟蒙的迷夢。他們看到,啟蒙主義者對理性的推崇,導致了理性與感性的分裂,人的形象被嚴重地扭曲;民主、自由、平等等觀念,在掃除封建特權、宗教神權的同時,伴生了現代科層體制,形成了對人進行新的奴役的牢籠;科學技術、工具思維極端發展的結果,使整個世界對象化,失去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浪漫主義思想史家馬丁·亨克爾寫道,“浪漫派那一代人實在無法忍受不斷加劇的整個世界對神的褻瀆,無法忍受越來越多的機械式說明,無法忍受生活的詩的喪失”。[2](5)浪漫主義者推崇人的情感、想象和意志,反對把人的理性與感性割裂,強調個性化的生活方式,追求無限和永恒,呼喚回歸自然,返回人的自然本性。浪漫主義者的主張,對啟蒙運動起到了反思和糾偏的作用。
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中國社會由前現代向現代轉變,在不斷落后挨打的處境下,西方現代文明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觀念,被一代代啟蒙者視為救國良藥。即使到了五四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現代文明受到了西方社會繼浪漫主義運動之后更嚴厲的質疑與批判,五四一代許多啟蒙者在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理性、人權等價值觀念時,仍然是無條件的、絕對的,這些觀念是以一種“真理”的身份進入啟蒙者的精神世界的。同是五四啟蒙者的魯迅沒有將西方的啟蒙觀念與價值視為真理。早在1907年,魯迅就以一個浪漫主義者的立場對西方現代文明進行了審視。
魯迅認為“文明無不根舊跡而演來,亦以矯往事而生偏至”。[3](50)西方文明,自啟蒙運動以來,對中世紀文明不免有矯枉過正之處,而產生不可避免的弊端。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魯迅指出英法等國啟蒙運動以來,“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彌漫于人心。”[3](49),魯迅沒有隨聲附和,大唱贊歌,而是進行了冷靜地分析。他認為,平等、自由、民主等啟蒙價值觀念在西方的普及確立,是“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流”,其弊端是“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3](49)人的個性、獨特性,就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幌子下遭到了扼殺。更進一步,魯迅看到民主、平等啟蒙觀念,不僅僅會扼殺個別人、個別天才的個性和獨特性。而且還會使整個社會淪于庸常,失去活力,“人群之內,明哲非多,傖俗橫行,浩不可御,風潮剝蝕,全體以淪于凡庸”。[3](52)所以,對于急于擺脫封建專制的中國人來說,西方的啟蒙觀念可能帶來的是另一種專制,又會使之淪為新的庸眾。
針對19世紀重物質輕精神,導致社會的功利化、人的物化和異化這另一大潮,魯迅對啟蒙運動另一弊端進行了反思批判。伴隨著啟蒙運動對科學的推崇,對工具理性的強調,物質財富在以幾何速度增長,而人的精神世界卻出現了荒蕪,以至于人在這個陌生的、異己的物質世界,找不到精神安頓的家園,產生了無家可歸感。魯迅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者對此早就有了警覺。“蓋舉世惟知識是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3](35)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科學技術,工具理性,其弊端又是對人的主體性、個性的扼殺,并且愈演愈烈,將使整個世界精神枯萎。“十九世紀后葉,而其弊端果益昭,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3](54)被工具理性所控制,整個世界包括人自身都被客體化、物質化,人已不能稱其為完整意義上的人,世界也將失去它的豐富和神秘,那么社會只將剩下虛偽和罪惡。“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盟,使性靈之光,愈益就于暗淡”。[3](54)啟蒙運動所導致的人的物化,社會的功利化,后果如此不堪設想,如果科學、理性等啟蒙價值和觀念不加審視就盲目引入中國,結果會怎樣呢? 魯迅指出:“中國在昔,本尚物質而疾天才矣。……則又號召張皇,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個人之性,剝奪無余。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3](58)所以,結局只會是更快地滅亡。
魯迅認為,要救中國,固不可沿襲原來的老路,也不可盲目照搬西方,將啟蒙思想觀念原封不動地引進來,依葫蘆畫瓢,而必須做出自己的決斷,經過一番反思批判,“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以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3](57)可見,魯迅是站在肯定人的個體性、主觀性、超越性的浪漫主義立場,對民主、自由、科學、理性等啟蒙價值觀念進行批判與分析的。他所激賞的,不是匍匐在啟蒙價值觀念下的庸眾,也不是封建專制宰制中的奴隸,而是“剛健不饒,抱成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3](101)具有自由意志、獨立個性、不斷反抗的精神界之戰士。
二、現實的批判
魯迅對啟蒙的反思與批判,在他早期留學日本時,主要站在浪漫主義的立場,縱觀整個西方現代文明,對其的扼殺個性、禁錮心靈進行了批判反思。正由于有早先對啟蒙的浪漫反思,使魯迅對西方現代文明保持了警惕,而沒有像其他啟蒙者那樣,將啟蒙視為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對啟蒙懷著樂觀的憧憬。尤其在經歷了《新生》雜志創辦失敗,回國后“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4](80)對啟蒙弊端的清醒認識,加上親身經歷的啟蒙失敗,和對中國現實的洞察,使魯迅根本鼓不起啟蒙的熱情。雖然,他聽從了金心異的勸說,加入了《新青年》的啟蒙陣營,雖然在《新青年》解散后,只有他仍然堅持啟蒙道路,及至十多年后,階級斗爭觀念盛行,許多人宣布魯迅過時了,可他仍抱著“啟蒙主義”不放。但是,在從事啟蒙工作的同時,他對啟蒙的批判反思也從未停止過。繼早年他對啟蒙的浪漫批判之后,他回到中國,在從事啟蒙工作的同時,他對啟蒙的反思主要站在現實主義立場,在啟蒙觀念引進中國后,對啟蒙價值的移植性、空幻性進行了思考。
魯迅對啟蒙的現實批判,首先著眼于啟蒙價值移植到中國后的變形甚至于產生相反的作用。他曾提到“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5](506)所以民主成了統治者獨裁的口實,自由成了戕殺學生、平民、進步知識分子的任意,科學成了中飽私囊的工具。“這并未改革的社會里,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并無兩樣”,[6](615)甚至還有可能更壞。自從民主、自由的氣息吹進中國來,“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復辟的自由,或者屠殺大眾的自由”。[7](70)于是有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有這個軍閥那個軍閥的混戰,有“革命,革命,革革命”。啟蒙的藥方非但不能使垂死的中國起死回生,反而加速了癰疽的惡化,加速了自身的潰爛。可以說,啟蒙移植過來后因水土不服,導致了更加殘暴的專制,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是一次又一次更血腥的殺戮;啟蒙導致了更愚蠢的蒙昧,革命者的血被當成治病的藥、一條辮子就能在鄉村引起軒然大波;啟蒙導致了精神的進一步奴化,正人君子成了幫閑的幫閑、學者文士露出了“叭兒狗”的丑態。
在中國社會未作整體變革,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情況下,啟蒙思想觀念傳到中國,只會變得面目全非,沾染上“鬼氣”與“毒氣”。竹內好認為,“面對自由、平等以及一切資產階級道德的輸入,魯迅進行了抵抗。……把新道德帶進沒有基礎的前近代社會,只會導致新道德發生前近代的變形,不僅不會成為解放人的動力,相反,只會轉化為有利于壓制者的手段。”[8(147)當中國其他啟蒙者熱烈歡呼“德先生”和“賽先生”時,魯迅對啟蒙的反思,不僅不是落后的表現,反而顯示了魯迅的前瞻性和超越性。
魯迅對啟蒙的現實批判,還體現在揭露啟蒙理想的空幻性。面對中國現代其他啟蒙者將自由、平等等價值觀念當作真理頂禮膜拜的情況,魯迅卻指出這些價值觀念在目前的中國只是虛幻的觀念和無法實現的理想。
在小說《頭發的故事》中,魯迅借“N先生”之口,指出了辛亥革命后社會依然如故,“懶洋洋”的“國民”已不記得雙十節,更不記得為民主、共和理想而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啟蒙者,“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里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3](488)啟蒙者以慘重的代價,換來的唯一成就竟是剪了辮子的人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了。付出與回報相差如此懸殊,反映了當時中國根本不具備接受啟蒙價值的土壤這一現實。“N先生”質問啟蒙理想家,“改革么,武器在哪里? 工讀么,工廠在哪里?”他認為“啟蒙理想家的一切努力,只不過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3](488)啟蒙者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目標,只可能出現在預約的黃金世界里,無法在當時的中國兌現。
魯迅還以小說《傷逝》,進一步警示人們對啟蒙價值不要迷信和盲從。小說《傷逝》里的涓生在子君面前是一個擁有西方自由、平等觀念的啟蒙者,并且一直以這套觀念引導她、評判她,以一個真理代言人自居。他先以這套思想觀念,喚醒了子君,“破屋里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里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9](114)子君在涓生的啟蒙言說下,認識到“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9](115)她不顧世俗的嘲笑,不顧家庭的反對與涓生同居了。可是同居不久后,子君只忙于做飯、喂雞等瑣碎的家務,以涓生那套啟蒙觀念衡量,她的所作所為毫無價值,她的精神境界非常平庸。涓生失業后,只忙于無聊家務、與小官僚太太吵架的子君,根本不符合他的那套啟蒙觀念,因此也不值得他愛了,并且還感到子君成了他生存的累贅。他明知拋棄子君,子君只有死路一條,可他還是以那套平等、自由的啟蒙話語為幌子,以“我已經不再愛你了”為借口,要逼走子君。此時,涓生也感到了自己啟蒙話語的虛偽,“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里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之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后惡意地刻毒地學舌”。[9](126)涓生以那套美麗的平等、自由啟蒙話語,誘惑了子君,接著又用它否定了子君,最終還利用它拋棄了子君。涓生因那套啟蒙話語的光環,獲得了子君“熱烈、純真”的愛,最后又毫無怨言地離開了他,自己去死。如果取下那個美麗的啟蒙話語光環,我們發現涓生其實只剩有膽怯、自私、冷漠、殘酷和虛偽。這樣一個人,只會空談平等、自由,不但擔負不起啟蒙的任務,相反還會使啟蒙走向反面。
通過涓生這個啟蒙者,魯迅深刻揭示了啟蒙價值觀念的空幻性,在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自由、平等插足的余地,對它的盲從只會導致悲劇的發生。實際上平等、自由的啟蒙思想觀念自五四以后,在中國形成了一種新的話語霸權,贊同附和者被視為進步,反之視為落后反動,而許多偽君子借自由平等之名大行營私舞弊的勾當。魯迅通過《傷逝》,告誡啟蒙者和被啟蒙者,不要對西方啟蒙觀念迷崇,否則啟蒙者將在無意中變成謀殺者,而被啟蒙者只會像子君那樣被剝奪話語權力,甚至生存的權力。
三、自我的否定
魯迅對啟蒙深刻的懷疑,還體現為對啟蒙者的自我否定。“歷史上的啟蒙主義者幾乎都是樂觀的,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言說的就是真理,預約的就是未來”。[10]魯迅卻是一個深刻的悲觀主義者。他用解剖刀解剖別人,更多的是解剖自己,尤其是那個啟蒙者魯迅。他在別人樂觀地看到希望的地方,他看到的是“鐵屋子”般萬難破毀的絕望;他在別人以真理在握的姿態,俯視民眾時,他卻清醒自覺自己絕非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魯迅是一個堅定的啟蒙者,卻又對啟蒙者身份不斷地自我懷疑與批判。
在魯迅小說中,啟蒙者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狂人、瘋子,一類是孤獨者。《狂人日記》《長明燈》里的啟蒙者形象都是精神不大正常的人。《狂人日記》里的啟蒙者某君,患有迫害狂癥,在他看來村里的趙貴翁、佃戶、老中醫、大哥,都滿眼兇光,“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3](445)都在找機會要吃他。《長明燈》里的啟蒙者,一心要熄滅吉光屯社廟里的那盞長明燈,他認為吹熄了那盞燈,就不會有蝗蟲,不會有豬嘴瘟。他的眼睛中,“略帶些異樣的光閃,看人就許多工夫不眨眼,并且總含著悲憤疑懼的神情”。[9](59)面對別人的阻勸,“忽又現出陰鷙的笑容”。當他想到用放火這法子以熄燈時,“閃爍著狂熱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尋,仿佛想要尋火種”。[9](60)無論《狂人日記》還是《長明燈》里的主人公,都呈現出一副心智失衡、理性失控的狀態。魯迅將啟蒙者塑造成狂人、瘋子,用意是深刻的。一方面,魯迅看到,歷史上那些反抗現狀、不滿奴役的先行者,統治階層容不下他,普通群眾不能理解他,往往會被大家罩上一個名目殺掉,這是中國歷史的老譜。對于一個要觸動乃至激烈否定封建傳統的現代啟蒙者,更不能見容于社會,所以會被視作“狂人”“瘋子”。《狂人日記》里的狂人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們不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3](447)由此可見,魯迅將啟蒙者塑造成狂人和瘋子,是對啟蒙者真實歷史處境和命運的洞察。《狂人日記》里的狂人,沒有被吃掉,是因為“早愈,赴某地候補矣”,他放棄了啟蒙立場,得以繼續容身于傳統社會。《長明燈》里的瘋子,因一再執著地要熄滅那盞長明燈,而被村人誆騙、嘲笑,最后被關了起來。另一方面,魯迅將啟蒙者塑造成狂人、瘋子,更體現了魯迅對中國啟蒙者本身具有的盲目、偏執、狂熱等致命弱點的批判與反省。中國現代啟蒙者,從西方學到了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就以為找到了真理,看到了未來,就要擺布蕓蕓大眾,“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如何生活,成為什么樣的人”。[1](35)他們的這種理想主義,這種盲目樂觀,如同《長明燈》里那個“閃爍著狂熱眼光”的瘋子一般,呈現出非理性狀態。成為啟蒙者的前提必須具有現代理性精神,而現在啟蒙者自身卻處于非理性狀態,那么這種啟蒙肯定是值得懷疑的。未經審視就照搬西方的啟蒙觀念,以為西方的啟蒙理性可以掃除傳統的一切愚昧與落后,導致的必將是非理性的狂熱與偏執。“那種所有一切都可以抽取出來的理性主義信念是令人恐懼的,或者與其說是理性主義的信念,毋寧是這種信念得以成立的理性主義背后的那個非理性主義之意志的壓力是可怕的”。[8](195)魯迅將啟蒙者塑造成狂人與瘋子,其良苦用心于此可見一斑了。
魯迅小說中的另一類型啟蒙者是孤獨者形象,如《在酒樓上》中的呂維甫、《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在前一類啟蒙者形象上,魯迅批判的是啟蒙者的狂熱、偏執。在這一類孤獨者類型中,魯迅揭示了面對傳統的威壓時啟蒙者的無力、無語乃至死亡。《在酒樓上》中的呂維甫,曾經到城隍廟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與人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于打起來。可是這個慷慨激昂、熱血沸騰的啟蒙者,10年后,卻過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大老遠從濟南回來,只不過是為了給3歲時死掉的小兄弟遷墳,給鄰居的女兒送兩朵剪絨花;為了糊口,到人家家里去教《詩經》《孟子》《女兒經》之類的書。啟蒙者呂維甫已經放棄了原來的啟蒙話語,變得麻木、無聊、頹唐,成了一個得過且過的人。在《孤獨者》中,作者描繪了一個啟蒙者根本無法容身的社會環境。從鄉村到城市,處處都奉行著虛偽的禮教;從大良的祖母到小孩大良、二良,個個都勢利自私。啟蒙者在這樣的社會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我”即使小心謹慎,還是被迫四處覓職,而又四處被驅逐。更加大膽、更具反抗性的啟蒙者魏連殳,竟被逼到了活不下去的絕境。最后他將行為完全顛倒過來,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這樣不僅被社會接納,而且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還飛黃騰達起來了。魏連殳與呂維甫一樣,面對現實的威壓,無奈地放棄了啟蒙,選擇了茍活,與黑暗的社會妥協。魯迅通過啟蒙者的失敗,不僅僅是為了揭示啟蒙任務的艱難,更在于否定啟蒙這一行為本身。啟蒙者自己尚且難于改變自己,重新回到了啟蒙前的舊我狀態,又怎能拯救別人,擔當啟蒙任務呢!“自覺到身為奴才的事實卻無法改變它,這是從‘人生最痛苦’的夢中醒來之后的狀態”。[8](206)所以像蠅子一樣飛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的呂維甫、魏連殳,內心都是非常痛苦的。呂維甫不斷地自責,“連自己也討厭自己”;魏連殳則以打牌、猜拳、失眠、吐血,草草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實,魏連殳、呂維甫就是魯迅另一個自己,他們的無奈與痛苦,就是魯迅自己看到了啟蒙的無力、無效,感到了無路可走的痛苦。
狂熱、偏執的啟蒙者和孤獨的啟蒙者,最后都成了失敗者,在魯迅筆下,根本就沒有成功的啟蒙者形象。魯迅自己作為一個啟蒙者,寫啟蒙的失敗,其實就是對他自己那一代啟蒙者的否定與批判,批判他們自己啟蒙頭腦的偏激、狂熱,批判他們啟蒙的無力、無效,從而否定了啟蒙的樂觀憧憬,否定了解放的幻想。這種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不以嚙人,自嚙其身”,[9](208)使魯迅較其他啟蒙者更清醒、更深刻,也更彷徨、更痛苦。當其他啟蒙者認為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出路時,魯迅卻在承受著夢醒之后無路可走的煎熬。
竹內好認為,“新的價值不是從外面附加進來的,而是作為舊的價值的更新而產生的,在這個過程中,是要付出某種犧牲的,而背負著犧牲于一身的,是魯迅”。[8](151)面對啟蒙,魯迅從浪漫的質疑,到現實的批判,再到對啟蒙者的自我否定,對啟蒙本身的價值偏頗、對啟蒙觀念引進中國后產生的問題、對中國啟蒙者的失敗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從來沒有將解放的幻想寄予在啟蒙上,也沒有寄予在任何其他方面。他所做的就是對舊傳統、舊習慣,不斷地施以猛烈的攻擊,目的是要催促新的產生,促進舊的滅亡,使中國能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于是魯迅主動地肩起了黑暗的閘門,放別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而把自己獨自留在了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9](170)
[1](英)以賽亞·柏林.浪漫主義的根源[M].南京: 譯林出版社,2008.
[2]劉小楓.詩化哲學[M].濟南: 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6.
[3]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4]魯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5]魯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6]魯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7]魯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8](日)竹內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5.
[9]魯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10]譚桂林.魯迅小說啟蒙主題新論[J].魯迅研究月刊, 199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