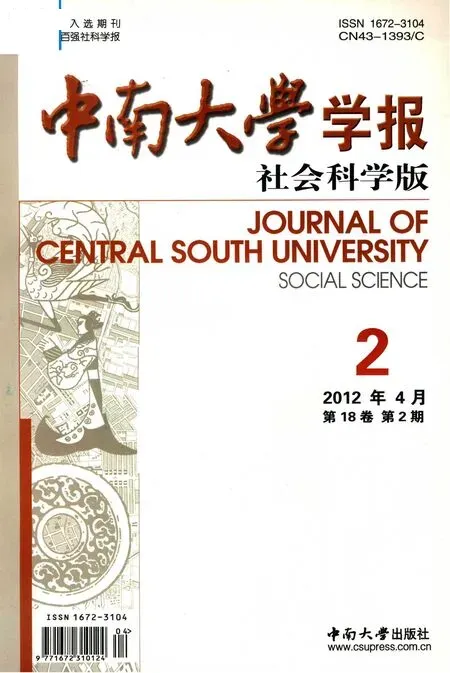話語批評主體性問題的修辭闡釋
涂家金
(福建工程學院外語系,福建福州,350108)
一、引言
批評話語分析(CDA)和批評語言學(CL)都以揭示人類象征實踐中的言辭互動規律和機構話語權力運作為目標。為簡單起見,我們以話語批評指稱二者。話語批評強調批評的反思性或對批評實踐自身的批評。對話語批評的理論前提進行反思也是批評的要義。作為話語批評最為倚重的當代理論家[1],Foucault、Bourdieu和 Habermas對主體有著不同的見解。這些不同的主體觀沒有或未能就批評何以可能的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闡釋,并導致話語倫理責任無法界定等問題的出現。Fairclough雖然有相當的篇幅梳理探討Foucault的話語權力觀,但隨后的批評分析專注于揭示不同機構權力的運作過程而并未觸及權力的動源[2]。Foucault權力觀最突出的問題是:既然權力無處不在,有意識的批評何以能突破權力之網?批評實踐自身的反思何以可能?Pennycook則只將Foucault與Habermas的理論進行關聯,指出前者的后現代主義思想與后者的現代主義思想存在著內在的沖突以示CDA之不足[3](84)。田海龍在批判系統功能語言理論語境決定論的基礎之上指出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想對于人的策略和批評能動性的解放[4](132?134)。然而,“后現代主義”顯得過于寬泛籠統。甚而有些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如 Foucault、Bourdieu等對主體性都持消極的態度。相對與此,當代西方修辭論辯理論家如 Perelman、Burke則秉持人文主義思想,對話語或批評主體的能動性持積極樂觀的態度。他們所闡說的修辭行動主體觀,能夠對批評主體性問題作出充分解釋。
二、Foucault的話語權力主體
Foucault的話語主要指稱能夠生產特定的言說、概念、效果的規約性實踐或未言明的規則與結構。人們可以通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存在著的某些觀點、行動方式、各種符號集成體(如建筑、文本、儀式)和由此而生的效果等不同話語顯現的場所而感知到某一話語結構的存在。Mills認為話語的效果源自權力、知識等因素[5](54,17?8)。在 Foucault看來,權力不是一個實體,不是可以占有的物,而是“或多或少有組織的、層級性的、互相協動的關系簇”[6](198)。它無處不在:行使自無數的點,彌漫于整個復雜的社會網絡,因而也必然例示在各種象征形態之中。他還指出,權力關系首先是生產性的。壓制完全不足以充分分析權力機制和效果,禁令、拒絕等只是極端的而非根本的權力形式。權力之所以能夠為人們所接受,恰恰在于它不僅僅只是通過說“不”作用于我們,而還在于它能夠“制造事物,誘發愉悅,形成知識,生產話語”[6](92?95)。
然而,Foucault的生產性權力觀并不意味著積極主體的存在。他指出,“個體不應被視為維系權力的某種基本的原子核。……事實上,在某些身體、手勢、言辭、欲望被識別為和歸屬于個體之時,個體已然是權力的首要效果之一”[7](98)。將主體視作權力的效果在某種意義上便宣告了主體的死亡。對于 Foucault而言,重要的不是“誰行使了權力”和“為什么(行使權力)”,而是“權力如何運作”。在將主體撇置一邊的同時,Foucault專注于他認為很重要的形構主體性的那個過程[5](34)。
Foucault認為,正是權力的規訓生產出了現代意義的主體。他相信權力的施行和學科知識的傳遞始自對身體的納入、控制與塑造。規訓因而即是“與身體相關的藝術”[8](137?138)。它意在通過不同的空間技術、時間技術、身體技術的組合,最終增加每一肢體動作的效率和不同動作的協調性。邊沁的“圓形監獄”典型地呈現了規訓式話語權力的運作。“圓形監獄”是一種全景敞視的環行建筑,中心設有一座了望塔,上面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行建筑。整個環行建筑又由許多小囚室構成。每個囚室的窗戶和照明設計足以保證中心了望塔上的人可以監視所有囚室里的犯人,而犯人卻看不到塔中人。這種無時不在的可視性及其所意味的脆弱性有利于犯人的自我約束與控制。不同的空間布局和由此帶來的可視性本身因此即可生成并支撐著規訓式權力。后者不必依賴于貌似“權力施行者”而實際上仍不過是權力結點或權力關系承受對象的人的力量或意圖。在Foucault看來,現代的工廠、醫院、軍隊和學校等都充斥著類似于“圓形監獄”的權力技術來觀察、監督、評估和生產不同個體[8](173?5,200?1)。不同的身體不再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肉體,而是經過話語權力的形塑變成了溫順、高效和有用因而可以執行各種社會功能的機器。身體進入到話語權力和社會的視野中。Foucault所理解的現代主體因而只是權力和話語的產物、例示或效果,而不是作用于權力或受權力壓制。
同時,Foucault的類似于庫恩“范式”的“知識型”概念也將其所理解的主體“無主化”。Foucault認為,不同歷史時期的知識型是不可通約的,是爆發式產生的。一般我們所說的歷史對于福柯來說不過是以“傳統”的名義,將歷史變遷中的許多變化、偶然性、異質性人為撇除,進而使其形成統一連貫、逐漸進步的敘事的結果。Foucault的目標正是要破除這種“連貫進步”之迷思,彰顯歷史之變化,也即真正的歷史性[9](148)。不難理解,Foucault傾向于將人類的話語切分、鎖定于互不通約的歷史時期。如此一來,某些思想在主流話語形態或知識型瓦解前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些與某一時期所流通的知識型格格不入的思想觀念總是被斥為瘋癲惡念。于是,語言的生命不再源自諸種的論辯或修辭互動,人類的話語實踐不再孕育和容忍紛繁主題。 換言之,知識型必然以泯滅真正的言辭互動或論辯為代價來實現統識與宰制[10](14?5)。
雖然后期Foucault也轉而關注“個體行為的問題”或“風格化的實踐”,但“這些實踐仍然不是關于個體如何(能動)創造自己的實踐”。也就是說,他的這種轉變并不意味著其轉向以主體作為話語實踐的源頭和審裁者的人文主義。后期Foucault總體上仍然固守于這樣的觀點:“人沒有任何足夠穩定的東西(即便是其身體也不例外)來充當自我認識或理解他人的基礎。”因此,他對“人將自我轉變為主體的方式”的關注只是其研究側重點的轉變,而非對主體看法的根本轉變[11](359?360)。換言之,后期Foucault仍然堅持主體性是權力效果(而非外在于或先在于權力關系和表征)的觀點。
Foucault的主體是權力關系的效果和例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將主體能動性和策略選擇性拋棄,并忽略了主體的話語倫理責任。這必然導致如話語批評那樣的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困境的出現:無能動性的人或行動體何以實施話語行動?何以可能掙脫話語權力的籠罩?如果我們以修辭學家 Burke的“人行動,物運動”(Men act, things move)[12](64)的戲劇主義新修辭思想觀之,Foucault的作為話語權力效果的主體實質上是已被客觀化為只能“運動”的物。如此一來,正如修辭學家Perelman所指出的那樣,“人不再是萬物的尺度;他成了玩偶。我們過往所傾向于認為是某種力量和動因的天才也僅僅只是一種(權力)結果;它不再是一種(啟迪之)光,而只是(無主之)反射;它不再是一個(自主的)聲音,而只是回響”[13](434)。這種“將充滿良知的人類事件轉變為類現象,將人變為其環境的產物”的主體觀“對人無疑是一種貶損”。在這樣的觀念之下,“即便有靈光閃現,人也不再是舉足輕重的事實存在:他成了反射、類現象和表象”[13](444?5)。
三、Bourdieu的習性主體
Bourdieu的主體觀可以從其理論體系中的關鍵概念之一“習性”得以揭示。習性是使行為人傾向于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動或作出反應的一系列的性情集合[14](12)。Bourdieu強調習性是具有持久特征但又可轉變的性情系統,是先定地發揮著“組構結構”作用的“結構化了的結構”。結構化了的結構是能夠客觀地加以規定(即獨立于個體的意識和意志)、程式化的生產和組構實踐與表征的各種原則。Bourdieu強調這些原則并非是某一個體精心策劃的行動的產物[15](72)。習性因而與“無意識”緊密勾連。它讓人的各種行為、決策、肢體動作等具有某些特定的傾向性。雖然Bourdieu也使用了“行動者”的指稱,但它絕非Perelman和Burke意義上的能動的有意識的行動主體。誠如Thompson所言,由性情集合即習性所生成的各種實踐、認識和態度是“有規律的”而非受到任何“(外在)規則”的有意識的協調或管制。那些構成習性的性情特征本身習得自一個漸進的反復灌輸的過程。習性之所以是結構化了的結構就在于性情特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習性形成的社會環境。換言之,社會環境的諸多特征會“銘刻”于習性之中。這也意味著具有類似背景的個體具有相對的同質性。結構化了的性情由于“銘刻”著特定的社會印記,因而還具有持久性,甚而歷個體一生而不變,并以前意識的方式發揮作用而不易為有意識的反思和修正所影響[14](12?3)。
雖然Bourdieu并不贊同將個體看成只會毫無主見地消費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傻冒”的觀點,但他強調人的行動總是具有先定特征。習性的同質性與持久性意味著“行動者”行動的相似性和某種無意識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主體的能動性。從一定意義上說,那些反復灌輸形成的性情更多是沉淀于個體的身體而不是心靈之中而作為其行動的前意識基礎[16](256)。Bourdieu之所以否定能動主體觀,原因在于他認為這種主體觀無法揭示某一文化的客觀結構與個體的特定傾向性、活動、價值觀和性情等之間的緊密聯系。修辭學家們認為行動者能夠以特定的利益或目標來指引自己的行動。但Bourdieu認為,個體之行動絕少是有意識的權衡或算計的結果。由習性而生的各種圖謀的特定效力皆因它們均非藉借意識與語言而發揮功用,皆因它們不受內省體察或意志控制之掌控[17](466)。
Bourdieu的習性主體觀具有濃厚的社會決定論色彩。它不僅固化了人的階層屬性,更嚴重的是,由習性“前意識”地生成和規約的主體的諸多話語實踐不再是主體改造自我、改造社會、革新文化的能動實踐。與 Foucault類似,習性闡說將主體的實踐化約為“運動”而非真正的“行動”,因而無可避免地否定了行動者批判、再闡釋因而修正自己的實踐邏輯進而推動社會變革的實踐理性,并導致類似于Foucault式權力所遭遇的問題的出現:習性個體如何掙脫、反制那些形塑習性的社會規約或實踐?人們何以可能改革、再造他們的社會并不斷促進其進步?話語批評又何以可能?由此伴生的后果是,假若我們接受Foucault的權力話語主體(“作者死了”)或Bourdieu的習性主體觀,那么,我們又該如何界定各種主體的話語倫理責任?話語批評又何以有積極意義?畢竟,如果各種話語的實踐者只是權力的效果亦或是受先在的習性指引,倫理責任必將消隱或模糊。任何威脅人類文明賴以存在的社會和道德根基的言語行為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歸因于無處不在的話語權力或潛意識習性的作用而得以證當開脫。
四、Habermas的交往行動主體
相較而言,Habermas的批判理論由于強調批判反思與理性論辯因而更適合于作為批判現實、實現社會革新的理論基礎。與Foucault不同,Habermas認為現代理性不應該被全盤否定、拋棄,而只需重建即可適應當代社會的發展。他的理論議程因而是重建理性,通過捍衛理性的反思潛力和不偏不倚的批判立場并以此解釋和批評那些扭曲的機構實踐來使理性重獲生機活力[18](45)。Habermas在其普遍語用學理論中區分了交往行動與策略行動,前者以真正的理解為目標而后者則意在成功。策略行動對應于由目的?理性行動以及象征行動組成的功利互動模型。它不同與交往行動的地方在于拋擲了言辭互動中的真誠與真實的“有效宣認”[19](40?1)。策略行動或者修辭學家所稱為的修辭行動在 Habermas看來無一例外地指向說服效果,因而至多不過是一種粗糙的取效行為而不具備交往行動的反思性有效宣認特征[18](52)。因此,Habermas傾向于認為,策略話語或策略行動具有內在的操縱性,理應成為鞭撻乃至擯棄的對象。
Habermas的理論闡說雖然以論辯作為交往行動的原型,但這里的論辯是一種完全以相互理解為目標、純然理性的反思性話語互動模式。這種論辯要求互動參與者本著真誠、真實和合規范的原則對某一爭議進行主體間性式的證當與辯駁[19](58),直至達成共識(某一方的觀點為他人接受或修改或放棄)。他關于交往行動的理論闡說不是基于一個實在的、不完善的現實世界所生發、界定的言辭實踐,而是以“超情境”、理想化的條件中所生發的言語行為作為出發點。他預設存在著一個規范的、程序化但卻是超驗的原初互動條件,即“理想言談情境”。 理想言談情境中的所有參與者均享有均等的言說機會。Habermas相信,假以不受拘限、全面公正的討論,話語的有效宣認終將達致共識和理解。理想言談情境實質上標示了一種不受任何功利或世俗因素扭曲的互動模式。
然而,正是由于理想情境的引入,日常話語實踐不得不被貼上“扭曲”或“墮落”的標簽;出于現實功利的目的而以影響他人為目標的所有話語不得不被交往行動這一理論參照所邊緣化。對 Habermas而言,共生于策略或象征行動之中的僅有利于某一方的派性利益總是“不道德”或“令人厭煩”之物[18](37)。簡言之,Habermas的理想言談情境和揚交往行動而抑策略行動的理論偏好無疑放逐了任何攜裹著功利或修辭基因的話語實踐。在 Perelman、Burke等修辭學家看來,任何言說實踐都是功利的,因而也必然都屬于策略或象征行動。諸如“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口號不過是踐行“無利益的利益”原則。其實質是Perelman所說的彰顯高尚目標、消隱達致目標的手段的論辯策略[20](85)。
雖然 Habermas承認行動者的意圖性和話語能動性,但這種理論贊許卻僅限于交往行動人,而那些歸屬于策略行動的所有的日常話語實踐和生活世界中的行動者難免蒙上了消極色彩而成為了批判、貶抑的對象。這實際上否定了人或行動體的修辭發明(即就某一議題尋求任何可說、就不同受眾尋求并訴諸不同言辭手段進行說服的過程)的能力。就這點而言,Habermas的交往行動主體顯然過于理想化而具有反修辭的屬性。它必然要求所有的個體或機構實踐者至少能夠暫時擱置各自的利益。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五、修辭行動主體
(一) 修辭行動與策略必然性
與Habermas不同,修辭學家Burke、Perelman等并不認為策略行動是什么“厭煩之物”。對修辭學家而言,人是象征的動物,因而也是修辭的動物。“修辭思想歷來以修辭者為中心,強調修辭者的施事能力”,與之相關的“動源”“意圖”等概念在修辭理論中至為關鍵。與客觀主義所信奉的“非人格化”相較,“人”在修辭思想中始終處于中心地位。這種“以人為本”的修辭意識還彰顯了修辭者?受眾的關系,并最終使能了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修辭轉向,使“學者們看清了人文學科話語的‘說服和道德本質’及其內在的‘解放和批判功能’”[21](292)。與 Bourdieu、Habermas等對主體能動策略性的悲觀看法不同,Burke認為,立根于等級差序和不完美的生活世界中的主體對于形形色色的象征運作的追求是普遍而無可厚非的。我們之為人的本質將在我們步出策略行動之域的那一刻喪失殆盡[18](36),言辭與行為必然由策略決定[22]。Burke相信,善與惡交織存在于我們的世界,但這也正是我們醉心于完美和總是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動因[12](16)。新修辭思想所理解的象征行動必然蘊含認同、區隔、奮爭與張力。認同的存在以各種差序的存在為前提,其實現可以動用情、理、威三個基本的修辭手段,而情與威顯然屬于Habermas批判的對象。認同也可以通過Burke所界說的戲劇主義五要素即情境、施行者、手段、目的、行動的不同組合呈現不同的言說視角或辭屏來實現。例如,對于某一事件的原因,人們可以歸因于“形勢所迫”(突出“情境”),也可認定為系相關人員的“本性使然”(強調“施行者”),還可以歸因于“設備問題”(彰顯“手段”)。話語五要素的變換體現了人或行動體順應現實世界的能力。
(二) “行動”與人的象征屬性
Burke的修辭理論區分了行動/運動這一基本的對立(即“人行動,物運動”),用以將人的主體能動精神與物體的運動或純生理的活動區別開來。他還明確將主體意識作為鑒別行動的因子,認為意圖性是界定行動的惟一不容置疑的因素,是所有行動最基本的共同點[23](61,241)。他指出,任何將行動簡約為運動的觀點都只能導致對人的能動性的理解太過于缺少象征性而無法窺探作為象征動物的人所專有的策略維度[12](53?4)。主體的策略行動性體現了人的象征屬性,即人既是制造象征的動物,也是運用/誤用象征的動物[23](16)。修辭因而是使用象征以形塑和改變人類自身及其環境的實踐,其基本功能在于使用語言等象征手段來誘發作為象征動物的人的合作、組建聯盟或贏取信奉。修辭根植于語言的基本功能之中。Burke因而干脆將語言直接定義為象征行動,并著迷于各種象征的策略力量。他認為,各種象征總是具有策略維度,是理解我們自身和實現變革的手段。
Perelman也認為,人的自由、自覺性和順應轉化的能力是人區別與物之所在,并使人服膺或抵制說服成為可能。“訴諸論辯意味著放棄訴諸武力(來解決問題),意味著珍視通過推理說服以贏取對方對己方觀點信奉的作法,意味著言說者不是將言說對象視為物,而是能夠自主判斷的人。”[13](55)他指出,人是其行動的作者。行動在此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了人之言說、作品、服飾舉止、行為等。正因為人是行動之主我們才能將與某一個體(或機構)相關的方方面面的實踐看成是其本質外顯之形式而對其加以評判。此即Perelman所界定的廣泛存在于話語實踐并發揮基礎作用的人?行推定(person-act presumption)。由此還可引申出本質?行動推定,即對該主體“本性”的揭示可以通過其他外化的廣義的“行”加以判斷[20](89?93)。人?行推定使批評和話語責任歸因成為可能。它還是(訴諸)權威、(訴諸)模范等存在的使能條件。權威的作用機制正是以某主體(如愛因斯坦)或行動體(如哈佛大學)作為言說的依據和語力源,將其(或成員的)言說、觀點、思想信念等(即廣義的“行”)作為該主體的展現進而作為話語互動倚賴的論據。人?行推定的廣泛存在并不必然導致修辭行動主體因可能的話語倫理追責而只能陷于被動。論辯主體是一個自主自由的主體。這種自由當然也會在言辭互動關系中因對受眾的話語順應而受到限制,但這不是否定或剝奪而是使能了其策略能動和反思之自由。作為修辭者的個體或行動體在Perelman看來可以從諸如廣為流通的事實、真理、推定以及價值、偏好等論辯前提[20](24?9)出發,推陳出新,通過諸如定義分解、訴諸外源因素、剝離例外等論辯策略來反制話語倫理責難、彌補言辭失誤等。
Perelman進一步指出,如果主體沒有自我轉化、革新思變之力,則教育將只是鬧劇,道德將喪失意義,諸如責任、罪感、優點這樣與人之自由能動緊密勾連的觀念將不得不被拋棄[13](205)。Burke、Perelman所界說的具備了目的性與主體意識的修辭論辯主體擁有實踐理性,能夠挖掘功能各異的實踐策略并順應情境諸元進而推動社會進步。反過來,正是因為主體的自由與能動(因而可以自主地判斷、做決定),道德與責任才能與之關聯;作為言說對象的受眾的主體性才不會被忽視[24](856)。
(三) “否定”與人的論辯性
人的象征屬性還典型的體現在人是“否定”的發明者,或者說,否定的概念為人所造并僅僅存在于人的象征系統之中[12](9)。它不僅不是一種歪曲、變形或尚須解決的問題,而是內在于作為運用/誤用象征的動物的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常常利用“他者”來界定自我、明晰身份、團結“我”族以共御“外”敵,實現 Burke所說的對立認同。那些在修辭行動中所遭遇的表面上反向、競爭性(而不必然是敵對)的各種阻滯因素(人、機構、觀點、制度等)在Burke看來并非只是純粹的消極力量。Burke辯證式地指出,沒有這些看似消極反向的“阻力”,或者說“反成主體”(counter-agent),也就沒有積極事物的存在。正是反成主體的存在,修辭者才需要費盡心機進行修辭發明,并通過與這些阻滯力量的砥礪而持續不斷地自我完善和進步。換言之,正是這些反成因素使能了話語實踐者的創造欲求、修辭行動和那些人類文明話語中可歸為真、善、美的一切事物。這表明了修辭學家對生活世界不完善的實用悅納和對主體能動性及反思性的樂觀態度。
反成主體或者說“否定”實質上體現了人的論辯屬性。這是修辭主體能動性的又一反映。這一屬性首先可以從自我作為修辭者?受眾的結合體得到佐證。Perelman指出,自我闡說或反思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論辯。他認為,我們反思時說服、批判自我的方式與針對他人的說服、批判方式無異[20](4)。話語與心理學者Billig也指出,思維只是基于外部對話的一種自我論辯。所謂“態度”只不過是自我論辯后最終立場的外化與修辭化表征[10](256)。論辯因而既是與他人互動的方式也是認識自我的途徑。它不僅貫穿于我們的生活實踐,也存在于我們自身。Bakhtin也強調,單聲獨白式的言說只是虛幻,所有的言說必然是向“他者”展開。不管言說看起來多么單聲獨白、多么專注于自身感興趣的物象而“不聞窗外事”,它都只會是對關于某一事物或問題的既有或可能出現的言說的回應,即便這種回應并無表露于外[25](92)。他指出,即便是看起來沉默、“被動”的受話人事實上也總是對所接觸到的他人的言說給予積極主動的回應——或認可,或拒絕,或延伸,或應用[25](68)。Burke也類似地指出,歷史饋贈給我們的每一文本都應當被視為是應對某一情勢的(論辯)策略。我們在考察如《美國憲法》這樣的文本時不應孤立地看待它,而應將其理解為是對流通于生發它的彼時的某些言說(如重商主義家長式統治的理論與實踐)的應答或辯駁[26](109)。對話或修辭學家所指的論辯因而是人的根本屬性。言說必然是充斥著證當與辯駁;所有的話語形態都是“在特定環境中產生效果的策略法”和“社會相互作用的形式”[27](441)。正如此,Burke說人是批評的動物[26](293)。
事實上話語批評實踐本身不折不扣地體現了修辭性——在“促進社會革新”這樣“不帶私利”的純學術批判的表象之下隱藏著話語批評非常實際和功利的修辭動機。首先,話語批評作為一種批評理路也好,語言研究學派也好,其一如商標般的縮寫名本身(如CDA、CL, MDA)即是一種類似于消費主義話語的營銷策略,或 Perelman所說的訴諸定義的等立論辯策略[13](208),意在最大限度地促進其在學術、教育場域和出版領域為學術受眾和商業受眾等所識記、傳播,并藉此帶動相關刊物、著作的出版及學術影響力的增加[28](41?2)。其次,“批評”這一字眼已然蘊含著話語批評實踐的修辭論辯性:在社會批判代表著一種高尚的修辭人格的當代西方學術場域,以“批評”冠名不僅是一種自我褒揚和證當,還暗含對那些非批評性的傳統語言理論或學術實踐這一反成主體的批評或回應,以及對學術資源乃至商業利益的爭奪[28](37?8)。“批評”與“非批評”的二元對立因此也是話語批評學者確立、昭示獨特學術身份的剝離論辯策略[20](130)。
六、結語
話語批評強調通過揭示機構話語生產者的權力操控和象征運作以促進社會革新與進步。然而,如果以Foucault的權力主體觀為基礎,則機構主體完全可以以自己乃“權力網”的蕓蕓一受體而開脫,何來機構壓制之罪責?如以Bourdieu之習性主體觀為理論支撐,則機構主體也可以沉淀“主體”中的無意識“習性”為藉口來搪塞其種種非為(如各族歧視、性別歧視)。而Habermas的交往行為主體則過于理想而超脫于生活世界之外。與此不同,根植于人文主義思想沃土的修辭學家認為主體是“行”之動源:不同個體或行動體的各種象征實踐均形構或認定為由主體生產、實施并產生各種社會效果的行動,因而可以認定為其“本質”所投射的“表征”,從而讓各種符號力與話語倫理責任關聯,為批判具體話語實踐對特定社會、文化的增益或損耗作用提供基礎。因此,修辭行動主體思想能夠讓“權力化”或“客觀化”的主體性得以恢復能動地位,為批評何以可能提供本體支撐。我們也可以藉此厘清界定話語倫理責任,從而彰顯批評的意義。
在當下東西方話語權力仍不平等的情況下,彰顯話語的修辭主體性對于在跨語際、跨意識形態的修辭互動中保持清醒頭腦亦有助力。在東西方話語互動中,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常常以隱性的形式展開。忽視或拋卻話語的主體性無疑會將源自西方的許多強勢話語的生產者泛化或者干脆忘卻,進而將隱含其間的跨文化動機擱置,為西方某些話語主體的“軟實力”的實現創造本不應有的機會。
[1]WODAK R.MEYER M.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London: Sage, 2001.
[2]FAIRCLOUGH N.Language and Power [M].London: Longman Group, 1989.
[3]PENNYCOOK A.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M].NJ:Lawrence Erlbaum, 2001.
[4]田海龍.語篇研究: 范疇, 視角, 方法[M].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9.
[5]MILLS S.Discourse.2nded.London & NY: Routledge, 2004.
[6]FOUCAULT M.Power/Knowledge [M].London: Harvester Press, 1980.
[7]FOUCAULT M.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M].Vol.1.New York:Vintage Book, 1980.
[8]FOUCAULT M.Discipline and Punish [M].N Y: Random House, 1979.
[9]BLAIR C.Symbolic Action and Discourse [A].In B.Brock (ed.).Kenneth Burke & Contemporary European Thought [C].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5: 119?165.
[10]BILLIG M.Arguing and Thinking [M].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7.
[11]BIESECKER B.Michel Foucault and the Question of Rhetoric[J].Philosophy & Rhetoric, 1992, 25(4): 351?364.
[12]BURKE K.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3]PERELMAN C, OLBRECHTS-Tyteca L.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M].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14]THOMPSON J.Editor’s Introduction.In P.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M].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1?31.
[15]BOURDIEU 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M].Cambridge,MA: Cambridge UP, 1977.
[16]ANDERSON D.Questioning the Motives of Habituated Action[J].Philosophy & Rhetoric, 2004, 37(3): 255?274.
[17]BOURDIEU P.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4.
[18]HABERMAS J.Communication&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M].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19]FARREL T.Comic History Meets Tragic Memory: Burke and Habermas on the Drama of Human Relations.In B.Brock(ed.).Kenneth Burke&Contemporary European Thought [C].Alabam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5: 34?75.
[20]PERELMAN C.The Realm of Rhetoric [M].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2.
[21]劉亞猛.西方修辭學史[M].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22]賀陶樂.《左傳》諫說應對的策略藝術[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5): 134?7.
[23]BURKE K.A Grammar of Motives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24]祝平良.從主體性哲學的角度看傳播活動中的傳受關系[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6): 854?6.
[25]BAKHTIN M.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r Essays [M].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86.
[26]BURKE K.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M].3rde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27]胡曙中.美國新修辭學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28]BILLIG M.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Rhetoric of Critique.In Weiss,G&R.Wodak (ed.).CDA: Theory &Interdisciplinarity [C].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35?46.